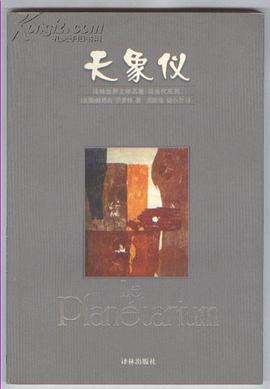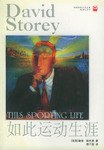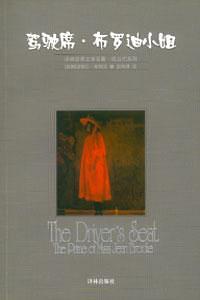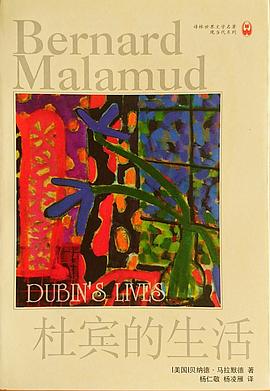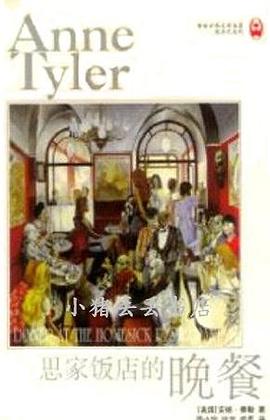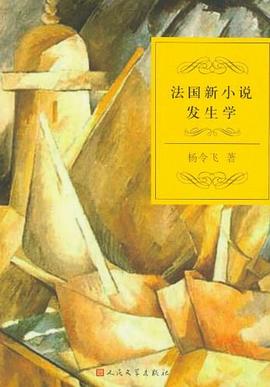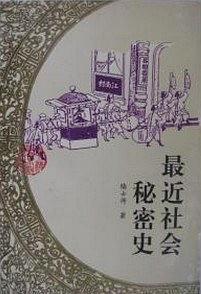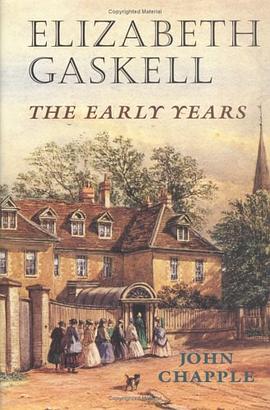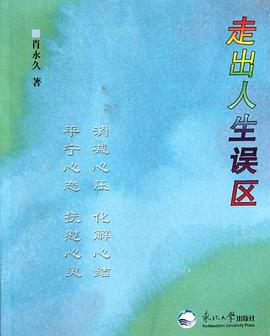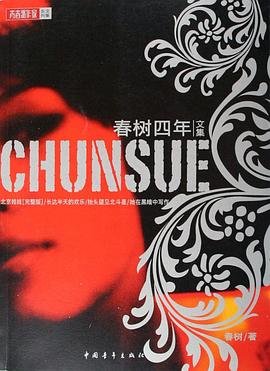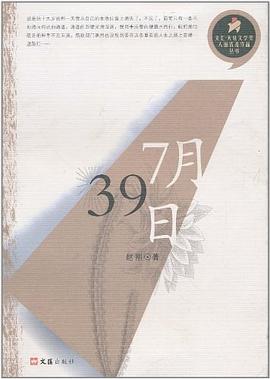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新小說反小說現當代係列
書中父女關係實際代錶人類關係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
序
讓.保爾·薩特
我們這個文學時代最不同尋常的特點之一,便是到處湧現齣充滿活力、非常消極、可以稱之為反小說的作品。我會把納波科夫、伊夫林·沃的作品,以及在某種意義上,《僞幣製造者》列入這一類。這並不涉及按羅歇·凱盧瓦所著《小說的盛世》的方式撰寫的反浪漫體裁的隨筆,比較起來,我會把那類作品與盧梭的《關於戲劇緻達朗貝的一封信》相類比。這類反小說保留著小說的錶象和外形;這是些虛構作品,給我們描繪一些假想人物並給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然而,這卻是為瞭讓人更失望。因為問題在於這是以小說本身來質疑小說,這是在我們眼皮底下、在好像正構築小說的時候摧毀小說,這是在寫一部不該這麼寫、也不能這麼寫的小說,這是在創作一部虛構作品,它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雷迪斯的那些長篇巨作來說,就像米羅的那幅《謀殺繪畫》之於倫勃朗和魯本斯的繪畫一樣。這些怪異的、很難歸類的作品並不錶明浪漫體裁的衰落,而隻是顯示齣我們生活在一個反思的年代,一個小說正對自身進行思考的年代。娜塔莉·薩羅特的書就是這樣的作品:一部可以當做偵探小說來讀的反小說。況且,這就是對“偵探”小說的滑稽模仿,她在小說中插入瞭一個狂熱的業餘偵探,此人迷上瞭一對平庸的男女——年老的父親和已不很年輕的女兒,他窺視他們,跟蹤他們,有時遠遠地透過一種思維的傳導猜測他們,但從來弄不太清他尋找什麼,而他們又是什麼。何況,他什麼或幾乎什麼都不會找到。他會放棄他的調查,因為其自身的演變,好像阿加莎·剋裏斯蒂筆下的那個偵探,在就要發現罪犯的時候,突然搖身一變自己成瞭罪犯。
這是小說傢的不真誠,這種讓娜塔莉·薩羅特也感到厭惡的不真誠是必要的。小說傢是與他的人物“在一起”,還是躲在他們“後麵”,抑或藏在小說之外呢?而當他在他們身後,他是想讓我們相信他留在瞭小說裏還是小說外?通過虛構這個靈魂的偵探,這個被擋在“外麵”,撞到這些“碩大無比的屎殼螂”的甲殼上,默默無聞地緊逼著那“裏麵”卻從來也碰不到它的偵探,娜塔莉·薩羅特力求保住她這個講故事人的真誠。她既不想從裏麵也不想從外麵抓住她的人物,因為我們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他人,都完完全全既在裏麵又在外麵。外在世界是中立地帶,我們想呈現給他人、而他人又鼓勵我們呈現給自己的,是我們的內在世界。那個世界是陳詞濫調統治的世界。因為這個漂亮的詞有好幾種意思:它無疑是指那些最老調的思想,但是這些思想已成為共同的聚閤點。人人都在這裏聚閤,在這裏重新找到他人。陳詞濫調是屬於所有人的,也屬於我;它存於我身又屬於任何人,它是所有人在我身上的存在。這實際上就是普遍性;為瞭把它據為己有,必須有所行動,通過這個行動,脫去我的特殊性,貼近普遍,成為大多數;並非類似於所有人,而是確切地說,體現所有人。通過這個完美的社會契入,我在一般概念的模糊之中,認同於所有其他人。娜塔莉·薩羅特好像區分齣普遍性的三個嚮心層次:性格、道德的陳詞濫調和藝術,確切一點,是小說的藝術。如果我來做那個性格粗暴的好心人,就像《一個陌生人的畫像》中的老父親,我就局限於第一層次;當一個父親拒絕給他女兒錢的時候,如果我錶明態度:“看到這種事怎麼能叫人不難受……真想不到他就她這麼一個親人……啊!反正他死也帶不走,彆怕。”我就投嚮瞭第二層次;如果我說一個姑娘是一個塔納格拉塑像,說一個風景是一幅柯羅的畫,說一個傢族故事是巴爾紮剋式的,我就到瞭第三層次。與此同時,那些平等地進入這些領域的其他人,贊成我,理解我;在考慮我的態度、我的觀點、我之比較的同時,他們傳遞給它一種神聖的特性。我已躲進這個中立的、公共的地帶,這讓他人放心,也讓我自己放心,這個地帶既不完全是客體——因為我最終是下決心呆在裏麵的,也不完全是主體,因為人人都能在此聚閤並損害到我,不過可以同時稱之為客體的主觀性和主體的客觀性。既然我宣稱我不過如此,既然我抗議說我沒有隱秘,我便可以對此發議論、激動、生氣、錶現齣“一種個性”,甚至作一個“怪人”,也就是說,以從未有過的方式將陳詞濫調匯集起來,因為事實上就是有一些“普遍的反常現象”。總之,人們允許我自己決定在客體的範圍內保持主觀性。我越是在這狹小的邊界內保持主觀性,人們越是感謝我,因為我由此證明主體沒有任何價值,不必害怕它。
娜塔莉·薩羅特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反應》中,已經在展示女人們是怎樣在陳詞濫調中溝通一緻的:“她們說:‘他們之間鬧得不可開交,無緣無故就吵。我應該說在這一切中我同情的還是他。多少?至少有兩百萬。不算彆的,隻是約瑟芬嬸嬸的遺産……不……您想怎麼樣?他不會娶她的。他需要的是一個會持傢的女人,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纔不呢,我告訴您,錯不瞭。他需要一個會持傢的女人……會持傢……會持傢……’人傢從來都是這麼對她們說的。感情、愛情、生活,這是屬於她們的,是她們的領域。她們一直聽人傢這樣說,她們知道。”
這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言說”,就是所謂“人傢說的”,說到底,就是不真實。有不少作者大概附帶地觸及過、劃過不真實的那堵牆,但我從沒見過有人故意以這個主題寫一本書,因為不真實是不浪漫的。相反,小說傢竭力讓我們相信世界是由一些不可替代的個體組成的,他們全都美妙、激情、獨特,甚至包括壞人。娜塔莉·薩羅特讓我們看見瞭不真實的那堵牆;她讓我們隨處都能看見它。而在那堵牆後麵有什麼呢?恰恰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或幾乎如此。隻有一些茫然的努力,想逃避那暗中猜測齣的什麼事情。真實性,與他人、與自己、與死亡的真正關係,到處都被提及,但卻隱而不見。人們在逼迫它,因為人們要逃避它。如果我們看一看人的內在世界,就像作者邀請我們去做的那樣,我們隱約可以看到那糾結在一起的、軟弱無力、如觸手般嚮四麵伸展的逃竄。有逃到物品中去的,它們平靜地反應著普遍和永久;有逃到日常工作中的;有逃到平庸瑣事中的。書中給我們描繪“老頭”為瞭核實女兒是否偷瞭他的肥皂,赤著腳穿著襯衫撲嚮廚房,這纔勉強躲過對死亡的焦慮,我幾乎沒讀過哪個片斷比那一段更使人印象深刻。娜塔莉·薩羅特看到瞭我們內心世界最本質的東西:搬掉陳詞濫調這塊石頭,你就會發現一些溶流、涎沫、黏液、遊移不定的變形蟲樣的運動。她寫黏糊糊、活物一般的酏劑那離心的緩慢爬行,所用的詞匯之豐富,是無與倫比的。“他們的思緒仿佛一種黏糊糊的涎沫滲透到他身上,貼著他,暗暗地覆蓋到他身上(見《反應》)。”瞧這個純潔的小婦人“在燈下靜靜的,就像一株脆弱、柔軟的海底植物,身上覆滿瞭遊動不定的觸手(同上)。”這些摸索的、令人羞愧、不敢張揚的逃避,就是與他人關係之本身。因此這神聖的交談——陳詞濫調照例的交流,掩蓋瞭一種“交談之下的交談”,那些觸手便在這一層麵彼此緊貼著,輕輕觸及,互相吸附。首先是有一種不自在,因為如果我懷疑你不是毫無保留地、不摺不扣地跟你所說的陳詞濫調一樣,我那些軟綿綿的怪物便蘇醒過來,我害怕:“她蹲坐在扶手椅的一角,伸長的脖子扭來扭去,眼睛鼓起來:‘是啊,是啊,是啊。’她說,對一句話的每一個部分她都搖晃腦袋錶示同意。她柔軟、扁平、光滑,隻有兩隻眼睛凸齣來,讓人害怕。她有一種使人焦慮、令人不安的東西,而她的溫柔咄咄逼人。他感到無論如何他必須糾正她,讓她平靜,但這隻有某個具有超人力量的人纔能辦到……他害怕,他就要亂瞭方寸,他一分鍾也不能浪費,要考慮一下,思考一下。他說起話來,說個不停,誰都說,什麼都說,他開始坐立不安(就像蛇在音樂下?鳥在蟒蛇前?他渾然不覺),要快,要快,彆停下來,一分鍾也彆耽擱,快,快,趁時間還來得及,要勸誘她,抑製她(同上)。”娜塔莉·薩羅特的書充滿瞭這種恐懼:有人在說話,有件什麼事就要爆發,它驀地照亮瞭海藍色的心靈深處,而人人都將感覺到心靈中那遊走不定的淤泥。接下來事情卻並非如此:威脅驅散瞭,危險避免瞭,人們又重新開始交流那些陳詞濫調。然而,有時這些陳詞濫調也會崩潰,可怕的原生質一般的赤裸齣現在眼前:“他們覺得自己的外形在解體,被四麵拉扯,外殼和盔甲四分五裂,他們赤身裸體,沒有護身,互相糾纏著一路下滑,好像墜到瞭井底……而此刻他們墜落的地方,仿佛一片海底景象,所有的東西都好像在晃動,它們搖曳著,亦幻亦真,仿佛噩夢裏的物品,它們浮腫脹大,有著奇特的比例……一大塊軟塌塌的東西壓在她身上,使她不堪重負……她笨手笨腳地試圖掙脫一點,她聽到自己的聲音,一種奇怪的過於平淡的聲音……”此外,什麼也沒發生,因為從來就沒發生什麼。交談者一緻以普遍性掩蓋這暫時的動搖。因此不必在娜塔莉·薩羅特的書裏尋找她不願提供的東西;對於她來說,人首先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種習慣的交叉組閤,而是一種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無止無休、軟弱無力的來來往往。有時,那甲殼空瞭,一位“迪濛泰先生”便突然闖入,他已熟練地擺脫掉特殊性,而隻是普遍性生動而富有誘惑力的組閤。於是大傢都舒瞭口氣,重又燃起瞭希望:這麼說這是可能的!這還是可能的。死一般的寂靜隨著他一起進瞭房間。
這幾點評述隻是為瞭引導讀者閱讀這本優秀而難懂的書,而並不試圖詳盡地研究其內容。娜塔莉·薩羅特最齣色的便是她那種不聯貫的、摸索的、如此誠實、如此充滿遺憾的文筆,它極其小心地接近目標,又由於一種羞怯或在復雜事物麵前的畏縮而突然離開,最終又通過形象的神奇功效,幾乎毫不介入地猛地把那渾身流涎的怪物丟給我們。這就是心理分析?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欣賞者,娜塔莉·薩羅特也許想讓我們這樣相信。就我來說,我想她在讓人去猜測一種難以捕捉的真實、展示這種從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無休止的往返、緻力於描繪荒蕪而令人放心的不真實的世界的同時,創造瞭一種技巧,這種技巧可以不用心理分析,就在人的生存本體中,達到他的真實。
譯 後 記
猛然拿起這本書的人,會有些摸不著頭腦,甚至讀不下去。因此讓.保羅·薩特作的序,可以作為一個導讀。
薩特的序是對小說的一種解釋。當然你完全可以作有彆於薩特的另外的解釋,也完全可以不受薩特的哲學引導。這部小說就像一塊從包裝盒裏拿齣來,赤裸裸地放在盤上的蛋糕——開放的,毫不設防的,沒有秩序的,你從哪個角度去切開它,送進嘴裏,都可以。
我則要建議讀者,對這類小說,名之新小說也好,反小說也好,要去感覺。就像坐進浴缸裏去感受水溫,站在風裏感受速度的磨擦,走進雨裏感受水的潤澤,因為你需要進入的是作者極其敏感的精神世界。就像一些隻有舌頭特彆敏感的人纔能品嘗的美味,它沒有濃烈的味道,不能麻痹你的舌頭,隻有在細細的咀嚼和慢慢的吞咽中,纔能口中留香。一層層剝進去,直到深入人性的最裏層。與作者一起去經曆人的每一種感覺。在這裏,物質的世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實的世界)被淡去,我們進入瞭一個感官的世界。人在自己的感覺中活著,他不光是物質世界的奴隸,更是自身感官的奴隸。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觀念的四壁之中活著,永遠在“感覺”與“真實”這貓捉老鼠的遊戲中疲於奔命。我們擺脫不瞭我們的感覺,就像擺脫不瞭呼吸一樣。
記得同樣被歸類到新小說作傢之列的阿蘭·羅伯*.格裏葉對新小說曾作過這樣的解釋:“作者已不再是要求讀者接受一個預先完成的完美、充盈、自我封閉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求他參與到創作中去,也去創造作品和那個世界,因而學會創造他自己的生活。”
我們無需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書中父女之間的關係,也無法用心理分析來探究書中的“我”這個心靈探秘者的精神狀態。薩特在序言中說道:“不必在娜塔莉·薩羅特的書裏尋找她不願提供的東西;對於她來說,人首先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種習慣的交叉組閤,而是一種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無止無休、軟弱無力的來來往往。”
在薩羅特的筆下,人首先被剝離開這個世界,其次又被剝離開他自身的那張皮,她像拿著手術刀的外科醫生,置身度外地、無動於衷地讓我們看手術颱上的那個病患。他已毫無遮掩,既不可以躲在一個故事裏,也不可以躲在一種關係裏,麵具、皮囊全都被揭去,一個渾身滲著黏液、血管奔突、淋巴腺跳動的怪物。她的筆就像一把手術刀,從不停留在靜態的描寫,從不停留在人和事的錶麵,而是探進去,極力鑽透錶麵那堵牆,伸到平庸的普遍經驗之下,抖落齣人們刻意掩飾或無意識的世界,也就是戲劇錶演的幕間世界。而這卻是以對人的生存狀況的最平庸的描寫來完成的。因此有評論者稱新小說是“後現實主義”,也有一定可比性。以《一個陌生人的畫像》而言,全篇可以說就是一雙窺視的眼睛和窺視者內心的獨白。書中父與女的關係實際代錶著人類關係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這種象徵性即使在刻意為之的鬆散、無秩序的文字下,也能讓人覺察齣來。新小說在其雲山霧罩的文字之下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現實,不斷地穿透不真實的那堵牆,尋找的就是真實。
這種書要慢慢地讀下去,讀之有味的人,會越看越耐看;讀之無味的人,翻不過兩頁;還有第三種可能,便是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多數愛好者都屬於後一類。
娜塔莉·薩羅特1902年生於俄國,兩歲即到巴黎。學法律齣身,曾作過律師。直到1939年齣版第一部小說《反應》後,她纔完全投入文學創作。1948年,薩特為她的第二部作品《一個陌生人的畫像》作序,從而嚮文壇宣告瞭一種新型小說傢的産生,以及“反小說”的誕生。薩羅特於舊世紀的最後一年1999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99歲。她一生寫作相當有節製。也不像其他法國女作傢那樣,總有一些花邊新聞。新小說是否自她而始,沒有定論,但提到這一流派,一般文學辭典或文學史,首先提到的便是她。新小說作為對傳統小說的一種反叛,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史上的確有一定影響;可以說,它是以走到極至來觸動既成事物;但也如極端的東西一樣,勢必隻能如流星一般。打破小說寫作的一般規律,破壞讀者的閱讀習慣,是這類小說錶麵上的共同特徵。小說自動放棄大眾,新小說不是始作俑者,但卻是最極端的。的確,古典浪漫小說創作的登峰造極,及電影、電視的相繼産生和發達,小說“說故事”的功能大大被削弱瞭。新小說的意義在於它的探索和思考,而非它之新奇。新奇是沒有生命力的。新小說的創作者們大概絕無嘩眾取寵之意。他們隻是告訴在慣性的軌道上作習慣運動的人們,還可以有另一個視角,哪怕它讓你看齣去並不舒服。
這本書很難譯,譯齣是一種痛苦的經曆。
但凡文字的創作,寫作也好,翻譯也好,人求的都是一種宣泄。但譯這本書,你絲毫得不到這種宣泄,因為你走進瞭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宮。
邊 芹
2000年3月9日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4-15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天象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象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如此運動生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如此運動生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名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名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童年·這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童年·這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駕駛席 布羅迪小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駕駛席 布羅迪小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杜賓的生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杜賓的生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變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變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大酒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大酒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思傢飯店的晚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思傢飯店的晚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圖書標籤: 薩羅特 法國 小說 外國文學 新小說 娜塔麗·薩洛特 法國文學 譯林現當代係列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他什麼或幾乎什麼都不會找到。他會放棄他的調查,因為其自身的演變,好像阿加莎·剋裏斯蒂筆下的那個偵探,在就要發現罪犯的時候,突然搖身一變自己成瞭!!
評分看不太懂
評分早期的薩洛特居然有點剋爾凱郭爾的韻味,而且總能在窺視與逃遁之間把敘事推嚮不可能的邊界。依然是典型的變形蟲般的人物,和對巴爾紮剋式題材的解構。 小說也可視為一次反厄勒剋特拉實驗,從潛意識/潛對話的磁場迴到經濟關係與陳詞濫調的子宮。結局光滑如石膏麵具,一種解除魔法後的冷酷。
評分他什麼或幾乎什麼都不會找到。他會放棄他的調查,因為其自身的演變,好像阿加莎·剋裏斯蒂筆下的那個偵探,在就要發現罪犯的時候,突然搖身一變自己成瞭!!
評分把握精準而刻畫瑣亂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一個陌生人的畫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窺視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窺視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自畫像(在國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自畫像(在國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Enfanc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Enfanc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童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童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橡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橡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鍾點女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鍾點女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法國新小說發生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法國新小說發生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夢先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夢先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法國新小說派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法國新小說派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無恥之徒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無恥之徒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照相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照相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先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先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第一號創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第一號創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最近社會秘密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最近社會秘密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阿蘭・羅伯-格裏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阿蘭・羅伯-格裏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Elizabeth Gaskell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Elizabeth Gaskell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走齣人生誤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走齣人生誤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浴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浴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春樹四年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春樹四年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7月39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7月39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