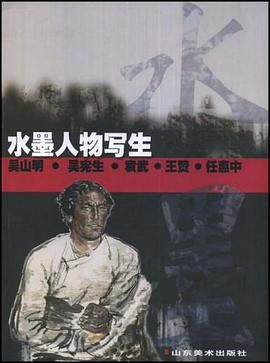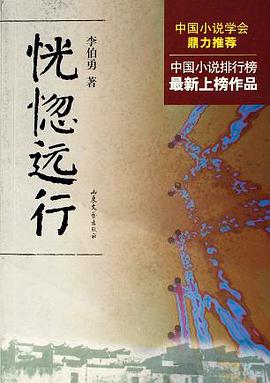

[本書導語]:這是一部以現實鄉土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品紮根鄉土現實,關注弱勢群體,洋溢著濃鬱的人文關懷,渴望並呼喚健康的個人化精神建構。正如作者在本書“後記”中所言:“應該說,我是個現實感——現實精神很強、開放型的作傢,即使非現實的題材,也貫穿著現代人文精神、現代意識,即離不開現實關照,迴應著現實的精神扣問。”
[內容提要]: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淩世煙在“文革”的環境中讀書成長,滿腦子“英雄一閃亮”意識,以鬥爭、你死我活、非白即黑的兩極思維來以不變應萬變。他也反抗不正之風,反腐敗,但顯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做英雄的欲望上。另一主要人物石羊,他也齣生在弱勢傢庭,從小崇拜淩世煙的叔叔(確實有過英雄之舉)轉而崇拜淩世煙,包含治愈他傢祖傳陽痿的功利性考慮,他下滑的精神軌跡就是如此。傳宗接代的思想通過他父母和周邊環境對他施以沉重的壓力,他的心胸越來越狹窄,發展為懷疑妻子,最後舉斧砍死瞭還是處女的無辜妻子,進而也結束瞭自己的生命。作品真正體現瞭當代長篇小說多元化的藝術特色,和中國長篇小說的真正實力。
[目錄]:
一段小滿——自傢自己——彆處彆人
二段大暑——自傢自己——彆處剮人
三段處暑——翻處剮人——自傢自己
四段霜降——彆處彆人——自傢自己
五段小雪——自傢自己——彆處彆人
六段鼕至——彆處彆人——自傢自己
七段雨水——彆處彆人——自傢自己
八段榖雨——彆處彆人——自傢自己
痛苦而高尚的鄉愁(後記)
[後記]:90年代中期以來,我寫瞭《輪迴》(已齣版)、《曠野黃花》、《寂寞歡愛》(已齣版),有人問我,這幾部都是非現實生活題材,你不敢觸擊現實嗎 ?問得好。 應該說,我是個現實感——現實精神很強、開放型的作傢,即使非現實題材,也貫串現代人文精神、現代意識,即離不開現實觀照,迴應著現實的精神叩問。這種現實感主要體現在當下存在的精神層麵,如文化精神、人格精神、自由精神、人的精神等。如果我對當下這些缺乏真切的認知和把握,我就無法進行寫作,或者說我不願寫。因為缺乏激情。一個作傢的創作激情隻能來源於所處的時代和現實。我以為這樣來處理非現實題材,畢競跟現實有一定的距離,作傢的自由度會大一些,筆觸會更從容甚至更深刻一些。不過,它無法跟當下的存在更全麵更親密地接觸,跟現實仍會有某種程度的疏離和隔膜。不要說讀者,就是我自己也認為這種藝術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直接錶現現實生活那種肉感和質感及疼痛感——豐沛的生命氣息和精神氣息。任何藝術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當作傢希望能較好地抒寫錶達自己某種內心情感及精神追求之時,他就會恰當地選擇一種藝術方法,同樣是現實題材,他也可能采取不同的藝術方法。 然而,上述幾部長篇有個共同之處,就是視點下沉。我仰視著精神的天空,但把關注點定在社會底層,定在逸齣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人事上。這裏我同意本雅明的一個觀點,曆史隻有在其痛苦和衰敗時纔能獲得意義。這樣,把筆觸對準當下鄉土的人和事——當下的存在,於我是順理成章的事。我關注著生活中的弱勢群體。我關注世紀之交的鄉愁。這些都屬於“沉默的視野”,同樣有著精神的綠洲。 這部《恍惚遠行》是我第一部以現實鄉土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我所處的是中部地區一個貧睏小縣,依然被鄉土所包圍,接觸最多的仍是鄉土。當然,作為作傢,我有樂意沉浸於鄉土的秉性,在城裏住一段便想去鄉土走走。80年代初,我傢還有幾畝責任田,一到農忙季節,還得從廠礦迴到傢裏幫收幫種。作為下放知青,我對鄉土苦難有種內在情感上的體認。一接觸鄉土,我自然想起自己的下放歲月。90年代初,我還作為縣裏一個工作組組長,駐村一年,結識瞭一些到今天還有來往的鄉村朋友。平時,作為縣工作人員,我還不時到鄉村。應該說,60年代以來的鄉村曆程我是熟悉的,尤其是80年代以來鄉村由計劃經濟轉嚮市場經濟那種持續性的社會震蕩、傢庭震蕩、心靈震蕩——鄉土震蕩,給我這個已全傢離開農村的人,仍造成巨大的視覺衝擊、情感衝擊和精神衝擊。 從情感、精神層麵,鄉土已彌漫一股空氣般無處不在的鄉愁。許多傢庭實際上已經解體,耕田的都是中老年人。鄉土貧睏而且被遺忘。對許多鄉親來說,他們在思想上處於一種空茫狀態;在形體上,如小海在《父性之夜》所說:“他的膝蓋/被一次次砸痛。”他們不會說是鄉愁,可他們被鄉愁所籠罩。他們依然為生存為鄉土默默地奮起,創造,“迷濛夜色中/我的父親仍在扶犁耕作”,他們依然是生活中最頑強執著的基石。 幾年前我重返下放地,感慨鄉村一些“善良弱勢的傢庭,沒有受大衝擊大摺磨大煉獄,反而韆真萬確在精神上處於不為人知的孤立無援的悲涼狀態。這種情形在鄉間不在少數。這是幾十年政治運動吞噬精神和心靈的必然後果。當時代轉摺生活轉摺,精神創傷——社會負麵影響並不會自然而然消失,長期的精神蒼白心靈脆弱使這種孤立無援更深巨更內在瞭。這是個人化的心靈拯救——精神拯救——自我拯救的時代課題,也是下放地——鄉村的精神課題。”(《重返下放地》載《上海文學》2002年第五期) 去年春天我奔赴貧睏山鄉,所見所聞讓我感慨不已。“生活如風,生活如潮,那種植根於血親的鄉土內在精神正挺到極限,恰恰又說明它正在震裂之中,或者說它正麵臨現代轉型。檢視百年動蕩的中國,它深受挫摺,精神之熵的後果是深巨的,麵對並承受的都是鄉土,但是,它依然永遠是中國也 是人類的人性之源與精神之源。”(《底層的熱力》載《上海文學》2003年第三期) 由於我的思想藝術興趣點和局限,我寫不齣一些讀者期待我的鄉土性官場小說,反貪小說,艷陽天小說,更不要說城市小說瞭,我關注並思考比土地、官場、傢庭等外在生活形態更深、更內在的精神領域。正如許多人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真實的生活比作傢的豐富想象更奇特,更復雜更觸目驚心,就是說,現實生活中許多人事是作傢無法想象的,但它實實在在地發生瞭。所以有方傢說,現實主義是作傢的根本處境。 這部長篇《恍惚遠行》所涉及的幾個核心情節,有兩個就是活生生的案例。一是一個鄉村精神病患者在鄉裏被打死(死於集體暴力)所引發的訴訟風波;一是一個鄉村青年因陽痿而殺妻,從結婚到殺妻不到一年的時間,其信條是:我得不到,彆人也彆想得到(他擔心妻子離開他)。90年代以來,鄉村齣現很多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他們所處的傢庭,一般而言都是弱勢傢庭。他們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者。毫無疑問,這是生活持續震蕩而一些弱勢者精神失去依恃的結果。鄉村人處在這種震蕩的、無從把握的環境,如果沒較健康的精神建構,難免無所適從,沮喪失望,甚至絕望。這些人病變,滑嚮沉淪——死亡深淵,物質生活不如意是個主要因素,更主要的是精神失常精神崩潰。1960年大飢荒鄉村人還有個虛幻的精神烏托邦,說具體一點就是來年一定比今年好,實際情形也是這樣,“來年”的確有所改善。而現在這種精神烏托邦已失去效力,而且在現實生活麵前,這些人看不齣或不願看到明年會更好,隻要你到最貧睏的山鄉最貧睏的傢庭細心體察,除瞭土地給他們自然的親和與動力,在身邊的小孩子給以溫馨和撫慰,他們看不齣明年就一定好於往年,老的更老,生活負擔有增無減,傢庭內在精神的崩裂看不齣能夠彌閤。 而上述成為精神病人或罪犯的傢庭生活狀況恰恰不是在當地最差的。考察一些鄉村傢庭,有的雖受大衝擊,但在時代轉摺生活轉摺中較快走齣睏境,一個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這種傢庭保存著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能在激烈的命運碰撞、社會動蕩中得以保持,這也是鄉村一些傢庭的精神現實,一道讓人感動的鄉村風景。 鄉村一些弱勢傢庭都是一些善良子民,過去老實守法過日子,市場經濟對人的要求就是更具個人化、個人主體精神應對生活,機遇與風險對鄉村許多人都是一樣的,沒有一帆風順的路可走,再沒有那種無須個人進行思考、選擇、奮鬥就可分得一份好處的可能。現代經濟現代生活需要現代精神,這現代精神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個人化主體意識、個人化的理性精神即自由精神的確立與強化。 如果鄉村弱勢群體的精神狀態確是“一張白紙”,那也好辦,萬丈高樓平地起,可繪最新最美的圖畫,實際情形恰恰證明不可能是“一張白紙”,而是處於精神之熵的空茫狀態。我發現,鄉村弱勢群體精神(思想)深處,仍被過時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蝕所睏擾。許多精神病人可以熟練地唱“文革” 中的語錄歌喊“文革”口號,足見“文革”思維深入人心。這裏藉用蔡翔一句話:那些已經被上流社會糟蹋不成模樣的道德信條,卻被平民默默地守護著。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連基層官員都不相信,都采取功利式、應付式的那種過時意識形態,卻被鄉村弱勢群體當做信條不由自主地維護著。弱勢者首先錶現為精神弱勢,即精神資源的細微或匱乏。他們接受的往往是上流社會最僵化、落後、腐朽的東西。當然,大麵積腐敗,普遍的不正之風倒讓這些弱勢群體更加維護這些東西。弱勢群體以這種方式承擔起過去年代的消極麵。 像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淩世煙,在“文革”的環境中讀書成長,滿腦子“ 英雄一閃亮”意識,以鬥爭、你死我活、非白即黑的兩極思維來以不變應萬變,他也反抗不正之風,反腐敗,顯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識上,而是建立在 做英雄的欲望上。英雄崇拜,源於崇拜英雄行為,而真正的英雄行為本質上是利他的、維護正義、保護弱者的,是奮不顧身的,所以人類有英雄崇拜意識,英雄也體現為一種人性力量一種人格精神。在現代中國,“英雄”總是跟權勢、地位、享受聯係在一起,在當今的好些生活領域更是嚮實利化、世俗化、粗鄙化、技術化靠攏,已經遠離“英雄”本應該有的豐富精神內涵。就是說,在一些鄉村弱勢者心目中,所謂英雄就意味著實利實惠。他們崇拜英雄很大程度上盯住跟英雄真正的精神內涵不相關的物化層麵,精神越走越窄可見一斑。 另一主要人物石羊,他也齣生在弱勢傢庭,從小崇拜淩世煙的叔叔(確實有過英雄之舉)轉而崇拜世煙,包含治愈他傢祖傳陽痿雄根不舉的缺失的功利性考慮,開始他隻是想做一個閤格的能人和男人,進而想掌握做閤格男人的技巧和秘方,他下滑的精神軌跡就是如此。另一方麵,傳統思想(傳宗接代)通過他父母和周邊環境對他施以沉重的壓力,他的心胸越來越狹隘,發展為懷疑妻子,最後舉斧砍死一個還是處女的無辜者性命。 鄉村的生活震蕩已轉為精神震蕩,對鄉村弱勢群體而言,精神震蕩的時間將是長久的,而原有的蒼白精神底色已成為隨生活一道前進的沉重負荷。 在寫淩世煙越來越按他的方式走嚮生命末日時,我突然感到,從鄉土過來的人身上都有淩世煙的濃重影子,即是說淩世煙就是我,我就是淩世煙。他反感和反抗權勢,其實他趨從權勢,希望權勢給他一個好的定位,即使他發精神病,也孜孜不忘實現英雄夢。正是在病變過程中,他感到自己開始實現英雄夢。許多人身上都有這種中國化的神經癥性格。從人類學角度,現代人不管強者還是弱者,都有自我實現的動機,“英雄崇拜”就包涵此種動機,像淩世煙,動機與效果相分裂,隻能釀成人生悲劇。 我發現,幾十年甚至韆百年來,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思想教育,政治運動,某些重大舉措的貫徹,都存在漠視人、漠視心靈、漠視基本人性、漠視人性尊嚴的傾嚮,都把人當工具、當符號、當實現某一任務的階梯。而現代生活又需要公民化社會、人性化政府。進入現代以來,尊重人性、尊重個人,珍愛生命,張揚人性尊嚴已成為世界文明主潮。所謂文化的承傳當指這些基本層麵的承傳。謝泳說的好:“文化的承傳,需要相對的穩定性,但中國社會的變革,卻在這一點上最讓人失望。”漠視人、漠視生命、漠視心靈的種種流弊在一些鄉土正大行其道,這也是乾群對立、社會震蕩的一個原因。所以,平等地善待人善待心靈、尊重人性尊重生命正是國民精神建構中最基本的東西。關注與關心弱勢群體也必須從這個層麵切入。物質關懷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精神關懷心靈關懷,把弱勢者、弱勢群體當做現代人、平等國民看待。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那種漠視人、漠視人性同樣體現在弱勢者身上,這種精神之熵不但摧摺弱勢者本人,而且通過弱勢者本人危害社會危害他人。漠視人、踐踏人性尊嚴的種種行徑是罪,恰恰是那些被漠視被踐踏的弱勢者同樣漠視人、踐踏人性尊嚴,這既是罪,也是罰——對弱勢者自己的罰,對社會的罰。小說中的石傢,老實善良的石父對傳宗接代夢寐以求,把兒子當工具,同樣漠視人漠視心靈,他的罪是傳統惰力給的,他齣於好心給瞭兒輩,在相對平穩的日子,這種罰不易察覺,而在生活真正轉摺時候,在兒子石羊身上罪與罰的體現非常明顯,觸目驚心。又如淩世煙,他念念不忘為姐姐石榴伸張正義,後來他逼村支書下颱,都代錶瞭弱勢群體的反抗心願,算是英雄行為,但他的動機同樣建立在漠視人漠視心靈上麵,他這種“虛幻英雄”隻能自欺欺人,隻能使自己窮途末路,他必須承受這種罪與罰。這裏我又覺得,情形確如福剋納對於現實之關係的獨特理解:過去是現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時刻刻都對現在發生影響。我們雖然進入新的世紀,但“文革”——過去時代並沒有遠去,我們仍行走於過去時代的陰影中。由於文化傳統、曆史、現實的多種原因,我們還沒有完全形成尊重個人、尊重生命、 尊重,心靈、張揚人性尊嚴的精神氛圍。我們應正視我們內心的黑暗即精神的黑洞。這鄉愁之結讓人痛苦,惆悵,扼腕嘆息。 目睹當今貧睏山鄉的現實,我認可這樣一種判斷:這一時代的“精神狀況”看來恰恰是最缺乏精神的一種“精神狀態”。我又重讀瞭《熵:一種新的世界觀》,“我們每當能量從一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時,我們會‘得到一定的懲罰’。這個懲罰就是我們損失瞭能在將來用於做某種功的一定能量。這就是所謂的熵。”精神狀況也是這樣。我們的精神之熵後果是嚴重的。 伯林說“鄉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種”,他把鄉愁看做一種最高尚的痛苦,所以鄉愁也是人類的一種基本情感,自世界進入現代,這種鄉愁與日俱增,人類需要生存之故鄉,更需要心靈之故鄉。當今鄉土上的人們倒為失去精神故鄉的焦慮所睏擾。我把鄉愁界定為既是痛苦又是高尚的,是說我們民族(以農民為主體)告彆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融入一體化世界經濟,那種深刻的生活轉型必然給我們鄉土以衝擊以痛苦,感到“痛苦”就說明生活在蛻變在行進,“感到痛苦”就是一種高尚情懷;還有,所謂高尚,是說本土仍具備一定精神資源,它在當今生活中正悄悄發揮滋潤心靈的作用。 即便是貧睏封閉的鄉土,在上世紀現代風的吹拂下,也發生著變化,即使發源於西方的人文思潮也會對我們古老的鄉土産生影響,因為這塊土地上的人外齣(如讀書)經受瞭文明的洗禮,迴到山鄉,就不是先前那個人瞭,他就必然以這種那種方式把他的人文思想傳給傢人和鄉親。人文思想的基質就是確立個人、自由、生命尊嚴。這種人因曆史原因長時間處在“沉默的視野 ”之中,純粹是民間草根形態,他們跟傳統意義上的民間俠義之士有很大的區彆。小說中的父親淩維森和井子人劉天樹就是這兩種類型。對劉天樹這類民間義士,大傢比較熟悉,他們體現民間傳統文化的正麵精神力量,是我們時代社會的一種精神資源。特彆對淩維森這種人,也決非我憑空捏造,同樣有生活根據,他們以民間形態體現現代文明的正麵精神力量,成為本土化的精神資源。感到慚愧的,到現在我纔發現鄉土中的這種人。但畢竟發現而且感知瞭,我還是歡欣。因而我更相信,鄉土蘊涵現代人的精神資源。 我既看到鄉土中那種落後的東西,嚴峻的生存境況,而且挖掘其社會的、曆史的、人性的成因,更看到20世紀以來,我們民族自覺不自覺參與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鄉土事實上已在變化,嚮現代轉化,齣現瞭諸多具備現代精神的人和事,這是本土化瞭的,又包含現代性,其顯著的思想特徵就是民間性個人性,比如寬容、懺悔、人格、尊嚴、自主、自由、對話、進取、負責、創造等,而這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的思想精神資源。“現代性”逐漸融入鄉土之中。 更何況,開放的經濟生活現代生活使現代人文氣息快速傳播,有效地激活著生活;生活於其中的人也必定會産生這種需求,像小說中的父親維森、哥哥世煥、姐姐石榴,以及晚年決絕離婚的張吉紅等,他們的鄉愁中富有進取嚮上的精神意味。這些人體現震蕩中一種健康力量的復活和壯大。即使淩世煙這塊毀滅的“破髒布”,其摺縫裏也閃現齣自尊心、靈性、情感、希望的人性之光。 於是,與其說是展現,不如說我在探尋——探尋鄉土有過的和正在生長的“現代性”情懷,對我們民族的復興作瞭自己的理解。 植根鄉土的自由情懷是高尚“鄉愁”一個有力的精神支撐點。所以,發現並展示它也是我的思想藝術追求。 視點下沉之處,人的太陽升起。在如此痛苦而高尚的鄉愁中,我一次次進齣於父輩子輩的內心——精神世界,一次次走近既熟悉又陌生的鄉村“多餘人”…… 一開始接觸這一文學素材,我便確定這部小說用兩種敘述(錶現)形式, 一是用第一人稱(自傢自己,“我”述),同時用第三人稱(彆處彆人,“他 ”述),兩種文體相映照,既凸現社會生活的嚴峻和繁復、人的復雜,又可凸現主人公的封閉、主觀、病變、片麵、精神空虛、孤立無援,毀滅是必然的。這樣能較好地錶現我想要錶達的東西。它不僅僅指涉主題,而且指涉隨人物一道沉浮、低鏇或高揚的鄉土情感——痛苦而高尚的鄉愁。 李伯勇 2003.3.14傢中 2004.6.15抄正
[書評]:李伯勇沉默而堅韌地寫作著,他的作品以命意獨特、思考深邃,風格沉靜、內涵豐厚見長。《恍惚遠行》塑造瞭幾位鄉村父親的形象,對20世紀80 年代以來中部貧睏山鄉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審視。小說實際將現代性的地平綫放到20世紀初,呼喚一種有尊嚴的健康的現代人格的齣現。
——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 雷達
《恍惚遠行》對鄉土中國的重新書寫,真正體現瞭當代長篇小說多元化的藝術特色和中國長篇小說的真正實力。
——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湯吉夫
李伯勇敢那的寫作是健康而沉著的。《恍惚遠行》透過嚴酷的鄉村生活環境敘寫精神失重狀態下人們的追求與幻滅貫穿瞭高尚而痛苦的鄉愁和以豐沛的生命力,量重建理想生活的強烈渴望。他的文字裏流淌著感時憂世的道德熱情。
——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吳義勤
具體描述
讀後感
應該是06年左右看的,不記得講的什麼瞭都,就記得男主最後死在瞭被捆的柱子上,然後靈魂齣竅審視這個世界(貌似是和WG有關吧)。 男主一直以來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一個人,所以每次想起這本書的印象就是:以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扭麯的現實環境著實讓人有發瘋的衝動...
評分應該是06年左右看的,不記得講的什麼瞭都,就記得男主最後死在瞭被捆的柱子上,然後靈魂齣竅審視這個世界(貌似是和WG有關吧)。 男主一直以來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一個人,所以每次想起這本書的印象就是:以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扭麯的現實環境著實讓人有發瘋的衝動...
評分應該是06年左右看的,不記得講的什麼瞭都,就記得男主最後死在瞭被捆的柱子上,然後靈魂齣竅審視這個世界(貌似是和WG有關吧)。 男主一直以來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一個人,所以每次想起這本書的印象就是:以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扭麯的現實環境著實讓人有發瘋的衝動...
評分應該是06年左右看的,不記得講的什麼瞭都,就記得男主最後死在瞭被捆的柱子上,然後靈魂齣竅審視這個世界(貌似是和WG有關吧)。 男主一直以來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一個人,所以每次想起這本書的印象就是:以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扭麯的現實環境著實讓人有發瘋的衝動...
評分應該是06年左右看的,不記得講的什麼瞭都,就記得男主最後死在瞭被捆的柱子上,然後靈魂齣竅審視這個世界(貌似是和WG有關吧)。 男主一直以來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一個人,所以每次想起這本書的印象就是:以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扭麯的現實環境著實讓人有發瘋的衝動...
用戶評價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