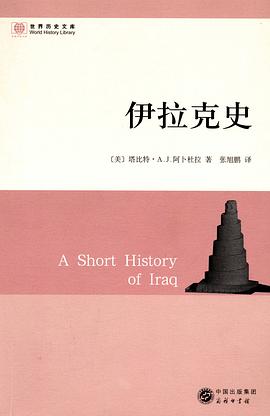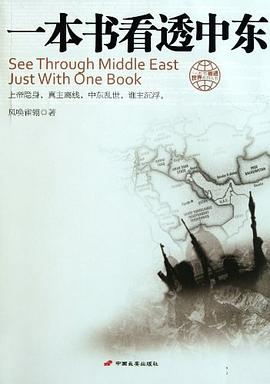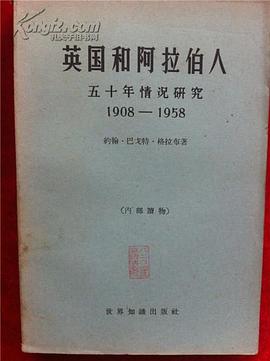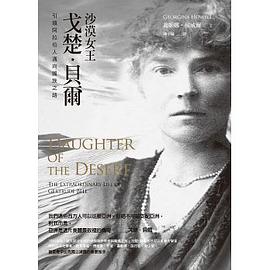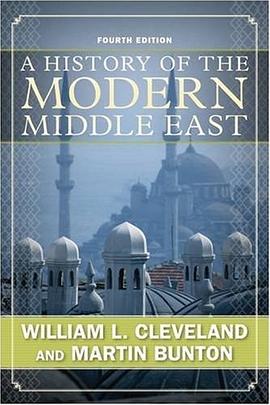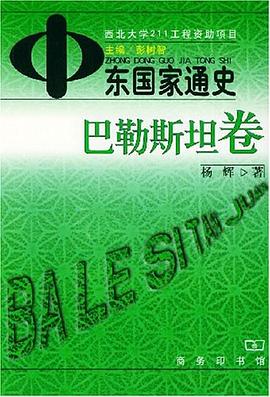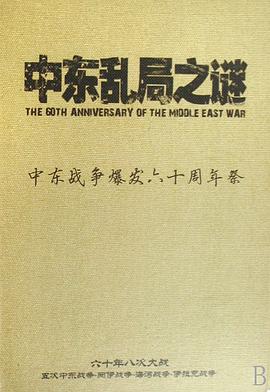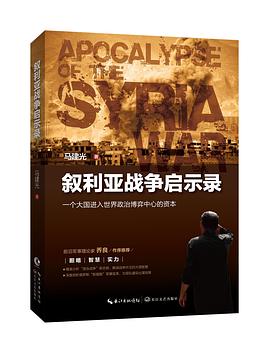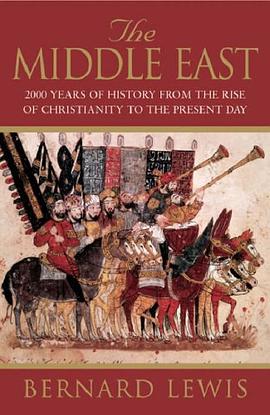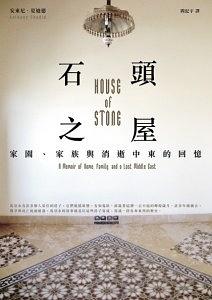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他曾遭到槍擊,被軍隊扣押毆打,最後在採訪途中身亡。
★ 2012美國國家書卷獎非文學類決選
林博文(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 專文推薦
張桂越(周刊巴爾幹總編輯)、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感動推薦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這裡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的傳奇中東戰地記者,重溯家鄉百年動盪歷史
將近一個世紀前,為了躲避戰爭帶來的殺戮、疾病與飢荒,夏迪德的祖父母離鄉背井,輾轉遷徙至美國南方,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則散布世界各個角落。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展開報復攻擊,夏迪德也深入戰區報導。遭到攻擊的平民城鎮之一,便是夏迪德的祖先聚居之地「馬亞永」。隔年他再度回到馬亞永,整修外曾祖父留下的百年石砌大宅。
《石頭之屋》從夏迪德返鄉整修屋子的契機開始,記述他與當地工匠和居民的來往,生動幽默,常令人放聲大笑,不但穿插回溯了一整個家族與地區百多年來的歷史,同時也是當代黎巴嫩及中東地區族群、宗教與文化最鮮明的寫照。他的文字洗鍊抒情,宛如吟唱一首歌,巧妙交織著他個人的經歷、家族的離散、馬亞永的興衰、黎巴嫩傷痕累累的歷史,以及百年前多元包容的燦爛中東。
★ 名人推薦
夏迪德這部回憶錄文字優美,生動記述了一個人逐漸融入中東世界與地中海東岸文化的過程,他曾祖父這幢屋子的房間與迴廊所述說的故事,將跟隨每個讀者許久許久。在《紐約時報》讀過他報導的讀者不只會對他身為作家的能耐感到佩服,他筆下每個人物的生命如何反映了當地揮之不去的不幸也將深印你的腦海。
──安德列.艾席蒙(Andr? Aciman),《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作者
夏迪德寫了一本優美的書,關於一個殘破的地方與一個心碎的人。《石頭之屋》哀淒、痛苦,時而令人放聲大笑。這是一個歷史與療癒的故事,夏迪德的文字如此抒情,像是聆聽一首歌。
──大衛.芬克(David Finkel),《好士兵》(The Good Soldiers)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我立刻就被夏迪德撼動人心的文字擄獲。……如果馬奎斯探索過非小說領域,《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感覺會像馬亞永一樣真實。
──戴夫.卡倫(Dave Cullen),《科倫拜》(Columbine)作者
看到第六頁,我對自己說,如果夏迪德繼續維持這樣的水準,這本書將會是經典。一頁一頁看下去,他真的保持這種水準,寫出了一部毫無疑義的經典。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塞敦》(Zeitoun)、《究竟是什麼》(What is the What)作者
★ 內文試閱
序曲:家園
千年來,阿拉伯語隨著時間慢慢演進,語彙幾乎無所不包,細節可說無微不至。「bayt」直譯是「房子」,但是它的意涵豐富,超出了房舍與牆垣,召喚出人們對於家族與家園的渴望嚮往。放眼中東地區,「bayt」是個神聖的字眼,帝國衰亡、國家覆滅、疆界改易,舊日的忠誠可能消失無蹤,或者一夕易主。然而「bayt」,無論指的是建築物,還是熟悉的根據地,歸根究底,都代表一份永不褪色的認同。
馬亞永位於今日的黎巴嫩。很久以前,伊斯伯.薩瑪拉(Isber Samara)留下一間房子。這間房子從來不曾要求我們佇足或進入,它只是等待著,必要時提供庇蔭。伊斯伯.薩瑪拉把房子留給我們,也就是他的家人,讓我們與過往連結起來,維繫我們的生存,做為許多故事的場景。我曾經花了許多年時間,拼湊伊斯伯的事跡。他年少時白手起家,我喜歡想像他如何生於斯、長於斯。豪蘭(Houran)的原野向遠處延伸,連愛作夢的他也難以理解想像。
在一張歷代相傳的老照片中,伊斯伯的肩膀看似厚實,但已顯出老態,儘管他並沒有機會老成那個樣子。而且他的表情帶有一抹淘氣的味道,感覺相當年輕。與其說伊斯伯英俊,不如說他引人注目,他的臉龐在風吹日曬中磨損,但眼睛依然是漂亮的葉門藍,與周遭景物的閃族棕對比,分外獨特罕見。伊斯伯生養了六名子女,看起來非常不修邊幅,紅棕色的頭髮糾結蓬亂,鬍鬚像一撮粗大蓬鬆的畫筆。他從小就出社會闖蕩,想證明自己的能耐;後來,他也相信自己已經證明。
伊斯伯與家人拍攝這張照片時,年紀大約四十來歲。然而更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後來的伊斯伯:他變成一位父親,雄心壯志不復當年,為了子女生存而將他們送往美國。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想像,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和一代又一代後人,度過跟他一樣變化莫測的人生。他是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預見我們流浪回來,走上龜裂的臺階,打開老房子的門。
伊斯伯傳承了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的好客傳統,他的房子總是歡迎旅人光臨。這幢房子是由岩石與磁磚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完工,周遭種了許多橄欖樹與李樹。它至今矗立在我們的故鄉,那地方的戰爭經常讓時間停止流動;它像一幅水中反射的倒影,在家族成員心中縈繞。我們是一個永遠無法安身立命的家族,成員關係緊密,從數十年前的幾個世代就開始離鄉背井。當我們想到「家」,根源意義或者地方意義的「家」,我們總是想到伊斯伯的房子。
伊斯伯的房子建築在一座小山丘上,洋溢地中海東岸(Levantine)風情,也透顯出他期待渴望的生活型態。它讓人想起一個失落的開放年代,當時鄂圖曼帝國尚未滅亡,各色各樣的人們在共享的土地上遷徙。伊斯伯房子所在的塞瑞爾區(Hayy al-Serail),過去曾是當地最美不勝收的社區,石灰岩建材、尖頂拱門、紅瓦屋頂。這些紅屋瓦是從法國的馬賽進口,在十九世紀初年見證了當地的四通八達與都會時尚。此外它們也像鄂圖曼帝國士紳戴的塔布什帽(tarboosh)一樣,透顯出地中海東岸的風格。塞瑞爾區的士紳們,銀器總是擦得發亮,每日午後必喝咖啡。家族元老,有如一張布滿塵埃的老舊長沙發,拿起繡有姓氏字母的手帕,擦拭著溼黏的眼睛。他們父子世代交替,傳承備受看重的姓氏。然而,伊斯伯的姓氏原本並不特別顯赫。
在伊斯伯所處的地域和時代,白手起家的例子並不常見,但他打響了自己的名號。他所屬的大家族默默無聞,只有「不到二十間房子」。他的家具價格不菲,遠從敘利亞進口,但也是不久之前才成為他的財產。他的房子獨樹一格,原因不只是新穎而已。建造這幢房子的伊斯伯是個作風粗獷的商人,唯有他的妻子芭希雅(Bahija)才能夠讓他不要一直盯著帳簿。這幢房子連結的時代,既蘊含珍貴的文化素養,也曾發生難以想像的悲劇。此外,它彰顯出一個善良但並不完美的人,如何善用自己的一生。伊斯伯建造的房子告訴世人,他摯愛以及賴以維生的事物;也提醒我們,日常生活的所在儘管並不起眼,但卻具備豐富的意涵。進入房子的雙扇門高大寬闊,正適合伊斯伯這樣的人物,他是一個關不住的人。
伊斯伯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兒名叫瑞伊法(Raeefa),生下我的父親。在我成長過程中,關於伊斯伯的回憶讓他死而復生,那些故事讓他變得真實起來,同時也將我的家人傳送到他的世界,一座已從新近出版地圖消失的驛站:傑戴迪特馬亞永(Jedeidet Marjayoun)。我的家人提到故鄉時,一定是稱呼它為傑戴迪特馬亞永,不會只說「傑戴迪特」或者「馬亞永」。我們使用全名,表達敬意,因為這地方是我們的源頭,是我們的家園,是我們存在的根本。
我的祖先定居的馬亞永,曾經是商品貨物的集散地,貿易的路線由基督徒、穆斯林與猶太人開拓經營,三大族群編織出古老中東的圖像。馬亞永是地區交通的門戶,通往地中海濱的城市希登(Sidon)、赫蒙山(Mount Hermon)另一邊的大馬士革、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耶路撒冷、古羅馬城鎮遺址巴亞貝克(Baalbek)。由此可見,馬亞永算是這個地區最具國際色彩的城鎮,它的文化與先進發展鶴立雞群。
然而今日並不時興對小地方的流連忘返,這些小地方與大世界格格不入。的確,馬亞永的光彩逐漸黯淡,而且過程已持續數十年。廣受歡迎的星期五市集,如今難以為繼,過去人們總是盛裝打扮參加,女士穿上來自大馬士革的華服,男士掛上購自美國的懷錶。現在夜裡的馬亞永,只見得到搖曳微弱的燈火,連走投無路的旅人都有可能錯過。來到城裡的廣場(Saha),店鋪的商品滿布塵埃,幾十年來都標明降價求售。店主不再把櫃檯擦得發亮,不再送上雪水釀成的果子露,也不再販賣來自異國的菸草。過去有一位壞脾氣的長老會幫人看病,心情好時還會開藥方,現在早已歇業。馬亞永已經停止觀照外面的世界,也完全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腳步。城裡四處散落著各種碎片,幾十年前的舊報紙,昔人特別留下的古怪物品。當然,如今已沒有公路通過馬亞永;它的影響力曾經遍及敘利亞全境,籠罩埃及西奈半島的大城阿里什(Arish),一路延伸到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的匯流處;相較之下,現在沿著馬亞永最大一條街走上一英里路,它就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
就在這地方,我的家族曾經協助樹立一座十字架,打亂了當地的平靜。我們雖然是馬亞永最早期的基督教徒,但是向來缺乏性情溫和公允的名聲。我們曾經走過這些街道,在開闢的過程中決定它們要通往何方,後來又沿著它們離鄉背井。雖然我們家族仍持續有新生代加入,但在情感方面依舊保持深藏不露(mastourin)的傳統,儘管我們回顧往事有時候還是會熱淚盈眶。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伊斯伯大宅是其中之一。我們稱這類房子為「mahjour」,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遺棄、荒廢、寂寞。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馬亞永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許多人從它們旁邊走過,把這些房子視為朋友。望向一扇又一扇破碎的窗戶,行經的人看到的是閃亮的玻璃,以及玻璃後方發生的事情。人們透過想像看著那些幽暗的房間,除了看見斑駁剝落的牆面、塵埃堆積的地板,還有幾位老友正點亮油燈、燃起煤爐。
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我還是每天都會想起他們。」離去的人留下來的房子四處可見,不再受到人們眷顧。「他們剛開始還會寄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留下的人記得我們失去的人。「我們一覺醒來,發現他們的房子成了空屋。」走進這些破落傾頹的房間,人們會聽到幽靈的聲音以及悔恨,來自仍然記得它們的人們。
閉上雙眼,忘了馬亞永。接下來你將穿過利塔尼河谷(Litani Valley),翻山越嶺,來到傑贊(Jezzine),再前往海岸邊的賽達(Saida)。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鄂圖曼帝國從崩解走向滅亡,一股持續百年的移民潮應運而生,我的阿姨叔伯、祖父母與曾祖父母也隨波逐流。馬亞永地處內陸,當時隸屬於所謂的「大敘利亞」(Greater Syria),阿拉伯文稱之為「bilad al-Sham」,戰爭帶來經年累月的無政府暴力狀態,血腥殺戮是家常便飯,各種疾病猖獗,饑荒情況嚴重;後者是拜英國與法國之賜,兩國強行封鎖地中海岸所有的阿拉伯港口。數以萬計民眾活活餓死,從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到伊斯伯的家園,都無法倖免於難。一項針對一百八十二座村落的可靠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住宅毀於戰火,超過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亡。
這可怕的十年以及後續的衝擊,促使許多村民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從南美洲、西非到澳洲,都是他們的寄居之地;也有一些人來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拉荷馬市與堪薩斯州的威契塔(Wichita)。這段流離的年代結束之後,一九二○年,當歐洲列強瓜分鄂圖曼帝國,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竟然比國內人口還多。
我的檔案櫃中有一個綠色的資料夾,標題寫著「家族紀錄」。裡面有歸化公民與婚姻的證書,美國陸軍發給我祖父的退伍令,一位姑姑為祖母寫的生平事跡,祖父從貝魯特搭乘「拉佐號」(Latso)輪船來到波士頓的紀錄。還有兩份皺巴巴、折成三疊的族譜,涵蓋我的母系與父系祖先,也就是薩瑪拉與夏迪德兩大家族。其中一份家譜上最早的一位先人薩瑪拉.薩瑪拉(Samara Samara)生於一七四○年,後來參與一場歷史性的大流亡,據說是由豪蘭地區(位於今日的敘利亞)的一群女性領導,來到山巒起伏的馬亞永。家譜的其他部分就更為複雜,開枝散葉成兩百多個名字,以英文和阿拉伯文一一仔細記錄。
資料夾裡也有照片,其中一張出現我的外曾叔祖父米克包(Miqbal),臉龐看起來還有點孩子氣,穿著很不合身的西裝外套,翻領上別著一朵碩大的白玫瑰。其他的照片,女士們愁眉苦臉;男士們蓄著翹八字鬍,一簇一簇的頭髮似乎永遠梳不整齊。無論女士男士,都拿出星期日才會穿的考究衣裳,打扮得非常花俏。老米克包開了一家布料服飾店,招牌上寫著「物美價廉」,但是英語翻譯就不是那麼肯定:「賓主互惠」。上面的字體顯然是出自母語人士之手,帶著阿拉伯文的優雅斜度,向左邊傾側,壓倒正經嚴肅、直挺挺的拉丁字母。
吸引我家人移民的美國,遠在馬亞永七千英里之外。儘管山路崎嶇,海道兇險,然而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卻是在剛離開家園的幾英里路,離開那些日後不再熟悉的面容。等到我們抵達紐約、德州、奧克拉荷馬或者任何一個地方時,我們已經失去許許多多事物。美國作家伊莉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寫道:「旅行時的第一個發現,就是自己並不存在。」換言之,你動身時不僅留下其他人,也留下你所知的自己。隨家族姓氏而來的權勢或懲罰消失了;先人胼手胝足換來的名聲,到新國度之後無人知曉;瞭解你生命歷程的人消失了;足以解釋你所犯錯誤的過往緣由消失了;在你抵達新國度的那一天,除了你的姓名之外,一切都會消失,甚至就連姓名都有可能被迫更改。
為了生存,太多的事物必須拋棄。你的感受遭到忽視,因為有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對這些旅人而言,他們還能擁有的就只是生存,以及回憶中的臉孔,直到他們珍藏的照片磨損不堪,甚或四分五裂。儘管我們都無法喚起它的形象,伊斯伯.薩瑪拉的大宅兀自矗立,訴說他的與我們的姓氏。這是一個讓人回顧過往的地方,有如一具船錨,回顧留在那裡的一切。對於我的族人,無論是離散還是團圓,伊斯伯的大宅向他們宣示:記得過去,記得馬亞永,記得你的本來面目。
作者简介
安東尼.夏迪德 Anthony Shadid
1968年生,黎巴嫩裔的美國記者,曾任職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常年派駐中東,報導中東地區事務。由於對伊拉克戰爭的傑出報導,他於2004及2010年兩度獲得普立茲獎國際報導獎項。2002年在約旦河西岸採訪時肩部中彈,甚至傷及脊椎。2011年在利比亞採訪反對格達費軍事獨裁的起義運動中遭到政府軍上銬關押,不斷受到毆打。2012年二月,夏迪德暗中潛入敘利亞報導戰況激烈的反獨裁抗爭,不幸在離境途中氣喘發作身亡。曾出版《先知的遺產:獨裁者、民主人士與伊斯蘭的新政治》、《夜幕低垂:美國戰爭陰影下的伊拉克人民》。
譯者: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讀者文摘》、《哈佛商業評論》、公共電視譯者,現為聯合報影音新聞部國際中心副主任。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揭密:透視賈伯斯驚奇的創新祕訣》、《紙醉金迷哈瓦那》、《別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等書。
目录信息
序曲:家園
第一部:返歸
1 沉默何所知
2 小橄欖樹
3 三隻小鳥
4 最後的紳士
5 黃金
6 早到的收成
7 別告訴鄰居
8 阿布金恩,這樣你滿意了嗎?
9 查亞先生出現
10 最後的呢喃
11 海瑞拉的烏德琴
12 城堡
第二部:家園
13 思鄉
14 羅莎娜灌木叢
15 笨貓
16 廉幕
17 鹽醃米克塔
18 消逝的危機
19 家
20 更糟的時代
21 以聖父之名
22 返家
23 噢,萊拉!
24 我的馬亞永
尾聲
致讀者
親屬關係圖
· · · · · · (收起)
读后感
今年看過最喜歡的書,就是《石頭之屋》了。作者夏迪德在被大廈將傾的利比亞政府拘捕期間,遭受監禁、毆打,以及死亡威脅。 高深莫測、無可無不可的利比亞官員對他吟詠起葉慈的詩: Thouse that I fight I do not hate, thouse that I guard I do not love. 這是一位即將覆亡國...
评分今年看過最喜歡的書,就是《石頭之屋》了。作者夏迪德在被大廈將傾的利比亞政府拘捕期間,遭受監禁、毆打,以及死亡威脅。 高深莫測、無可無不可的利比亞官員對他吟詠起葉慈的詩: Thouse that I fight I do not hate, thouse that I guard I do not love. 這是一位即將覆亡國...
评分今年看過最喜歡的書,就是《石頭之屋》了。作者夏迪德在被大廈將傾的利比亞政府拘捕期間,遭受監禁、毆打,以及死亡威脅。 高深莫測、無可無不可的利比亞官員對他吟詠起葉慈的詩: Thouse that I fight I do not hate, thouse that I guard I do not love. 這是一位即將覆亡國...
评分今年看過最喜歡的書,就是《石頭之屋》了。作者夏迪德在被大廈將傾的利比亞政府拘捕期間,遭受監禁、毆打,以及死亡威脅。 高深莫測、無可無不可的利比亞官員對他吟詠起葉慈的詩: Thouse that I fight I do not hate, thouse that I guard I do not love. 這是一位即將覆亡國...
评分今年看過最喜歡的書,就是《石頭之屋》了。作者夏迪德在被大廈將傾的利比亞政府拘捕期間,遭受監禁、毆打,以及死亡威脅。 高深莫測、無可無不可的利比亞官員對他吟詠起葉慈的詩: Thouse that I fight I do not hate, thouse that I guard I do not love. 這是一位即將覆亡國...
用户评价
“石頭之屋”,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仿佛握在手中的不是一本薄薄的书,而是触手可及的岁月和过往。它不像那些华丽而浮夸的书名,反而显得质朴而内敛,却又饱含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吸引力。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各种画面:可能是古老村落里饱经风霜的石砌小屋,也可能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隐士居所,又或者,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某种坚不可摧的情感或信念。我好奇,作者究竟是如何解读“石頭之屋”这个概念的?它是在描绘一个物理空间,还是在隐喻一种心理状态?它是在讲述一段历史,还是在探讨一种人生?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进入一个充满质感和温度的世界,在那里,我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能听到岁月的低语,能体会到生命中最本质的力量。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种宁静而深刻的阅读体验,让我在这片“石頭”筑起的“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与思考。
评分“石頭之屋”——一个多么引人遐思的名字!它像一块沉默的巨石,散落在我的书架上,散发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我被它深深吸引,不仅仅是因为封面上那粗犷而写意的笔触,更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所蕴含的可能性。它让我想象着高耸的山峦,坚固的堡垒,或是深邃的洞穴,每一个都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秘密。我开始好奇,这座“石頭之屋”究竟是什么样的?它隐藏着怎样的过往,又将带领我走向怎样的未知?是关于历史的沉淀,还是关于人性的拷问?是关于孤独的守望,还是关于坚韧的抗争?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扉页,让作者的文字为我一一揭晓。这个名字,它像一个引子,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探索和发现的渴望。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沉浸其中,与书中人物一同经历风雨,感受喜怒哀乐。这座“石頭之屋”,它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书名,更是一种象征,一种对未知世界的邀约,一种对心灵的洗礼。我期待着它能够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让我在这文字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港湾,或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感觉,绝非仅仅是书的标题那么简单。它在我脑海里构建了一个宏大而古老的意象,仿佛是某个被遗忘的角落,藏匿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它让我联想到坚韧,联想到永恒,联想到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智慧与情感。我无法想象,这座“石頭之屋”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是矗立于荒野之上,默默承受风雨的洗礼;还是深埋于地下,见证着无数次的潮起潮落?我期待着,作者能够用他的文字,为我勾勒出这座屋子的轮廓,让我看到它曾经的辉煌,或者,是它如今的寂寥。更重要的是,我期待着,能够通过这座“石頭之屋”,去了解那些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受,让我能够与书中人物产生深刻的共鸣,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意义。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我内心层层涟漪的思绪。它没有矫揉造作的华丽,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一种与生俱来的厚重感。它让我想象着那些古老而坚固的建筑,它们沐浴着风雨,见证着沧桑,却依然巍然屹立。我开始猜想,这座“石頭之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是关于坚韧不拔的意志,还是关于深沉的情感?是关于历史的沉淀,还是关于现实的写照?我期待着,作者能够用他精妙的文字,为我一点点揭开这座“石頭之屋”的面纱,让我看到它最真实的面貌。我渴望着,它能带领我进入一个充满质感的世界,在那里,我能感受到时间的流淌,能体会到生命的顽强,能领悟到那些在看似平凡事物中隐藏的深刻意义。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的对象,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盘旋,仿佛一首古老而悠扬的旋律,低沉而有力。它没有直接的点明内容,却勾勒出一种坚实、沉静、又充满故事的意象。我立刻联想到那些历经风霜的古老建筑,它们沉默地矗立在那里,却仿佛承载了无数的岁月和回忆。我开始好奇,这座“石頭之屋”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会是一个物理空间,一个具体的建筑,还是一个精神的象征,一种内心的寄托?它会讲述一个关于家族传承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个人坚守的史诗?它会描绘一段关于爱情的缠绵,还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永恒?我期待着,作者能够用他独特的视角,为我描绘出这座“石頭之屋”的模样,让我能够触摸到它的质感,感受到它的温度,听到它在风中低语的故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深刻的思考,让我重新审视生命中的坚韧与温暖,让我在那冰冷的石头背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力量。
评分我必须承认,初见“石頭之屋”这个名字时,我的内心是涌动着一丝犹豫的。它听起来如此厚重,如此坚硬,似乎预示着一种沉闷和压抑。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冰冷、无情的岩石,是无法撼动的阻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我曾一度担心,这本书是否会是一部充斥着悲伤、绝望,或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然而,我又不甘心就这样被名字所吓退,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最深刻的意义往往隐藏在最朴实甚至有些粗糙的外表之下。“石頭之屋”,它或许象征着一种根基,一种家族的传承,一种文化的积淀,或者,是一种心灵的避难所。或许,在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石头背后,隐藏着的是最柔软的情感,最炽热的渴望,最动人的故事。这种对未知内容的猜想,反而勾起了我更强烈的好奇心。我开始思考,作者究竟是如何将“石頭”与“屋”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意象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在描绘一个物理空间,还是在隐喻一种精神状态?它是在歌颂坚韧,还是在反思固执?我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准备迎接这本书可能带给我的震撼,无论是惊喜还是挑战。
评分“石頭之屋”,多么有力量的一个名字!它立刻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种坚固、朴实、却又饱含历史感的画面。我无法想象它会是什么样的故事,但我可以肯定,它一定不是那种轻飘飘、转瞬即逝的浮华之作。我期待着,它能给我带来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仿佛置身于那座“石頭之屋”之中,感受它独特的氛围。或许,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家族传承的故事,一座古老的石屋,见证了代代人的悲欢离合;又或许,它描绘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如石头般顽强地抵御着生活的风雨;也可能,它是一个关于孤独与守望的隐喻,在那冰冷的石头建筑中,隐藏着一颗火热的心。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石頭”与“屋”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期待着,它能够带给我一种深刻的思考,让我反思生命的意义,感受历史的厚重,体验人性的复杂。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盘旋了许久,它像一首古老的歌谣,低沉而悠扬,带着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回响。我开始在我的想象中构建这座屋子的模样。它或许坐落在荒凉的山野,被风雨侵蚀,却依然巍然屹立;它或许是家族世代相传的宅邸,承载着无数人的悲欢离合;它或许是一个精神的象征,代表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永恒不变的信念。我期待着,作者笔下的“石頭之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而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故事的空间。我希望它能够带领我走进一个别样的世界,让我感受那些与现代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和人生哲学。我好奇,住在“石頭之屋”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又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他们是否拥有着比我们更纯粹、更深刻的情感?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让我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沉浸在一个充满诗意和哲思的篇章里,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充满了神秘感和厚重感,让我心生向往。我无法猜测其中具体的情节,但它唤起了我对那些古老、坚固、却又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建筑的想象。它让我联想到的是那些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东西,是坚韧、是传承、是守望。我好奇,这座“石頭之屋”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可能是物理上的建筑,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寄托。它会讲述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还是一段关于个人奋斗的史诗?它会描绘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还是会揭示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我期待着,作者能够用他独特的笔触,为我描绘出这座“石頭之屋”的模样,让我能够感受到它的质感,它的温度,以及它所蕴含的生命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深刻的共鸣,让我在这冰冷的石头背后,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力量,让我在这静默的屋子里,听到岁月的低语。
评分“石頭之屋”,这个名字,着实像一个谜语,又像一扇紧闭的门,让我充满了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我无法确定它究竟会带我走向何方,但名字本身已经为我描绘出了一幅充满想象空间的画面。它让我联想到古老的传说,那些关于守护、关于传承的故事,或许这座“石頭之屋”便是这一切的载体。又或者,它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生命的坚韧,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即使面对风雨侵袭,也能岿然不动。我揣测着,作者会如何运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来构建他的故事。是会将它描绘成一个具体的建筑,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场所,还是会将其作为一种精神的隐喻,一种内心的寄托?我期待着,它能够带给我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份“石頭”般的厚重与“屋”内的温暖。我渴望着,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共鸣,找到慰藉,找到那些隐藏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之处。
评分一座小镇,一所大宅,一个消逝的宽容世代。
评分翻修好的家族房子将永远矗立在马亚永,但永远都回不去了。只是框住了一块土地和过去的回忆,对于发展还需要磨灭共性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回去了。
评分翻修好的家族房子将永远矗立在马亚永,但永远都回不去了。只是框住了一块土地和过去的回忆,对于发展还需要磨灭共性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回去了。
评分翻修好的家族房子将永远矗立在马亚永,但永远都回不去了。只是框住了一块土地和过去的回忆,对于发展还需要磨灭共性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回去了。
评分一座小镇,一所大宅,一个消逝的宽容世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