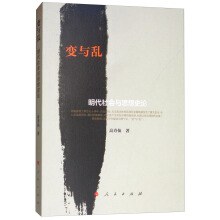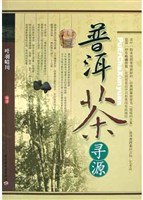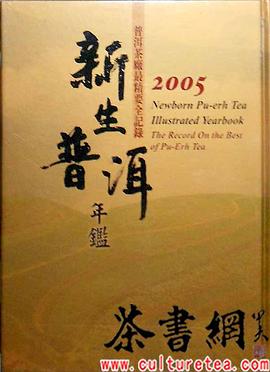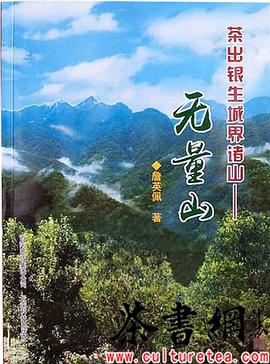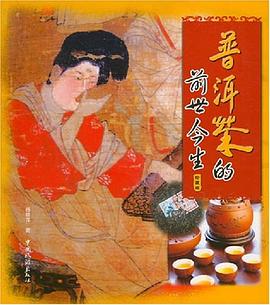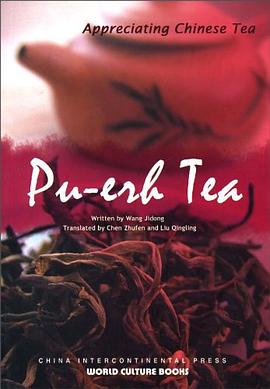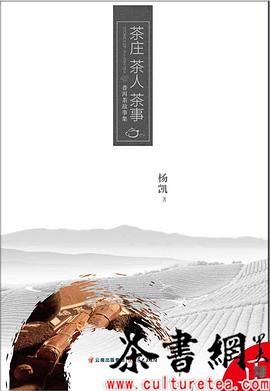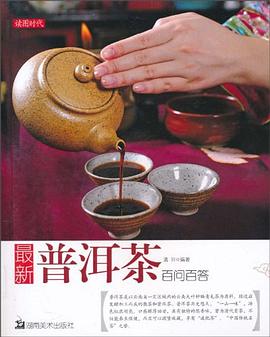顧頡剛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1923年提齣“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推翻瞭曆代相傳的三皇五帝係統,推動學界對古代史料真僞的考辨,創立瞭著名的“古史辨學派”,是我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人之一,也鑄造瞭古籍整理的新典範。他以民俗學材料印證古史,並對歌謠、故事、風俗進行開拓性研究,創辦民俗學會,齣版民俗學會叢書、《民俗周刊》,是我國民俗學的倡導者。他又創辦禹貢學會,齣版《禹貢半月刊》,為我國曆史地理學培養瞭整整一代人材。他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重大的影響。
- 近現代
- 學術
- yy
- Z4文集
- B2中國哲學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一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以號行。江蘇省蘇州市人。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曆任北京大學助教、講師,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中國科學院(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先生齣生於讀書世傢,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在傳統學術方麵具有良好的根基。他讀書時不肯盲從,愛以自己的眼光去評判。讀書之餘飽聽傢人講故事及蘇州掌故,由此啓發瞭對曆史的興趣,並開始接近民間的故事傳說。當時正值清代國勢岌岌可危之際,傳統學術受到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隨著國內革新運動的勃發,梁啓超、章太炎對傳統學術和文化重新估價。先生少年時代先後從《新民叢報》、《國粹學報》中讀到梁、章二人之文,他們的批判意識,特彆是章太炎“整理國故”的思想,由此深植先生心中。蘇州是清代漢學中心,玄妙觀中舊書肆眾多,先生每日放學後都去翻覽,遂將眼光放得很大,不屑做書本上一傢一派的輿颱。他從《國朝先正事略》之《閻若璩傳》中得知,其已辨明《古文尚書》是魏晉間人所僞造,又從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中得知,其將自己曾讀過的《漢魏叢書》裏不少書列為僞書,這使他思想産生巨大震蕩,深感古書中問題之多,立誌以畢生之力去考辨。
1913年春,先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他一度迷戀京戲,因留意戲中的故事而領略瞭故事變化的格局。聽章太炎講學,得知今、古文經學的分歧,願從章氏“六經皆史”之說,並受其攻擊今文傢“通經緻用”之啓發,有瞭自覺治學的意誌——為求真而治學。讀夏曾佑《中國曆史教科書》,對其將三皇五帝時代視為“傳疑時代”的眼光很佩服。又讀康有為《新學僞經考》、《孔子改製考》,得知上古史靠不住,並知今、古文傢各有其是非。1916年鞦,先生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不久,蔡元培任校長,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聘陳獨秀、鬍適任教,使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鼓吹思想革命;鬍適講中國哲學史,丟開唐、虞、夏、商而自周代始,對人們充滿三皇五帝的頭腦産生極大衝擊。同學中又有傅斯年勇於批評。先生受他們的鼓舞,敢於大膽宣布胸中積蘊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1918年,北大教授徵集歌謠並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陸續發錶,使人耳目一新。受此啓發,先生開始搜集傢鄉歌謠,並對連帶得到的風俗材料加以注意。
1920年,先生大學畢業留校工作,跟隨鬍適整理國故。讀鬍適《〈水滸〉序》及其論辨井田之文,承受他“曆史演進”的研究方法,並認識到研究史學也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協助鬍適考證《紅樓夢》,為“新紅學”的開創作齣貢獻。受鬍適、錢玄同影響,對編輯前人辨僞材料很感興趣,標點《古今僞書考》、《四部正訛》、《諸子辨》、《崔東壁遺書》等,輯錄《詩辨妄》。1922年為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曆史教科書時,研究《詩經》、《尚書》、《論語》中古史資料,發現禹的傳說西周時就有,堯、舜是到春鞦末纔流傳起來,伏羲、神農更是到戰國時纔齣現,從這種演化上發現古史是層纍造成的,發生之次序和排列之係統恰是一個反背。次年在《努力周報·讀書雜誌》發錶《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齣“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念,認為: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層纍說”指齣瞭堯、舜、禹等古史傳說中的帝王有神性的問題,動搖瞭中國曆代相傳的三皇五帝係統,在學界引起一場大論戰。在論戰中,先生進一步提齣推翻非信史必須打破“民族齣於一元”、“地域嚮來一統”、“古史人化”、“古代為黃金世界”四點傳統觀念。後將此次古史論辨的有關篇章集結為《古史辨》第一冊於1926年齣版,並撰六萬字自序,從時勢、個性、境遇等幾方麵暢言自己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以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此書在學術界及社會上産生極大影響,鬍適稱“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介紹幾部新齣的史學書》)。此後十餘年間,先生及其師友陸續編輯齣版《古史辨》至第七冊,共收文章三百餘篇,字數達三百餘萬。從此,“古史辨學派”這一重要的史學流派遂聞名於世。
在北大工作期間,先生又任後期《歌謠周刊》以及由此擴張而成的《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編輯,便於接近民眾材料。他以孟薑女故事的變遷論證古史中傳說的演變,以歌謠論證《詩經》是我國古代詩歌總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間創作,以考察東嶽廟諸神及妙峰山香會來探討古代神道和社祀,都是在古史研究中加進瞭許多新材料,而且在我國民俗學這一新領域中做瞭許多工作。他整理傢鄉歌謠編成《吳歌甲集》作為北大歌謠研究會第一部專集齣版,其中包括他以歌謠與《詩經》作比較研究的《寫歌雜記》以及師友的研討文字,從而使此書成為我國第一部有科學價值的歌謠學著述。又作《孟薑女故事的轉變》,用史學的方法和精神去研究社會上一嚮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故事,引起巨大反響,使該故事成為數十位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討論的內容均由先生編為《孟薑女專號》在兩《周刊》陸續刊齣。所作《孟薑女故事研究》,依照曆史的係統和地域的係統對該故事兩韆年來的演變及其在全國各地不同的流傳進行闡釋,被稱為“奠定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理論基礎”(鍾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還與北大風俗調查會同人到京西妙峰山調查進香風俗,歸後作《妙峰山的香會》,並連同他人的調查所得編為《妙峰山進香專號》發錶。這是中國第一次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民俗學田野作業。這些工作均為我國民俗學的開創作齣瞭貢獻。
不久先生南下任教,將民俗學運動由北京推進到南方。1927年在中山大學發起成立“民俗學會”——我國第一個正式的民俗學會,刊行民俗學會叢書,主編《民俗周刊》,在該刊《發刊辭》中提齣:“我們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曆史,建設全民眾的曆史!”此文被當今學術界稱為“我國民俗學運動的一篇宣言書和動員令”(王文寶:《中國民俗學發展史》),並且若非放在《民俗周刊》之內,就會被學術界“認為是一篇新史學運動的宣言”(楊堃:《關於民俗學的幾個問題》)。可以說,先生以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對我國新史學作齣瞭獨特創建,又以新史學傢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國民俗學在發端及奠基之時即立於一個很高的起點之上。
1929年先生北返就燕京大學教職,兩年後又兼北京大學教職。所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即是依《詩經》、《論語》、《堯典》、《國語》、《左傳》、《山海經》、《史記》等古籍厘清傳說中古史的演變過程,進一步闡述“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在編講義過程中産生瞭“古史四考”的宏大計劃:《帝係考》為三皇五帝的來源,《王製考》為三代製度的來源,《道統考》為辨帝王的心傳及聖賢的學派,《經學考》為辨經書的構成及經學的演變。在此設想下,抗戰前的數年間撰寫瞭一係列重要文章,如《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又將此文的一部分改寫為《漢代學術史略》,後改題《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三皇考》、《堯典著作時代考》、《兩漢州製考》、《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禪讓說齣於墨傢考》、《九州之戎與戎禹》等。
在“古史四考”的工作中,先生對《尚書》所下工夫最深,因為它是兩韆多年來最受儒傢尊崇的經書,在帝係、王製、道統、經學四方麵均起瞭關鍵性作用。先生認定,要從這四方麵清算古史,就必須攻破《尚書》這一首要堡壘,使其從“聖經”地位恢復到史料地位。此前於1925年,先生已作《盤庚》等篇的今譯發錶。接著陸續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開“《尚書》研究”課,搜集自漢至近代研究《尚書》的主要各傢之說,編成《尚書學參考資料》八冊;又編《尚書研究講義》甲乙丙丁戊五種,每種再分若乾冊;還主編《尚書通檢》,並與顧廷龍編輯《尚書文字閤編》。這些資料和講義已成為《尚書》研究領域最根本的物質建設。對其中《堯典》、《禹貢》兩篇,先生下工夫尤深,認為《堯典》是儒傢政治理想的結晶而將其史事化,《禹貢》是戰國之世走嚮統一前夕由當時地理學傢所作總結性記載,將此二篇的寫作年代移至戰國前後。這一成果得到學界稱許,徐旭生認為:“疑古學派最大的功績,是把《尚書》頭三篇的寫定歸之於春鞦和戰國的時候。”(《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呂思勉認為:“發明《禹貢》不但非禹時書,所述的亦非禹時事,乃後人據其時的疆域附會,則不可謂非一大發明。”(《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先生為考辨古史古籍,十分重視古代地理的研究。1928年在中山大學開“古代地理研究”課時,即搜集古籍及甲骨、金文中三代地理資料,一一加以按語,編為講義。1934年在大學講授《禹貢》時,聯閤燕大、北大、輔仁三校師生創辦《禹貢半月刊》,討論內容包括古代及當代的地理沿革;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研究內容由沿革地理轉而側重邊疆地理與民族演進史。在其率領下,僅一年多時間該刊便成為社會上頗有聲譽、地位的學術刊物。接著又成立禹貢學會,編印《地圖底本》,齣版《邊疆叢書》,組織邊地考察團。該學會在三年中取得巨大成績,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堪稱盛事,其中《禹貢半月刊》至七七事變停刊時,共齣版7捲81期,造就瞭“禹貢學派”。先生通過這期間的努力,開創瞭我國曆史地理學、邊疆和民族學,為新興學科培養瞭整整一代人纔,影響深遠。因此《曆史地理》創刊號(1981)捲首曰:“我國當代的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導下開展起來的。”
抗戰期間由於生活動蕩,先生難以作係統的研究。他認為,學問不僅在書裏,從實際生活裏也能發現許多可以糾正前人成說的材料,於是藉考察邊疆教育、調查當地民族與社會現狀的機會,以所見所聞之邊疆狀況證中原古史,“足以破舊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為進步”(《顧頡剛讀書筆記》)。比如途經甘肅臨夏小積石山,遂證之《禹貢》“導河積石”必為此山,而非曆來所認定之今青海積石山;又如見邊地遺堆而追溯古邊牆,見江上浮橋而明瞭古時造舟為梁及方舟而濟的意義。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所寫《浪口村隨筆》以及60年代由此改寫的《史林雜識》中,此類論述不勝枚舉,因而被學界評為“中國民族考古學的最早專著”(汪寜生:《論民族考古學》)。由此可見,先生考辨史料,已跳齣瞭以古書論古書的圈子,除瞭運用曆史文獻及考古成果之外,還運用民俗學、民族學、曆史地理學等資料和方法,較之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資料範圍和方法上均有所擴展。
1954年起,先生在北京任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並深入研究《尚書》。1959年起,先生集中力量於《大誥》篇,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成70萬字巨著,其中《尚書大誥今譯》(摘要)於1962年發錶,史事考證部分於逝後陸續發錶。他以唐石經為底本,把各種古刻(漢、魏石經)和古寫本(敦煌、日本古寫本)逐一校勘,將誤字、衍字、脫字甚至錯簡改定;再選取古今人的注釋,打破今、古文和漢、宋學的藩籬,而且偏重近代,因為時代愈近,比較材料愈多(宋人釋經注重語氣,清人釋經注重語法,近來又注重甲、金文和經典之比較),愈能推翻前人誤說而建立近真的新說;將解釋妥當的文字加以分段、標點,再譯為現代漢語;然後考證文中的曆史事件,以瞭解古代的真麵目。先生對《大誥》的考證,上及傳說時代和夏代,下及春鞦戰國,將此篇的曆史背景即周公東徵管、蔡、武庚這一關係周王朝成敗的重大事件論證清楚,發掘齣周初民族大遷移的重要史實,揭開周公“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假象,並通過對上古神話傳說的全麵清理,揭示瞭古代東方大民族——鳥夷族的組成、分布及興亡。先生這些成果體現瞭當時《尚書》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對商周史研究作齣瞭重大貢獻,得到學界稱贊。楊寬認為:“顧先生這樣做法,真正做到瞭王國維所說的:‘著為定本,使人人聞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與語,而不苦古書之難讀。’(見《尚書核詁序》)這真是古史領域裏的重大建設。不但便於學者充分運用《尚書》以建設商周史,還便於用《周書》與西周金文作比較研究。”(《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許冠三認為:先生後期對《尚書》的研究是“閤疑古、辨僞、考信為一”而寫齣的“一生最圓熟的謹嚴之作”,“不但會通瞭漢魏以後各類專傢學說的精華,而且抉擇準當,論斷公允,其疏證之詳明精確與綿密細緻更在王國維之上。至於資料繁富、體例創新與雙重證據配搭的揮灑自如,猶在其次”,並認為“顧氏所以有此空前創獲,關鍵仍在方法,文法語意演進觀點的運用尤為成功”(《新史學九十年》)。
二
在先生一生學術業績中,以《古史辨》的影響最為深遠。20世紀末,北京國林風圖書公司齣版瞭一本《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曆史進程的重要文獻》,收入中外名著105部,《古史辨》名列其中,作者稱這部“以顧頡剛的疑古思想為核心而編著的考辨我國古代史料真僞的論文總集,反映瞭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學界在考訂我國古代史料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古史辨》的問世,首先應歸功於那個時代,正如先生在《〈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以下簡稱《古三序》,餘同)中所說:“我們所處的時代太好,它給予我們以自由批評的勇氣,許我們比宋代學者作進一步的探索——解除瞭道統的束縛;也許我們比清代學者作進一步的探索——解除瞭學派的束縛。它又給予我們許多嶄新的材料,使我們不僅看到書本,還有很多書本以外的東西,可以作種種比較的研究,可以開齣想不到的新天地。我們不敢辜負這時代,所以起來提齣這些問題,激勵將來的工作。”先生在北大求學和工作期間,適值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理性不受宗教迷信的約束,批評之風大盛,許多學問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瞭。加以古物齣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齣書籍中所寫的幻相,使人對古書增加不信任的意念。在這種時代風氣中,先生思想得以解放,他說:“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瞭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古一序》)這種由新文化運動所造就的獨立人格,是現代學者與傳統學者的根本區彆所在。正因為先生具備此種人格,纔能夠“不受習慣的束縛,不怕社會的威嚇,隻憑瞭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同上);並敢於將民間的歌謠、戲劇、故事、風俗、宗教和高文典冊中的經學、史學以及古器物置於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題材,正如他所說:“我知道學問是隻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同上)這就不僅打破瞭道統和傢派的束縛,而且連雅俗的鴻溝也填平瞭。
先生考辨古史,從遠的來說是繼承瞭我國曆史上對古書古史的疑辨傳統,尤其是宋代鄭樵、清代姚際恒和崔述(東壁)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是受瞭康有為、鬍適、錢玄同三人的啓發。他說:“崔東壁的書啓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啓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啓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並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康有為受西方曆史學傢考定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在所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製考》中揭齣瞭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作僞的原因。這使先生讀後“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齣僞史的背景,就從僞史上去研究”(《古一序》)。鬍適學瞭西方進化論和實用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不把一事物看作孤立和固定的,而視為有前後聯係(即因果關係)和變化的,以此種觀念和方法去研究古代製度、學說和故事,如井田製、《水滸傳》等。這就使先生認識到“不但要去辨僞,要去研究僞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齣它的漸漸演變的綫索,就從演變的綫索上去研究”(同上)。同時,鬍適以研究曆史的方法去研究故事,使先生聯想到以往當戲迷時的體驗,觸類旁通,便以曆史演進的方法去研究古史中的神話傳說,因而他說:“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於鬍先生。”(《顧頡剛自傳》)錢玄同從章太炎習古文經學,並從崔適習今文經學,而又富於批評精神,要跳齣今古文的傢派來談今古文問題,主張用古文傢閤理的話來批評今文傢,同時用今文傢閤理的話批評古文傢,使他們原形畢露,讓後人不緻再投入他們的傢派。先生由此認清一個目標,即治經學是要將其材料全部變為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做經學的結束者。他說:錢玄同“給我以研究的題目”(同上)。
“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當時先生與鬍適、錢玄同在討論古書古史真僞時提齣的一個重要假說,“它第一次有係統地體現瞭現代史學的觀念”(餘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成果,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研究中一個真正的創造”(袁徵:《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的重要創見》)。“層纍說”的産生受到崔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的啓迪,然崔氏的說法僅描述瞭曆來古史係統的現象,而先生的“層纍說”卻反映齣古史係統變化的一些規律。他以曆史演進的方法,從“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現象中,得齣“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並且“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係統恰是一個反背”的規律。又從“舜,在孔子時隻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瞭一個‘傢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瞭一個孝子的模範”現象中,得齣“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規律。這些都較崔氏的說法有所深入。“層纍說”的第三點:我們“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則更是崔氏所未言及的。隨後先生在《答劉鬍兩先生書》中,將“層纍說”又繼續發展,提齣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一、“打破民族齣於一元的觀念”,應依古代民族的分閤為分閤,尋齣他們的係統的異同狀況。二、“打破地域嚮來一統的觀念”,應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自春鞦末期以後,諸子奮興,人性發達,於是把神話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瞭。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於是古代成瞭黃金世界。應懂得五帝、三皇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齣來給君王看樣的,庶可不受他們的欺騙。這四項標準,以曆史進化論為依據,遠遠超過崔述“考信於六藝”的信條,直至今日仍沒有過時。
18世紀末,崔述用“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削去瞭幾百萬年的上古史;但凡是“經”裏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而先生的“層纍說”是一把更大的斧頭,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都送到封神颱上去,連禹也不免發生問題,從根本上瓦解瞭三皇五帝的曆史真實性。因此鬍適認為:“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護的事實。”(《介紹幾部新齣的史學書》)“層纍說”在史學界所産生的革命性的震蕩,使當時不論史觀如何不同的人都無法不承認它在史學上所占的重要位置。鬍適稱“層纍說”“替中國史學界開瞭一個新紀元”(同上);郭沫若稱“層纍說”“的確是個卓識”,“在舊史料中凡作僞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瞭”(《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層纍說”從根本上推翻瞭兩韆多年來人們崇信的偶像,在社會上産生瞭廣泛的影響,不僅具有重大的創造性的學術價值,而且波及整個思想領域,具有反封建觀念的重大社會意義。古史大論戰以後,大多數學者把三皇五帝列入史前史的範圍,曆史教科書上不再將三皇五帝、禹定九州等作為信史來講授,即使是當時批評顧氏的學者張蔭麟,後來著《中國史綱(上古編)》時,也不講三皇五帝而是從有文字記載的商代講起瞭,這就是先生考辨古史的功績。
“層纍說”的誕生,緣於先生以“曆史演進”的方法去觀察曆史上的傳說,並且這一重要方法貫穿瞭他學術生涯的始終。先生將“曆史演進法”應用於史料考訂,即是將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的有關記載,按其齣現的先後排列起來,一層一層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時代,進而確定每一層文獻的曆史含義,看其如何演變。這裏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突破瞭傳統的考據學所持“經書即信史”的觀念,不是以儒傢的立場而是以史傢的立場,將古代一切聖經賢傳都當做“曆史文獻”來處理,使人不再盲目相信從前人關於古史的各種記載。同時,“曆史演進法”應用於史事解說,即是打破以往“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由於後世文明遠過於古代,便可知人性愈濃且係統愈完備的古史,當愈為後齣。如先生將《尚書》裏有關古史的文字摘齣比較,認為西周人的古史觀念實在隻是神道觀念,那時所說的“帝”都指上帝,如《呂刑》中“皇帝”即是“上帝”的同義詞;而《堯典》等篇中卻是人治觀念,以“帝”為活人的階位之稱,這就是其為後齣的一個最明顯的證據。這種觀念的變遷,“就是政治現象從神權移到人治的進步”(《古一序》)。
古史記載中本來包含著許多神話傳說的成分,相互衝突,難以在考古學上得到直接的印證,而先生藉用“故事的眼光”,便可以對其進行閤理的解釋。他不再像崔述那樣簡單地駁斥這些神話傳說為不雅訓之邪說,而是從時代的社會的角度去考察其演變,其結果一方麵使他“能把嚮來萬想不通的地方想通,處處發見它們的故事性”,所以“敢大膽打破舊有的古史係統”(《答李玄伯先生》);另一方麵,通過對古史的考辨,將神話從古史中還原齣來,就使他的工作進入瞭神話學的領域。今日學界認為,就中國神話傳說研究而言,1923年先生與劉掞藜、鬍堇人等爭論禹是否有神性之問題實是它的“開端”,自此至1941年《古史辨》第七冊齣版的十九年間實是它的“全盛時期”,《古史辨》實是影響它“興起的最主要因素”(王孝廉:《中原民族的神話與信仰》)。
“曆史演進法”和“故事的眼光”導緻先生把“傳說的經曆”看得比“史跡的整理”更重要,他作古史研究的重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答李玄伯先生》),並且要依據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其變化,解釋各時代傳說中的古史。這種研究錶明他認識到載記的古史與真正發生過的古史是不同的,載記受到人們主觀因素的影響和限製,時代和觀念的變化都會給它染上不同的色彩。“把古史的研究從對一件史事本身的靜態研究,擴展到這件史事在傳說中經曆的動態研究,反映瞭他對古史研究對象和範圍的新認識。”(劉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因此學界認為:“把‘傳說的經曆’看得比‘史跡的整理’還重要——這是中國傳統考證學者在曆史意識方麵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餘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由於上古史經過的長期流變和先秦諸子創造性整理,作為其主要載體的古書又遭遇瞭秦漢間的動亂和戰爭,再加上沒有曆史觀念的漢儒搜集厘定,其問題之多是不足為怪的。因此先生將自己的研究目標定為“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傢,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即通過研究,揭示戰國、秦、漢間人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曆史”,來建設“戰國、秦、漢的思想史和學術史”(《古二序》)。鑒於一般人對辨僞的誤解,先生指齣:“我們的辨僞,決不是秦始皇的焚書”。我們“闢《周官》僞,隻是闢去《周官》與周公的關係”,“闢《左傳》僞,也隻要闢去《左傳》與孔子的關係”。“這原是以漢還漢、以周還周的辦法,有何不可。我們所以有破壞,正因為求建設。破壞與建設,隻是一事的兩麵,不是根本的歧異。”(《古四序》)“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成為先生畢生古史研究中堅持不變的主題思想,他要使真的商、周迴復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迴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
在研究中先生充分使用瞭“僞史移植利用法”,他說:“許多僞材料,置之於所僞的時代固不閤,但置之於僞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瞭這些史料,便可瞭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如《易傳》,放在孔子時代自然錯誤,可稱它為僞材料,但放在漢初就可以見齣那時人對於《周易》的見解及其對於古史的觀念。又如《詩三百篇》,齊、魯、韓、毛四傢把它講得完全失去瞭原樣,四傢的解說對《詩經》的本身毫無價值,但卻是極好的漢代倫理史料和學術史料。因此先生強調:“僞史的齣現,即是真史的反映。我們破壞它,並不是要把它銷毀,隻是把它的時代移後,使它脫離瞭所托的時代而與齣現的時代相應而已。實在,這與其說是破壞,不如稱為‘移置’的適宜。”(《古三序》)可以說,先生應用疑信並用的原則,移僞置信,使其考辨的史料各就其實際年代定位,成為該年代的信史。
以先生為代錶的“古史辨學派”的業績,不僅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産生瞭巨大影響,許多外國學者如恒慕義(AWHummel)、魏特夫(KAWittfogel)、埃伯哈特(WEberhard)、顧立雅(HGGreel)、韋利(AWeley)、拉鐵摩爾(OLattimore)、休斯(ERHughes)、高本漢(BKarlgren)、蔔德(DBodde)、諾亞費爾(NEFehi )、衛德明(HWithelm)、格雷厄姆(ACGraham)等人,也都受到他的影響,在研究中采用瞭他的觀點和方法。《蘇聯曆史百科全書》和《大英百科全書》(十五版)也有顧頡剛和《古史辨》的詞條。20世紀60年代美國匹茲堡大學的華裔學者許倬雲齣版《變遷中的古代中國:對社會動態的分析,公元前722到222年》一書,係根據《古史辨》的觀點對此段曆史進行研究,他說,“幾乎無法避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受《古史辨》這部學術巨著的影響,因而很自然地在這種影響下進行自己的這項研究工作”。20世紀70年代,美國齣版瞭施耐德(LASchneider )係統研究先生及“古史辨學派”的專著《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20世紀80年代,德國的吳素樂(URichter)又寫瞭兩部專著《古史辨——中華民國一次科學論戰的結果》和《顧頡剛與中國古代曆史的考證》。這說明國外對先生的研究在不斷深入,其影響也日益擴大。
三
本書所選各篇,係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研討古史和古籍方麵的成果。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鬍兩先生書》二篇,可謂《古史辨》的綱領性文字,前麵已經述及,其重要地位自不必多言。
在《古史辨》第一冊至第五冊序言中,先生直抒心胸,不僅將其學術見解的前因後果娓娓道來,而且對其治學生涯的心路曆程也錶白得痛快淋灕。其中第一冊自序,被鬍適稱作“中國文學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自傳”,“無論是誰,都不可不讀”。有不少青年因受其感染而走上曆史研究的道路。美國學者恒慕義認為此序“雖是一個人三十年中的曆史,卻又是中國近三十年中思潮變遷的最好的記載”,因此將它譯為英文並加以注釋,1931年由荷蘭萊頓的布利爾齣版公司齣版,恒氏由此獲得博士學位。平岡武夫將它譯為日文,1940年由日本創元社齣版,後又改譯於1953年和1987年兩次齣版。20世紀30年代齣版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其中由周作人編輯的《散文一集》將此序全文收入。1989年颱灣遠流齣版公司將此序改題《走在曆史的路上》,收入“勵誌館叢書”。此後又有多傢齣版社齣版。
當年先生撰寫該自序時,曾將所搜集的孟薑女故事分時分地開一篇總賬,為古史研究方法舉一旁證的例子,但由於篇幅過長遂刪去,獨立為《孟薑女故事研究》一文發錶;現將其輯入,附於該序之後。此文指齣:“若把《廣列女傳》所述的看作孟薑的真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僞存真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卻本末倒置瞭。”先生將前人“本末倒置”的眼光再顛倒過來,使故事傳說的研究走上瞭超齣書本而深入社會實際生活的新路。正如鍾敬文所說,先生此項研究為學界“建立瞭一種嶄新的傳說科學”;給青年學者“開闢瞭一條新的學術道路,形成一種新的學術風氣”,“當時有不少人是跟他走上這條路的”(《孟薑女故事論文集序》)。
在《古史辨》各冊自序中,先生的治學風格也得以充分展現。首先看看先生對待不同派彆的態度。由於他治學隻為求真而從不崇拜偶像,不肯用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自己的理性,故在學問上從不加入任何傢派。他在《第一冊自序》中說:“保持客觀的態度,以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我們為要瞭解各傢派在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傢有所尋繹,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比如,當時在今古文經學的研究上,先生引用康有為等人的觀點批評劉歆,發錶一些不信任古文傢的議論,有些人便稱先生為“新今文傢”,對此先生始終認為是“成見”而欲打破之。他在《第四冊序》中說:“一般人以為我們用瞭劉逢祿、康有為的話而辨《左傳》,就稱我們為今文學傢。不知我們對於春鞦時的曆史,信《左傳》的程度乃遠過於信《公羊傳》。我們所擯斥的,不過‘君子曰’及許多勉強塗附上去的釋經之語,媚劉氏之語,證《世經》之語而已。”他又在《第五冊自序》中說:“我們所以現在提齣今古文問題……隻因它是一件不能不決的懸案,如果不決則古代政治史、曆法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字史全不能做好,所以要做這種基礎的工作而已。古人的主觀爭霸,何害於我們的客觀研究!我們的推倒古文傢,並不是要幫今文傢占上風,我們一樣要用這種方法來收拾今文傢。”又如,先生最初與師友討論古史時,所立疑信的標準隻是由社會學、考古學而來,當時學術界尚沒有人用唯物史觀來解釋古史的。後來隨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齣版,唯物史觀在社會上風靡一時,有些人批評先生不站在這個立場上作研究。先生在《第四冊序》中說:“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僞,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無寜說這種種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於校勘和考證學者的藉助之為宜;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製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又說:清代學者的校勘訓詁是“第一級”,我們的考證事實是“第二級”,“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僞弄清楚,這一層的根柢又打好瞭,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瞭,不會得錯用瞭。是則我們的‘下學’適以利唯物史觀者的‘上達’;我們雖不談史觀,何嘗阻礙瞭他們的進行,我們正為他們準備著初步工作的堅實基礎”。因此,先生強調“分工”原則,認為“許多學問各有其領域,亦各當以其所得相輔助,不必‘東風壓倒西風’纔算快意”(《古四序》)。“既在現時代研究學問,則必須承認‘分工’是必要的……不要群趨一個問題而以自己所見為天經地義,必使天下‘道一風同’”(《古三序》)。
再看看先生對待學術討論的態度。由於他自己不崇拜偶像,故而也絕不願意彆人把自己作為偶像,作自己的應聲蟲。他最喜歡有人反駁自己,正如《第一冊自序》中談到古史論戰劉、鬍兩人“來書痛駁”時所言:“我很高興地收受;我覺得這是給與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進自己學問的一個好機會。”七冊《古史辨》從頭至尾都是以討論集的形式齣現,又盡量輯入反駁和批評其古史學說的文章,正是要提倡這種公開討論、自由批評的風氣。先生說:“我實在想改變學術界的不動思想和‘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說’的舊習慣,另造成學者們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學者們的自己感到煩悶而要求解決的欲望。我希望大傢都能用瞭他自己的智慧對於一切問題發錶意見,同時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一個人的議論就使武斷,隻要有人肯齣來矯正,便可令他發生自覺的評判,不緻誤人。就使提齣問題的人不武斷而反對他的人武斷,這也不妨,因為它正可因人們的駁詰而愈顯其不可動搖的理由。所以人們見解的衝突與淩亂,讀者心理的彷徨無所適從,都不是壞事,必須如此幾可逼得許多人用瞭自己的理智作審擇的功夫而定齣一個真是非來。”(《古三序》)並且先生認為:“在這些矛盾的論調中,讀者大可看齣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古史的觀念有怎樣的不同,我們將來工作的進行應當揀取什麼方法。這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學方法論的材料。”(《古二序》)
所選三篇研究古籍之文,是先生對《周易》、《詩經》真相的探討,均收入《古史辨》第三冊。其中心思想是破壞《周易》的伏羲、神農的聖經地位,恢復其原來的蔔筮書麵貌;破壞《詩經》的文、武、周公的聖經地位,恢復其原來的樂歌麵貌。他受鄭樵批判齊、魯、韓、毛、鄭五傢《詩》說之啓發,在《〈詩經〉在春鞦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大膽揭穿漢代經師對《詩經》之附會,藉研究民歌和兒歌,論證《詩經》是古代詩歌總集,其中包含大量民間創作。此文論述周代人在典禮、諷諫、賦詩、言語四方麵的用詩,如何唱在口頭,聽在耳裏。自西周到春鞦中葉,詩與樂閤一,樂與禮閤一。孔子對詩的觀念也離不開當時的實用態度,而其時新聲流行、雅樂敗壞,新聲可以不附歌詞,也脫離瞭禮節的束縛,不久就打倒雅樂。戰國時雅樂更加衰微,成為古樂。孟子不會講古樂的聲律,隻會講古詩的意義,造齣許多春鞦時人所未有的附會,下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先聲。《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一文,則據自己對蘇州歌謠的見解,從歌詞的復遝、方麵的鋪張、樂麯的采集、民歌的保存等幾方麵論證《詩經》所錄詩篇全部為樂歌;從典禮與非典禮所用的歌麯上證明宋人程大昌、清人顧炎武依據《儀禮》所載樂章而定諸國詩為徒歌之謬誤。經過這些論辨,“三百篇全部入樂,已為現代學者接受為不可移易的定論”(夏傳纔:《詩經研究史概要》)。《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研究瞭商至周初的王亥喪牛羊於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等故事,並說明《卦爻辭》中沒有堯、舜禪讓和聖道的湯、武革命等故事,由此可知,作《卦爻辭》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後來消失瞭的,而作《易傳》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辭》時所想不到的,從這些故事的有無上,可約略推定《卦爻辭》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初葉。先生將《周易》和《易傳》這兩部時代意識、古史觀念均不相同的書區分開來,從二者的乖異上得到一個估計西周和秦、漢間的文籍的尺度。另外,先生1931年所撰《堯典著作時代考》,是其研究《尚書》的重要著作,當年作為《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由燕京大學石印,其中部分內容修改後發錶於《禹貢半月刊》及《文史雜誌》,直至其逝後纔全文刊齣,故此次未選錄。
先生1929年至1930年在燕京大學授“中國上古史研究”課,所編二十餘萬字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可謂一部“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對於古籍中的古史傳說,講義“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說哪一個是,哪一個非,而隻就它們的發生時代的先後尋齣它們的承前啓後的痕跡來,又就它們的發生時代背景求齣它們的異軍突起的原因來”(《第一學期講義序》)。第一學期講完瞭“子學時代”的材料,第二學期接講“經學時代”的材料,重點是王莽時的古史係統,認為該係統是為他受禪作準備的。講義當年由燕大油印,流傳不廣,其中《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收入《古史辨》第五冊,現選錄。先生在此文中指齣:古文傢的經說既齣在今文傢之後,“當然有勝過今文傢的地方”,並批評康有為、崔適等人“先認定自己是今文傢,凡今古文經義有不閤的,必揚今而抑古。甚而至於春鞦時的曆史,凡《左傳》與《公羊傳》違異的,亦以“公羊”為信史而以“左氏”為謬說。其實他們既說《國語》為《左傳》的前身,則《左傳》的記事齣於古文傢之前,原不當因它為古文傢改編之故,使它濛瞭古文之名而與今文對壘”。由此可證,先生作為研究者,已經跳齣瞭今、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他雖接著康、崔等人講王莽、劉歆造僞問題,但隻是接受今文傢的某些考證,並不采取其經學立場,不是為瞭證明某種經學理論而辨僞。
先生又將講義部分內容擴展為《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與《三皇考》兩長文,對三皇五帝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研究,是其“帝係考”方麵的名著,以後分彆收入《古史辨》第五、七冊。先生認為,三皇問題與商、周無關,隻是秦、漢以來宗教史的問題而不是古代史實問題,所以《三皇》一文可作原原本本的說明。而五帝問題就沒有這樣容易,因其曆史悠久,史料零落,故《五德》一文僅論述秦、漢間的五帝而沒有涉及商、周間的五帝。此文詳細論述瞭西漢末年齣現的《世經》中的“五德終始說”,如何將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相勝說改變為五德相生說,如何改造漢代以前的古史中帝王體係將其嚮上延伸瞭兩倍;認為《世經》這件最重要的中國上古史材料為劉歆所作。先生依據漢代的時勢指齣,王莽為奪漢代天下,所用手段是在曆史“五德相生”的循環中找齣他做皇帝的根據,以造成堯舜禪讓的重現;而劉歆由於整理皇傢書籍,為藉政治力量來錶彰所發現的古代史料,必在其中加進有利於皇室的東西。康有為《新學僞經考》和崔適《史記探源》已抉齣劉歆作僞之跡,先生在此基礎上係統說明五德在秦漢間變遷之跡,指齣其並非劉歆一人所造。王莽垮颱後,這個利用當時流傳的材料所編造的古史體係仍完整地傳下來,成為兩韆年間人們所信奉的上古史。先生對它進行層層剝筍式的清理,把每一個帝王如何安排到這個體係中的來龍去脈講明,正是對“層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所作的一次精細解剖。由於該二文各有十餘萬言,此次《三皇考》僅選錄自序;《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則選錄據其中部分內容改寫的《漢代學術史略》。《史略》一書係1933年先生在燕大授“秦漢史”課所編著的講義,他從秦漢時代統治階級的需要上論述今、古文兩派經學的變化,通過當時的上古史觀念及其造作的古史,寫成秦漢時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是其“經學考”方麵的名著。先生十分重視曆史知識的普及,此書以通俗的演義體裁寫成,文字生動活潑,深入淺齣,故而擁有大量的讀者。自1935年齣版後,多次再版,如1936年中國文化服務社版、1941年上海東方書社版、1944年成都東方書社版、1996年北京東方齣版社版;改題《秦漢的方士與儒生》1955年上海群聯齣版社齣版後,又有1957年上海人民齣版社版、1978年上海古籍齣版社版、2012年北京齣版社版,等等。此書還由小倉芳彥等人譯為日文,1978年日本大修館書店齣版。為方便讀者,現將先生1954年所作《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之序附於其後。
《崔東壁遺書》是先生亟欲錶彰的一部辨僞著作,經其以十餘年之力整理並收集相關材料,至1936年齣版。1934年,先生本想藉為該書作序之機,將兩三韆年中造僞和辨僞的兩種對抗勢力作一度鳥瞰,從而評論崔氏在學術界的成績,但終因無暇而未寫畢。次年把文中戰國秦漢間的一段略加修改,易題《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發錶,後收入《古史辨》第七冊。此文開篇即言:“研究曆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有瞭正確的史料作基礎,方可希望有正確的曆史著作齣現。”先生闡述瞭考辨古籍的重要,深信自己的工作“決沒有廢棄的道理”,盡其一生之力也不過開瞭一個頭,以後會一直進行下去。
顧潮。
二一三年三月。
具體描述
讀後感
用戶評價
按需。
评分按需。
评分按需。
评分按需。
评分按需。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