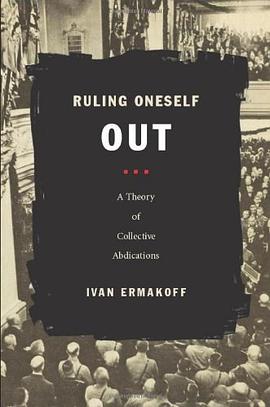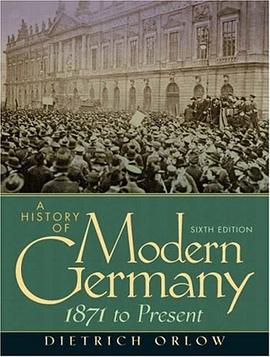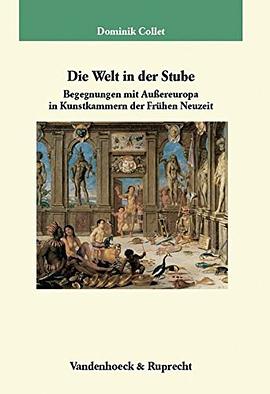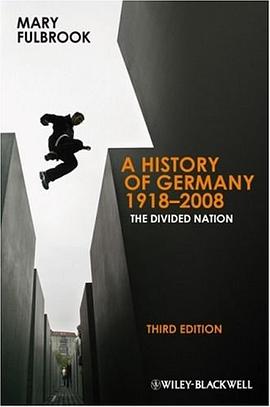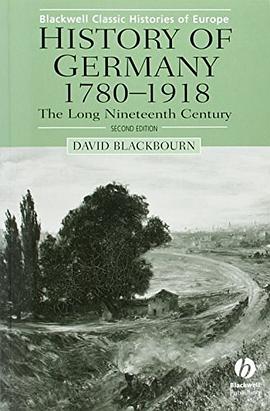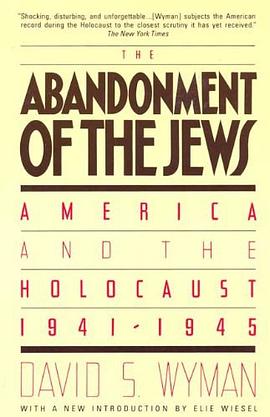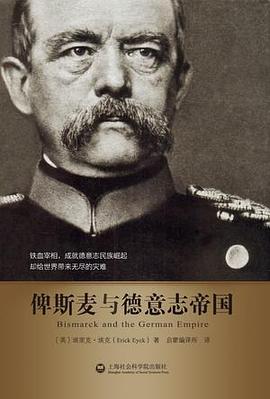具体描述
《德意志公法史(卷三)》所涵蓋的時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起,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為期不過短短30年。然而其間德國卻遭逢戰爭的洗禮、帝制急速崩解、共和體制倉促建立又隨即衰微、納粹黨徒合法奪取政權又藉此終結民主憲政等巨變。作者Michael Stolleis教授在本書中詳盡地描述了這段時期中,德國國家體制以及政治、社會與經濟條件的種種巨變,究竟對當時的德國公法學界(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造成了何種影響,身處其中的德國公法學者又是如何回應此一巨變的精彩過程。對於同樣亦曾經歷威權統治的台灣來說,本書除了可以讓我們深入瞭解德國公法知識史上的精彩一頁外,或許也可以進一步作為我國公法學界發展歷程的參考座標,提供諸多反思台灣過去政治、社會及經濟變遷與公法學界間互動過程的思考元素。
推薦序一
隨著全球化的腳步,相較於以往,當代世界各國的法律文化更為緊密的交互影響。回顧歷史,整個東亞法律世界的西方化,不論是日本的法律現代化或者中國清朝歷經中華民國初年的變法,以及遷台後在台灣的法律現代化,我們都看到了單向的繼受西方法律。更清楚地說,東方繼受西方歐陸與英美的19世紀法律文化,當中主要的繼受對象是當時被西方國家認為「晚熟」的民族國家──德國。台灣的法律文化深受德國法律的影響,但我們對於德國法律的歷史發展與脈絡,卻始終瞭解不深。即使我們也清楚知道,一個國家的法律的生成與發展,始終與國家整體發展與社會歷史條件,密不可分。法律不是孤立的條文本身而已,法律也代表著國家權力之開展、社會之形成,以及參與其中的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互動。
社會科學不能不重視社會、文化與歷史發展之因素,法學為社會科學之一環,更應如此。我們的憲法深受德國威瑪憲法的影響,因而對這部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自由民主法治國家憲法,其制定之歷史背景、實施之經過,以及其為何後來有無法令人預見的結局?其演變的過程與前因後果,頗有探討的必要。因而,岳生德國留學期間(1961-1966),在海德堡大學兩次選修指導教授Hermann Mosler教授開設的「德意志憲法發展──自1918年至1949年」(Deutsche Verfassungsentwicklung von 1918-1949,1964年、1966年),並選修Böckenförde教授開設的「近代憲法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Neuzeit,1965s)。這些課程當時並不熱門。1960年代德國正全國上下專心致力於重建以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為核心的憲政秩序、健全聯邦憲法法院之運作、統一行政訴訟制度、實施德國法官法等;對於過去威瑪共和與納粹政權的反省與批判的聲音較為低調與保留,有關論著亦尚不多見。
如今,本書Michael Stolleis教授撰寫的《德意志公法史(卷三)》之出現,副標題為威瑪共和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法學與行政法學,正滿足了探索威瑪憲法與所謂「第三帝國」時代憲政黑暗期者的渴望,令人欣喜。Stolleis教授在這本書當中,首先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德國威瑪共和建立的影響,尤其是帝國崩解與共和的創立(第一章與第二章)。其次,以威瑪共和的建立與威瑪憲法的制定為主軸,探討當時德國公法學界對於此時政治現實的回應。其中主要描述威瑪憲法中具有爭議條文的解釋與討論,以及包含當時關於方法論的爭議(第三章與第五章)。同時,處理各邦憲法與行政法的發展,尤其是對於行政法學與行政學之關連性(第四章與第六章)。最後,說明希特勒依據威瑪憲法奪權後,德國公法學的轉變及其因納粹影響而逐漸崩毀的過程(第八章至第十章)。Stolleis教授清楚分析,威瑪憲法承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容納威瑪共和中各種勢力的期待與不滿,以及被希特勒政權摧毀的過程。
Stolleis教授自1975年至2006年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並自1991年起擔任馬克思普朗克歐洲法律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Rechtsgeschichte)所長,直至2009年退休。Stolleis教授長年獻身於公法史的研究,其著述多元且豐富,從早期的納粹時期的法律史研究,之後多本關於近代的國家法與公法史的專書,晚近也擴及東德的法律史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著作為德意志公法史四鉅冊(即將於2012年出版卷四)。
譯者王韻茹博士現任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王博士是台大法律系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在學期間曾選修岳生在該所講授的「行政法專題研究課程」,其碩士論文「論議會自治之界限──以釋憲權控制立法程序為中心」,由許宗力教授指導。之後,譯者赴德進修,追隨Stolleis教授研究憲法史,2007年夏,獲得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學位。2008年8月11日岳生在慕尼黑與Peter Badura教授伉儷見面時,Badura教授送岳生他在公法季刊(Archiv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剛發表的一篇短文,即對 王韻茹博士論文「1945年之後憲法基本權與基本權理論在台灣之發展──繼受德國基本權理解之歷史」(Die Entwicklung der Grund- rechte und der Grundrechtstheorie in Taiwan-Eine 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rundrechtsverständnisses)的書評。Badura教授為台灣公法學界的好友,在台灣有許多位表現傑出的門生,曾來台訪問數次,其對於以德文發表的台灣憲法學論著感到興趣,並不意外。岳生一方面感謝Badura教授對台灣的關愛,一方面也為譯者之論著能在德國歷史悠久的公法刊物被介紹,感到慶幸。回國後,同年11月21日,即邀請譯者在台大公法中心與翁元章基金會合辦的第17次「新秀論壇」,就「德國威瑪共和中的基本權與基本權理論發展」發表專題演講,其資料豐富、內容充實,推論中肯,甚受好評。王博士為作者Stolleis教授在台灣的「單傳弟子」,多年追隨作者學習與研究,必能信實地傳達Stolleis教授的真意。岳生相信本書將有助於台灣公法學界瞭解威瑪共和與納粹政權時代的憲政演變,故樂意推薦為之序。
前司法院 院長
前台大法律學系 教授
翁岳生
2011年11月
推薦序二
德國公法與公法學(包括憲法與行政法)對於台灣影響非常深遠。但是,到目前為止,台灣多數公法學的研究者及一般法律人對於德國公法的發展史理解有限。德國著名的公法史及社會法研究權威Michael Stolleis教授,從1988年開始,連續出版《德意志公法史》卷一、卷二與卷三。分別探討德國1600年至1800年、1800年至1914年及1914年至1945年之間德國公法學的發展歷程。這三本書是瞭解德國公法學從近代至現代的發展,及其對於德國影響的權威之作。現在王韻茹助理教授歷經四年的努力,將《德意志公法史(卷三)》翻譯成華文出版。這是華語地區讀者的福音。
我跟Stolleis教授認識於1994年,當年我在進行研究中國法制史過程中,體會到有必要更進一步進行比較法制史的研究;於199年8月開始接受國科會一年的補助,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進行德國法制史研究工作。當時Stolleis教授是「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所長。我雖然不認識Stolleis教授,但是透過書信,直接跟他自我介紹,並提出要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中心進行研究工作的請求。Stolleis教授不僅協助我的家庭在法蘭克福找到住房,並到機場接送我們全家。
1995年7月離開德國之後,因為忙碌,我幾乎沒有跟Stolleis教授有進一步私人的聯繫。但是在我研究「德國法制史」的歷程中,Stolleis教授所撰寫的《德意志公法史》共三卷的著作及《在不法中的法》(Recht im Unrecht-Studi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還有他所編輯並參與寫作的《17、18世紀國家思考者──帝國公法學、政治及自然法》(Staatsdenker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Reichspublizistik, Politik, Naturrecht)等書,對於我在法制史的研究與寫作都有重要的啟發。
Stolleis教授書寫的《德意志公法史(卷三)》,在時間上橫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14-1945)。這本書共分為十章。在第一章中Stolleis教授以「漫長的告別」作為標題,讓讀者從19世紀的歐洲社會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國家法學與行政法學的發展脈絡中。本書的第二章到第十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重點。從第二章到第六章探討的是德國在納粹帝國取得政權之前,德國公法學的狀況:包括當時大學教授、大學的情境與行政法學的發展(第二章);德國的革命與威瑪共和的建立,探討當時憲法的重要核心議題(第三章);當時各邦的憲法與行政法(第四章);關於學者間有關國家學研究方法的辯論與國家的危機(第五章):當時的行政法學、行政學及教科書(第六章)。
本書的第七章到第十章則是討論在納粹政黨於1933年取得國家統治權之後,德國公法學的發展:包括國家法學與行政法學在大學及法學雜誌的狀況(第七章);德國公法學如何走入毀滅與自我毀滅的情境。(第八章);行政法學及國際公法學在納粹帝國的發展,包括當時的規範、教科書、雜誌及研究機構等(第九章);檢討公法學、大學在納粹政權中的角色,探討如何進行評價等議題(第十章)。
《德意志公法史(卷三)》華文翻譯的出版,除了可以讓華人地區的公法學者理解德國公法學在1914年至1945年前後發展的狀況,還可以讓華人地區的法律人及一般讀者,深刻瞭解到法律與法學對於一個國家與社會的影響。
透過王韻茹助理教授的翻譯,我們看到Stolleis教授這本書努力呈現德國或歐洲人如何面對1914年8月世界史上的重大轉捩點的處境。Stolleis教授在第一章開始提到20世紀初:「連當時的人們也意識到一個時代的結束。瞬間,歐洲數百萬人的生活觀幡然大變,政治與公共生活處於新的事實條件當中。」
他透過下面的話提到20世紀的戰爭特性及其對於當時生活的影響:「龐大戰爭機器撼動了俄國沙皇、德意志帝國、奧地利多民族國家、法國與英國;彷彿是19世紀與其所有的奮鬥與成果都捲入一個漩渦當中。即使彼此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仍強調彼此間的連續線,此時的多數人也還無法完全掌握每一個轉捩點的重要性,然而無論如何,和平美好舊時光及『安全的黃金時期』(Stephan Zweig)已走向黃昏。」
Stolleis教授用他歷史研究者的敏銳觀點,告訴我們:「那些對國家還懷有情感的人,他們歡呼戰爭的爆發是救贖(Erlösung),他們懷舊回憶戰爭前的時光。擁有穩定通貨與安全市民生活關係的君主制散發出美好光輝,至少以往享受過舒適生活的人如是想。」(取自本書翻譯中的第一章第一部分)
在書中的最後一章,Stolleis教授提醒我們:「……關於如何評價1914年至1945年的三十年間,一個學科走上的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人們可能會提出應採何種『評價』標準問題。由於是歷史研究,這個標準是無法外於歷史的,故不應從後見之明的知識中得出這些評價標準。即使這些評價標準使得『評價』有其可能,但應根據何種的判準(Kriterien)與規範(Normen)?這看來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儘管如此,Stolleis教授還是提出一個可能:讓素材說話。他提到:「完全放棄評價之出路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在選擇與描述素材時,這些關於素材之品質的與道德的評價一定會出現,也必須出現,因而人們也不能對這些素材投降。每位作者與讀者都瞭解,評價必然與時代相關,並且相當主觀。」(以上均取自王韻茹教授第一章的翻譯)
今年(2011)10月政治大學法學院邀請Michael Stolleis教授進行為期四天的會議。在會議中,Stolleis教授分別針對「德國公法史的寫作與研究方法」及「轉型正義」、「法律與文化」等議題,跟台灣法學教授與學生進行交流。在這四天的會議中,我有機會跟Stolleis教授與王韻茹助理教授進行更深刻的交流與對話;也因此很榮幸地接受邀請為《德意志公法史(卷三)》的華文出版寫序。
我相信讀者跟我一樣,透過王韻茹助理教授「信、雅、達」的翻譯,在Stolleis教授為我們描繪1914年至1945年德國公法學的世界中,沉思與體會法學知識對於世界的意義。
政治大學法學院 特聘教授
陳惠馨
作者序
歐洲法學自中古時期起逐漸開展,主要是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荷蘭與德國的大學中,其起源是為了註釋再度被發現的「羅馬」法。人們將羅馬法理解為一種具統一性的法,並且教授與學習之,與此同時,法律實務卻遵循鄉村、城市與各邦國的習慣法,或者在宗教事物上遵循教會法。
在歐洲,傳統上我們將發現西方「新大陸」與東方「中國」與「日本」的15世紀至17世紀,認為是早期近代,此時法律的統一性開始分裂。人們區分了私法與公法、刑法、采邑法(Lehnrecht)、自然法與國際法。在德國,1600年左右,首次有了公法的課程(ex iure publico)。
對於與公法關係親近的法律史學家而言,書寫公法史是相當吸引人的一件事,在其中,無論是對公法的思考與書寫、或是在大學中對公法的分析與思想上傳遞,都與憲法史與行政史緊密相關。這曾是幾乎無典範的一項任務。我撰寫的(德意志)公法史卷一的編年始於1600年,終於「神聖羅馬帝國」於1806年的結 束 。(德意志)公法史卷二始於19世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 ,其間歷經了1848年「德意志革命」與1871年民族國家的建立,此不僅是憲政運動的年代,也是工業革命與「社會問題」的年代。
這本(德意志)公法史卷三的內容涵蓋了1914年至1945年,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威瑪共和與國家社會主義時 期 。這本書描述了德意志歷史上扣人心弦並充滿沉痛哀傷的年代,但此書只從法學觀點為觀察。度過種種危機並從君主制轉變為共和的體制,最後(威瑪共和)仍結束於獨裁制。從俾斯麥時期的公法學之中,形成了威瑪共和的威瑪憲法與公法學,同時也伴隨有名的「方法論論爭」。1919年凡爾賽條約之後,國際法重新獲得重視。自由法治國的行政法轉向成為工業社會的干預國家與給付國家的行政法。
納粹獨裁體制利用並強化上述工具。此獨裁體制混合了傳統與新興法律,以及規範與恐怖統治。即使私有財產制仍持續存在,卻可以為政府所強制徵用。少數族群──尤其是猶太人,被剝奪權利並被迫流亡至他國。最後,這個體制(於戰爭期間與趁著戰爭之際)在集中營「消滅歐洲的猶太人」。在這段時期,德意志國家法與行政法處在最低點。這個學科不僅從外部被摧毀,也因內部公法學者的作為而自我消滅。這個解消的過程對於學術史是重要的:應如何理解這個國際上受到尊重的法律文化竟會屈服於獨裁的強制?當國家法與行政法學者在正當化這個政府的行為或者至少以口頭加以美化粉飾時,又是懷著什麼樣的動機?
1945年之後,這些法律人如何能回歸民主法治國家之基礎?被驅逐之公法學者又如何自處?法治國、社會國以及民主又要如何重新建構?
對於一位以母語書寫且從未想過會有外國讀者的作者而言,因其作品被翻譯而使得他的孤獨工作變得有價值。翻譯開啟了新的文化空間與帶來新讀者,而且可再度改變讀者的視野。因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們應看重與支持翻譯這件事。我相當欣喜,在法蘭克福取得博士論文的王韻茹博士 能承擔並完成了這項翻譯工作。她謹慎與深入地鑽研了20世紀前半葉德意志的公法史。我由衷地感謝她!
Michael Stolleis
法蘭克福 2011年12月
作者简介
1941年7月20日生于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德国法学家和法史学家。2006年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公法和法制史教授席位荣退。1991-2009年担任马克思普朗克欧洲法制史研究所所长。
1、 生平
他是Erich Stolleis的儿子,前者在1937-1941年间担任纳粹政府的路德维希港的市长。1960年从今天位于葡萄之路的Neustadt的Kurfürst-Ruprecht文法中学毕业后,施托莱斯在海德堡和维尔茨堡学习法律、日耳曼学和艺术史。1965年和1969年分别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1967年在慕尼黑跟随Sten Gagner获得博士学位,在短暂担任von Campenhausen男爵的助手后,1973年在慕尼黑获得国家法、行政法和新法制史以及教会法的教授资格。一年后,接受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邀请。1991年获得德国科学研究协会颁发的Gottfried Wilheilm Leibniz奖。同年成为马克思普朗克欧洲法制史研究所(MPIER)所长。2006年从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席位和MPIER所长职位上荣退。但是在2009年9月之前仍然担任临时领导人。他是大量的国内和国外学术组织的成员,也是各种丛书和期刊的共同编辑。
他的研究领域是公法(社会法)、当代法制史和近代法制史(尤其是公法的学术史)。鉴于他毕生从事研究和教学以及作为学术上的典范,2010年3月5日,获得联邦一级十字勋章。自2004年起成为德国自然科学学会成员。
2、 著作
《Christian Garve的政治道德》,博士论文,慕尼黑大学1967年版。
《18世纪晚期哲学背景中的国家理性、法律和道德》,哲学研究丛书第86卷,Meisenheim Hain1972年版。
《纳粹法律中的福利形式》,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第15卷,柏林Schweitzer1974年版(教授资格论文,慕尼黑大学1973年)。
《早期近代的国家财政》,美茵河畔法兰克福Klostermann出版社1983年版。
《德国公法史四卷本》,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8-2012年版。
第一卷,1600-1800年的帝国出版物和警察学,1988年版。
第二卷,1800-1914年的国家学和行政学,1992年版。
第三卷,1914-1945年共和与独裁时期的国家学和行政学,1999年版(2012年还以《德国公法史:魏玛共和与纳粹时期》为题出版了特别版)。
第四卷,1945-1990年东西德的国家学与行政学,2012年版。
《公法史中早期近代的国家和国家理性》,美茵河畔法兰克福Suhrkamp1990年版。
《不法之法:对纳粹法制史的研究》,美茵河畔法兰克福Suhrkamp1994年版。
《构建与干预:对19世纪公法史的研究》,美茵河畔法兰克福Suhrkamp2001年版。
《德国社会法史概论》,斯图加特Lucius和Lucius2003年版。
《法律的眼睛:一个隐喻的故事》,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4年版。
《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东德的国家学与行政学》,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9年版。
《施托莱斯选集》,两卷本,欧洲法制史研究第265卷,Stefan Ruppert和Milos Vec主编,美茵河畔法兰克福Klostermann出版社2011年版。
目录信息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作者序
前 言/1
第一章 漫長的告別
1.重大轉捩點/5
2.與19世紀漫長的告別/8
3.戰爭之前的國家法與行政法/24
第二章 戰 爭
I.戰爭爆發、戰爭結束與大學/27
1.戰爭爆發/27
2.大學教師與大學/29
3.戰爭中之憲法修改/33
II.戰爭時期的國家法理論/40
III.戰時行政法/45
1.1914年之前的起點/45
2.新的法律形式/47
3.期刊雜誌/54
4.小 結/56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当某种程度的法学的客体与方法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之后,本应可建立价值秩序的“法学”理念核心反而成了空洞的言辞。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19世纪开始成长,不再存在基础。这也许可以适度说明市民的举止,基于1926至1930年间方向与方法论争的确信,人们强调,在公法领域,实证主义已被超越。在政治与历史形式中,公法再次源引“生存”,但这样的确信却无法作为一个反抗政府的基础,相反地,这个受宣传的反实证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亦即,国家法、行政法与国际法的政治化。法律实证主义已成过去式,代价却是失去了原本受文本拘束的法律体制对于自由形式保护的特质。”
评分“当某种程度的法学的客体与方法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之后,本应可建立价值秩序的“法学”理念核心反而成了空洞的言辞。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19世纪开始成长,不再存在基础。这也许可以适度说明市民的举止,基于1926至1930年间方向与方法论争的确信,人们强调,在公法领域,实证主义已被超越。在政治与历史形式中,公法再次源引“生存”,但这样的确信却无法作为一个反抗政府的基础,相反地,这个受宣传的反实证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亦即,国家法、行政法与国际法的政治化。法律实证主义已成过去式,代价却是失去了原本受文本拘束的法律体制对于自由形式保护的特质。”
评分“当某种程度的法学的客体与方法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之后,本应可建立价值秩序的“法学”理念核心反而成了空洞的言辞。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19世纪开始成长,不再存在基础。这也许可以适度说明市民的举止,基于1926至1930年间方向与方法论争的确信,人们强调,在公法领域,实证主义已被超越。在政治与历史形式中,公法再次源引“生存”,但这样的确信却无法作为一个反抗政府的基础,相反地,这个受宣传的反实证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亦即,国家法、行政法与国际法的政治化。法律实证主义已成过去式,代价却是失去了原本受文本拘束的法律体制对于自由形式保护的特质。”
评分“当某种程度的法学的客体与方法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之后,本应可建立价值秩序的“法学”理念核心反而成了空洞的言辞。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19世纪开始成长,不再存在基础。这也许可以适度说明市民的举止,基于1926至1930年间方向与方法论争的确信,人们强调,在公法领域,实证主义已被超越。在政治与历史形式中,公法再次源引“生存”,但这样的确信却无法作为一个反抗政府的基础,相反地,这个受宣传的反实证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亦即,国家法、行政法与国际法的政治化。法律实证主义已成过去式,代价却是失去了原本受文本拘束的法律体制对于自由形式保护的特质。”
评分“当某种程度的法学的客体与方法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之后,本应可建立价值秩序的“法学”理念核心反而成了空洞的言辞。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19世纪开始成长,不再存在基础。这也许可以适度说明市民的举止,基于1926至1930年间方向与方法论争的确信,人们强调,在公法领域,实证主义已被超越。在政治与历史形式中,公法再次源引“生存”,但这样的确信却无法作为一个反抗政府的基础,相反地,这个受宣传的反实证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亦即,国家法、行政法与国际法的政治化。法律实证主义已成过去式,代价却是失去了原本受文本拘束的法律体制对于自由形式保护的特质。”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