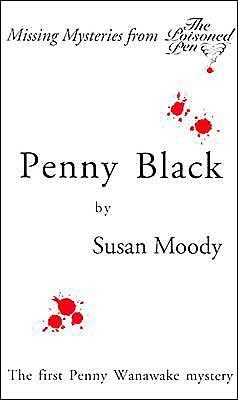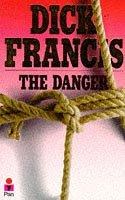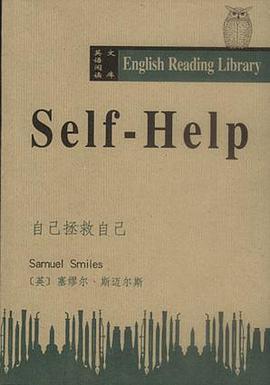词语穿越诗歌和生命内部时的特性
──金肽频诗歌印象及对他的某些心理阐释
胡书庆
摘要:金肽频是一位多年来一直在诗歌的玫瑰园默默耕耘的诗人。本文的叙述在文本分析和文本的心理透视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对金肽频诗歌创作的内容风格及其精神存在进行了深入考量,悉心感领了他那抽象与移情共同编织的丰富多彩的诗歌话语场。本文还对金肽频诗歌创作所表现的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精神还乡──进行了深度的心灵抚触。
金肽频是一位多年来一直在似乎永远都会具有某种古典抒情色彩的诗歌王国的纵深地带默默劳作的诗人──在这一点上颇类似他的同乡诗人海子。他的诗作没有刻意堆砌的意象,没有蛮横的表现形式上的变形,没有趋炎附势的“语言秀”,但我独乐意倾听这种朴素、本色的诗歌。它们是词语穿越诗歌内部和生命内部时的一种自然呈现。
(一)
综观金肽频的诗歌创作,在内容风格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己下潜到意识的深层对生存体验的诗性再现或消解(一个主要的聚焦处是诗人的日常感官体验)。这是诗人与世界相遇后把自我从外部世界中退缩回来,在自己心中展开一种智性的审美和感知诉求;诗作充斥着具有浓厚象征、隐喻色彩的意象。另一类是把自己的情怀直接寄托于移情对象上去,抒发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思念与向往。这样的诗作是一种纯净、优雅的个人抒情,意象表达上清澈如水。前一类诗歌具有较强的象征主义色彩,后一类则是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
在第一种劳作场域,诗人使用的是象征刀法,这刀法精确、细腻,使他言说的任何事物都站在了词语的芒上。在这里,词语和象征没有任何区别。诗人运用词语把触动他的形象封存,从而也把某种内涵永远封存进去──这是诗人天生的事业之一,他的诗歌领地有时就仿佛一个专门对形象进行封存的心智作坊。这类诗句在表达上有时像数学一般的精确(当然,虽然精确,也是诗性的,而非科学性的)。比如《转身而过》这样写道:“我认识一位麻醉师小姑娘/她浑身长满绿色/她有一身植物的气息/她走路的姿态叫做飘//那天我去找她,九楼/我要整整写出九行诗或者九个夜晚/九个阶梯才能到达的高度/在角落里向她说出一个字:疼!/长在额头里二十年的疼……”。[1]再比如《身体里的门》:“忘了钥匙,不能打开的寂静/是比这道门更深的门/一枚银针清晰地/在里面睡着/满屋的书却醒在那儿//暮色里,被我遗忘的这把钥匙/正在家中 享受着米饭的温暖/亲人的关切/成群的蚁虫从墙边跑过/显得从容而没一点局促//让一粒火重新回到灶膛!/钥匙对人类充满了好意/而在这个夜色超重的夜晚/它却像一张遗物启事/胆怯地躲进我的体内/让我体会/门是怎样一座空空如也的肉体”。[2]
我们可以拿《身体里的门》简单分析一下,试着去触摸一下被它打上了封存的密蜡的内涵:这首诗精确地暗示我们,生存的真理是某种澄明,它就仿佛一道有某种机关的门,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机关,生存便变得很简单,你的生存就不再像是一直被监禁于某个幽暗的房间里了;而打开这道门的钥匙,不是知识和认知(“满屋醒着的书”),而是某种适性而得的与生活本身的亲和力。
倾听这一类诗歌,总让我觉得,诗歌虽然是一种语言事实,但它暗示了一种内在自由的原则。它把生命的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语言,语言由此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生命肉身,一如《某一个疼》所写:“某一个疼 或者不像疼/一疼就是二十年/在两个词的中间/他们像梭子一样立着//某一个疼是模糊的 或者说/清澈得让你的骨头发亮/疼透了 只剩下一堆/血肉粘连的水分子//……某一个疼 不是头疼/也不是某些已知的词语/秘密地构成私人语法”(《某一个疼》)。当然,这种源自生命肉身的发声仍是象征的。它们把诗人内在的心理经验和情绪记忆投射到现象那里。只是,诗人以一种天赋的超人的感性洞察力发掘出了现象与现象间、心灵与现象间的诗意的关联。
我有时还觉得,诗人仿佛比一般人多了一重眼睛──一种很强的知性直观能力(康德将直观的繁多性综合为一体的思维能力称为知性,这里取此意;一般的词典上把知性解释成悟性,感觉还不是十分到位似的),金肽频能洞察到现象间的某种深层关联。然后,他还能寻找到准确的意象把某种已经内在化的经验表象出来。凡高曾说他能看到流动的空气,那是一种怎样的知性能力啊!我们不妨也来感领一下金肽频在这方面的能力吧:“一次又一次的风来到这里/模仿着田里/遍地的身影 少妇和野草/瞬隙之间奔跑而过的小动物/在土地深处延伸”(《紫云英》)。
不过我此时还想说的一点是,在这样的诗性劳作场域,诗人的心智活动虽然首先体现为一种审美诉求,但它也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心力和脑力的精神性创造活动。在与世界的相遇中,他总是费力地清理好自己“茫然的思想”,搜遍“所有的词语”“寻找一个关键”,“然后在它的刀刃上 看到锋/看到一种美妙的进入方式”(《关键词》)。也许外行人还以为创作一首诗就是惬意地往纸上写文字,实际上很多时候却是一种艰难的心智角力。诗人那个“长在额头里二十年的疼”说不定就与此有关呢!也许诗人自己有时已经感到了这样的诗歌劳作所带来的严重生理后果,于是萌生从中摆脱出来的愿望,一如他在《秋场》中对周围的风物进行一番诗歌抽象后如此突兀而直白地所表达的:“而我/开始遗忘/头痛开始加剧”。
当诗人“头痛”于抽象时,他当然不会就此离开诗的,他这时会来到另一个诗歌表现场域:移情。抽象与移情都满足了他审美诉求的需要,但如果说抽象使他“头痛”的话,移情则使他轻松。移情往往是他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单纯的歌唱和向往。诗人在这里被一种纯美的意境表达所包围,从而使他享受到一种单纯的审美的愉悦。在金肽频迄今发表过的数百首诗歌里,两类诗歌话语交替呈现,共同织就了他丰富多彩的诗歌话语场,也从不同的维度表证了诗人丰富复杂的思想和情感。
在自己的后一类诗歌里,诗人像一位誓将自己委身于土地、委身于人间真情的大地赤子,向生活的事物问好,并对美好的人性、人情和美丽的大自然进行了虔心歌唱。他歌唱春天:“露珠。纯粹的宫殿/缔造着青藤 绿叶 紫云英/也缔造着春天的童话”(《春天的几种形式》);他歌唱大地:“今夜。大地的杯盏/宽阔无比空旷无比/我在大地上行走/我是人类中的一个 鱼之外的鱼/月华如水 黄金杯盏呀/您是我永远的怀抱!//大地母亲 芳醇的杯盏/深深收藏人类中的我”(《大地的杯盏》);他歌唱本真意义上的劳动:“流火的七月 稻谷金黄/这是农民的季节/一年一度 农民的节气/火一样的光芒无法阻止他们//通向喜悦的丰收和秋后的牧场”(《无限的七月》);他歌唱人间真情:“从何而来 沉默的使者/你呈现钢铁的颜色/波涛相逐 无数的翅羽/压迫青鸟/青鸟像一道曙光/撕开溶集的百川/撕开苦难和风暴//三只大翅插在鸟的身上/一只是妻 一只是儿子/再有一只是故乡/青鸟 神的青鸟/在漂浮着琴音与水纹的河流上飞翔/大海的源头 敞开的麦田/听见了么/来自土地的第一声言语”(《青,我终身守护》)……在诗人的虔心歌唱里,我们不难触摸到一种浓浓的大地情思,和一种浓厚的人间情怀。
如果说诗歌的抽象力很多时候具有一种对生活的消解甚至某种程度的排拒色彩的话,移情诉求则似乎相反,它恰恰表现为一种接受力。实际上,诗人的审美力也更大当量地表现于移情诉求中。借此机会,我们不妨谈谈审美力这一话题。审美力的能力不像抽象能力那样,“它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它只能形成对已存在的组织结构的调节”;它是“感觉力的精练”,并且,“感受性并不产生任何东西,它纯粹是接受”。[3](p.24-25)其实,对天性比别人敏感的诗人来说,正是其审美力使庸常的生活事物在他自己的内心里形成了可接受的事物。审美力实质上就是一种接受力。这一点很重要。一些纯粹智慧型的抒情诗人,其诗歌劳作充满着危险──当他的精神性掘进达到一定深度时,对终极事物的思考彻底宰制了他,于是他“把自己毁掉的危险总是近在眼前”。[4](p.3)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审美力在他那里的表现的不足。对他们来说,诗歌创作似乎更像是一种认知意志的体现,而非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审美诉求。当一个诗人被认知意志所主宰并把这种意志交由诗歌去解决时,他将注定遭遇某种内在的危险。
金肽频的审美力是葱茏的──也正是这一点印证了他似乎更接近于是一个接受者而非一个消解者。他常常像一个初醒者怀着对世界的无限欣喜──有时自然也会伴随着世界和存在的神秘所带给他的某种轻柔的痛苦和迷惑──开始为他观感到的任何事物“命名”,“就像一个新亚当开始为万物命名”。他这样给春天“命名”:“春天,是给一朵花命名的过程/春天。在走出土地之后/就公布了花的清洁与秘密”(《春天,是给一朵花命名的过程》);他这样给故乡的远山“命名”:“阳光充满四处。阳光朗朗读着/那些遮掩得很深的内容/森林的声音不断被点燃/流逝的岁月重又回到山冈/谁高举着心灵的花朵 我曾睡过的岩石/从河流里升起”(《在遥远的山巅》);他这样给自己的出生地“命名”:“出生在这里:石头/无限的 抽象的 几乎不存在/我出生的地方一无所有……死亡在这里:石头/具体与真实同时存在/天空面对着大地/就像死亡面对着出生/这样的死亡:没有一定时间”(《出生地》)……这样的“命名”活动营造了一个没有人的精神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每一种现象都奇妙地道说着自己的变形。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其实在这样的“命名”活动中,自然和人文诸事物,以及诗人自己的喜怒哀乐,也都将在诗歌话语氛围本身那温柔的存在中在风景的灵魂中得到延续。
(二)
下面我要特别从金肽频的诗歌存在里提取出一个最核心的主题加以深度的心灵抚触,这个主题就是精神还乡。
通读了金肽频的大部分诗作后我感到,他的诗作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心灵某个层面上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让我感到里面仿佛隐含了一种精神的漂泊与回归的仪式。“漂泊”就是离开乡土,离开他的出生地来到城里。这“漂泊”一开始是地理意义上的,但曾几何时它就转变成了某种精神漂泊。“回归”的含义则是从精神层面回归他那已经被精神化了的“心理乡土”。在他这里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触到一个在城市漂泊的“地之子”的某种心理真实。
他写于1996年的《一场充满形式的风暴》真切地叙述了他的这一“心理故事”的全貌:“我忘记,我愿意表达/十七年前那场风暴/把一枚乡村里的种籽/吹进了城市//我忘记,我愿意表达/青山环绕家乡/山上布满白石/粉碎机的声音 像炊烟/在青瓦沟脊间跳跃//我忘记的 石头 圩堤/越活越健康/泥土的步伐永远落在时间前面/老家的门框里不断传出/结婚 生育和改嫁//我愿意表达的 是一个方向/把阳光轻轻投放在里面/把窗口对准了绿色/然后说 风暴 风暴/带我在晚上回家!”
这一“心理故事”,以及诗人在很多其它地方的诗歌记述,似乎告诉我们,一位乡村少年,怀揣某种梦想从乡村来到城市,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在城里扎下了根,不过他始终没有从精神上真正认同城市生态;或者说,他总是对城市生境有一种心理上的不适应感。没有诗意的城市给他带来这样的没有诗意的想象(好在他直写城市生态的诗就那么寥寥几首,能想象得到诗人是断不肯把更多的诗思赐予它的):“布匹和乞丐相拥而眠/铁栅栏在铁栅栏后面/以困兽般的眼光窥视着”;“钢筋 混凝土 相互握手/绿色村庄在遥远处伫望/几个流氓 几片树叶/都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设防”;“是一声咳嗽 或者是/一个拧毛巾的动作/然后泪水被泪水淹没”(《想象城市》)。而当诗人“从城市内部穿过”时内心则是这样一种感觉:“空虚的叶子 如果回头/只需一眼就心灰意冷”(《从城市内部穿过》)。诗人时时感到城市生境给他带来种种压抑感,而且,精神认同的危机也使他常常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这激发了他别寻精神补偿的愿望。自然,作为一个从大地深处而来的“地之子”,这寻找会与美丽的乡土事物相遇,一如他诗中所写:“从城市内部穿过 让人看见的/是在切开一种叫思乡的苹果”。于是,“被绿色深深掩盖的村庄”开始“在他的梦中散步”,大地深处无尽美丽的风情开始在他的诗国里建造“一座爱情童话”。
诗人歌唱乡土风情的诗在他全部诗作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这些诗作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醉人的图景,叙述了一个个“好的故事”。如《月山》写道:“月亮形的山 静谧 安详/就像我梦中的村庄//我梦中的村庄 住着两条河流/沿着河岸/是一块充满情意的地方/一对少男少女就在那儿长大//年年春风吹着 雨水滋润/这座村庄是座富裕的村庄/无数的白石头 雪一般围拢着/一小片桃花/开在我梦想不到的地方//月山掩映 石头知道/春天是风/爱情是雨水/这两样事物的背后/藏着一个绿草如茵的村庄//这里,八百米地下的黄金/以它敏锐的光芒/将地面上的人们照亮”。
诗人还在很多篇什中由乡土之恋上升到一种更为深厚也更为悠远的土地情思,和一种无尽敞开的大地情怀,用一种大地乡愁“构划他内心的时光”(这一点前面已有所述及,这里不再详细论述)。比如在《轨迹》中,诗人如此美丽地幻化了我们这个东方农耕民族古老的生存图景:“天空裂开一道缝/河流流出//两个人 坐在岸边/河流就是他们的目光/阳光一隅 他和她/构成另一隅……有人的地方/一定也有牲畜和庄稼/按照季节降下的雨水/在大地上描绘出人的面孔/以及山头的模样”。
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论点认为,“地之子”们是一些民间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乡土之恋具有一种“民间乌托邦”意绪,因为真实的乡土根本就不是这样子。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警醒于这一点而忽视了我们关于诗人的论述真正应该用力的地方。我们的论述真正应该用力的地方是:诗人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这是诗人对抗令他失望和厌倦的现实生境的一种精神诉求,“他在诗人的精神视域建构起一种梦境氛围,他在创作活动中藏进这个梦境,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可以忍受。”[5](p.10)这种精神诉求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审美诉求。而这种审美诉求之所以能成立,就在于诗人是在对乡土事物进行追忆。“追忆使记忆不再仅仅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而是一些美好的只可在心中经历的表象,在某种诗心与逝去的美好事物的相互触摸中神秘地显现。”[5](p.9)这样一来,诗人所诉诸的乡土就不再是真实的乡土,而是一种“桃源梦”,一种精神家园。
我们说,作为话语的诗歌本身不是故乡,但写诗则表征着诗人时时处在一种精神还乡中。就是通过这样的诗歌创作,他得以在精神上游离城市而遁入田园牧歌情致那永恒的人间福祉里去。也许诗人有时也确实意识到这种精神支柱的某种脆弱性──因为真实的乡土事物可能也时时威胁着他的“桃源梦”,于是从灵魂深处萌发出更为邈远更为深沉的精神诉求意向,使自己的精神与更神圣的事物建立关联:“……北斗七星 组成一根长长的锁链/连接起光明与幸存者……黑夜里 七匹马/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七匹明亮的星座/将时间的背景渐渐淡化……空旷的车子载着我/就像载着五吨重的石头/驶向遥远的方向里蕴藏的沙漠”(《隐遁》)。不过,像《隐遁》这一类诗在金肽频的全部诗作中比较少见,他更多地还是在一种自己对生活的葱茏的审美力的引领下唱着生活的恋歌,同时把写诗这种审美诉求本身当作了自己的基本精神生活方式。其实,对一个天生的诗人──或者说有一颗艺术的深心的人──来说,“唯一的可能性是生活在艺术中。只因生命的美学幽灵,所以生命才成为可能。”[6](p.357)对他来说,所有形式的精神还乡都有其内在的离心力──由于他对“时空之无限”的知性敏感,即便是人类中那些逝去的伟大精神典范们亲自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所点燃的一簇簇精神火焰,接触过后也可能让他“手心感到冰凉”(《玻璃里的火焰》)。他所拥抱的始终是审美本身。
(三)
金肽频在他的第三部诗集《金肽频诗选》的自序中认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有责任为自己素洁的诗歌而守望”。他进而声称,面对一切他深感龌龊的东西──首先是指当代诗坛某些看上去挺红火的所谓的诗歌(它们的命运当然会像一堆堆废纸屑那样早晚要被清扫出去),“除了诗句,只有用身体来反对!”乍一看到这一有点怪异的说法,使我一下子联想到当下语境中一个很时髦的说法──“身体写作”,然而当我悉心倾听了他的诗歌后才发觉,他之所谓“用身体反对诗歌”,在内涵上与那个时髦用语的具体所指完全是两码子事。他所说的“身体”的确切含义指的是全息的、内在的生命体验和经验。在这个“身体”里,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意志都是一个总体状态。诗人相信,他不可能写出比他本人的那个“身体”更真实的东西;而他的那个“身体”,恰恰是他“心灵的最好图画”。再者,诗人还坚信,除了通过他自己,他“没有达到世界的通道”,也不会有通达诗神的领地的路径。所以我说,对金肽频的诗歌存在而言,那是一种生命真实,一种心灵事实。
当然,诗人的诗歌存在首先是一种诗歌事实,是一种从诗歌内部流出来的命名和道说。它们秉有词语穿越诗歌内部和生命内部时自然会获具的一切特性。那穿越诗歌内部和生命内部的词语首先表征为生命的诗歌切入,也即以诗歌本身的方式道说诗人的生命体验和经验;其次,它还表征为诗歌的生命呼吸,也即诗人的生命体验和经验,诸如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悲悯心理,他的受难感和超越感,甚至他的神经和血液等等,又都在他那对自然、人文诸事物的诗意的命名与道说中得到延续。于是我还想说,金肽频的诗歌存在实际上暗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啻为一种把生存本身审美化的人生艺术。自1988年开始发表诗歌以来,近20年过去了,金肽频虔心地实践着自己的这种人生艺术。诗和他的生命本身早已融为一体。他以这种独属于他自己的自我感悟自我认知方式──
……小心翼翼地翻着他自己
读不懂的地方 绝不跳过去
对诗人来说,在其生命与诗的互相融入中,诗实际上扮演了他的守护神角色,因为每当他觉得某种“浓烈的幽暗从一旁悄悄靠近”时,每当他被“白日之斧无情地砍伤”时,每当他在岁月的深处突然感到仿佛已经失去了一切时,最后总是会有“一些小心翼翼的词语”穿越满心的创伤而来,“在春天”带领他“成功的突围”(《当我们秘密地通过一些词语》)。不消说,诗就是诗人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心灵的居所,如果没有这个居所,他的精神和心灵就会无家可归。诗人为什么选择了诗?这主要是基于一种审美诉求。诗人对什么事情都敏感,包括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悲剧性;但是,“当一个事件或一种情绪──一旦他把之诉诸艺术──使他进入一种美化的境界,进入一种新的感知或理解的境界,他就会通过这种诉求而感受到某种超越感”,[7](p.4)由此得以使他能够从内心里拥抱他在尘世注定要受伤的“在内心里滚动”的人生道路──因为他既已踏上这“受伤的道路”,他就天生需要一种审美的力量,就“只有像某个词拼尽所有的力量”(《受伤的道路》)。总之,是审美诉求使得他一旦在这个世界上遭受到适应上的危机时,一任“梦的神把他带走”,一任梦中的“大风”吹开生活灰色的表层,“露出被泥土深深埋藏的黄金”(《假如有一天你忘了我》)。
如果一定要让我用几句话总结金肽频诗歌创作特色的话,我想说,金肽频的诗笔就像一把犁,它能翻耕生命的深层,使生命的深层体验、使意识的那些神秘的覆盖层(感觉、情绪、心理、精神等)的黑土面朝上,在穿越诗歌内部和生命内部而来的词语中被照亮。通过他而获得新生的词语就像一束束从生活背后射过来的光,使那些本来不能使自己发光的生活事物在他的诗里具有美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金肽频.金肽频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金肽频.花瓣上的触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3]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唐少杰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胡书庆.翱翔与低回.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6]尼采.我妹妹与我.陈苍多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7]胡书庆.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具体描述
读后感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