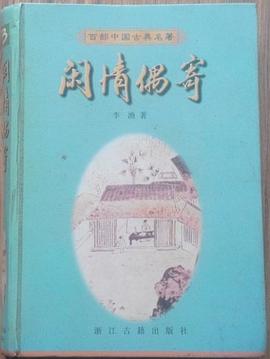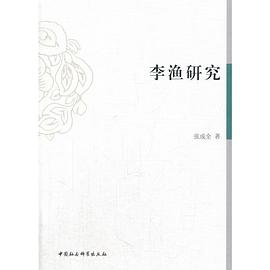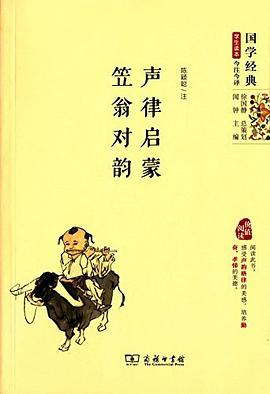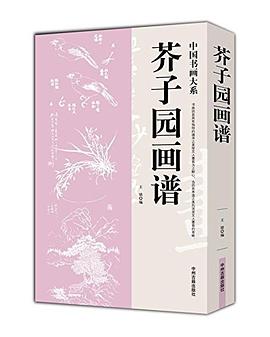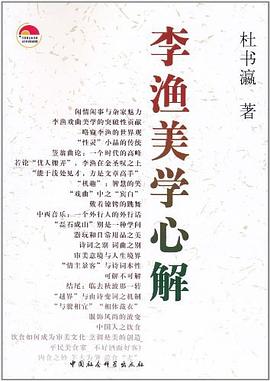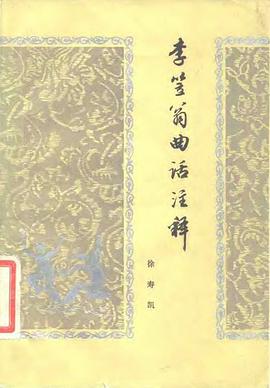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通常被后人称为《李笠翁曲话》,它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最系统、最全面论述戏曲创作和表演艺术的一部理论著作(见《中国历代曲论释评》第370页)。读完《笠翁曲话》以后,真有一种将其全部手抄一遍的想法,因为,从戏曲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创新以及对实践指导的角度而言,《笠翁曲话》真可谓字字珠玑。下面我想以札记的形式,逐句、逐段、逐篇地表述阅读后的感想,而不是以自己的思路对其进行所谓的系统归纳,因为《曲话》本身的论述顺序已经很系统了。感想多的篇章,则多写一些,感想少的,就少写一些;再根据笠翁的戏曲理论联系一点如今的戏曲现状,这样,这篇闲文就有实际的意义了。
《词曲部》
“结构第一”
笠翁十分重视戏曲创作的文学价值,并且细致、系统地总结戏曲创作的规律,这是在他以前的戏曲理论家们所没有做过、或没有做系统的工作。但理论界存在对李渔曲论评价过高而对《十种曲》评价过低的情况,谭帆先生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把李渔的曲论和曲作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即:以汤显祖到‘南洪北孔’这一系列来观照李渔的戏曲创作,而从古代曲论缺乏体系性、完整性这一背景来评价李渔的戏曲理论。这两种评价实际都不完全准确,如果从综合角度研究李渔,其实李渔的创作(甚至包括小说)与其理论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即李渔的戏曲是一种追求轻松、圆通、规整的通俗剧,而其曲论则是实现这种创作追求的实践技法理论。”(见《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不失公允的。
在这一部分中,笠翁指出“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能看出笠翁为学甚为客观,具有民主科学的精神,他认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把戏曲创作提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也正因为他重视“填词”,才会把这个当时旁人认为是“末技小道”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思考、梳理、研究。《笠翁曲话》对指导戏曲创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就是置于一般文体的写作,也同样能够适用。
对于结构第一的重要性,笠翁以生理(造物之赋形)与建筑(工师之建宅)的比喻来说明,而词采和音律都是“似属可缓”的。
“戒讽刺”
这一小节中,笠翁提出,戏曲剧本中,不同人物生、旦、净、丑的行当设置,体现了作者的好恶:“心之所善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
还提出对戏曲作者思想境界的要求:“传非文字之传,一念正气使传也”,戏曲作者应该将“名不与身俱灭”作为自己的追求。笠翁认为,填词作曲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将其仅仅作为宣传工具是不合适的,其内容有托名讽刺、用笔杀人的本意就更是离开了制曲的创作精神,因此,他会在传奇之前加一段“誓词”,力戒讽刺。当然,把戏曲的娱乐与讽刺两种功能截然割裂也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说这取决于观众的市场需要,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势,现在有的宣传部门片面强调写实,恐怕其实更多关注的也仅仅只是戏曲工具性的教育功能。
“立主脑”
笠翁解释他自己提出的“主脑”,“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可以说是首先阐述了现在通称“主题”的主脑的科学涵义,而“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就是说作者立言之本意是为一人一事而设,现在的“主题”至多再提炼一层,即这一人一事表现什么意思。没有主脑,“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至今的戏曲创作,仍有这种多中心的现象,虽然创作者认识不同,但如果也经常造成“观者寂然无声”的结果的话,就不能不说是创作的缺陷,会使得“有识梨园望之却走也”。
“脱窠臼”
“脱窠臼”既是对创作必须求新求变的要求,也是成功的诀窍。“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但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其实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新戏,都是如此,其“新”只是说明其出现的时间靠后而已。
“密针线”
这一节中,笠翁强调,戏曲的情节前后要有照应铺垫,“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能够经得起推敲。王国维曾经指出元杂剧的情节前后有很多漏洞和不近情理之处,其文学价值只在于“有意境而已”,而笠翁所处的时代,对于当时的戏曲样式——传奇的戏剧性的要求,已经提高了一大步,所以他认为“今日之传奇,事事皆逊于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外,胜彼一筹”;由此谈到传奇与元曲在艺术上的借鉴问题,“既为词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见,谓事事当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这其实也是论述了在继承优秀传统的问题上,不能食古不化,照抄照搬,而是吸收当中的合理之处,“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笠翁认为,“元人所长者,”只不过是曲,而作为曲、白、关目具备的综合艺术——传奇,就必须要综合这三种所长。
“减头绪”
“减头绪”和“立主脑”是相关的概念,立主脑必然减头绪,头绪减则必然主脑立,“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其实中国戏曲中意象化了的人物登场,以四小卒代千军万马,点到为止,明白意思即可。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中虽然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一人扮演,无关人物挥之即去,招之即来,目的只有一个:突出主线,便于观众理解,用笠翁的话也可以说是便于“传”。
“戒荒唐”
正如笠翁在前面论述到的,创作的目的在于传世,那么应当在平淡中见功夫,力戒荒唐。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须深入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是来之不易的。这一节中,笠翁还指出了放之文学艺术领域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王道本乎人情。“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由此让我想到了建国以前,曾在南方红极一时的以封神戏、济公戏为代表的大机关布景戏至今所以不传,笠翁其实于数百年前已经明确指出了原因:没有本乎人情。对于目下的戏曲创作,是否本乎人情,恐怕仍应该作为指导思想。“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是笠翁认为“最上一乘”的境界。
“审虚实”
对于如何处理虚与实的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笠翁在题中以“审”字明之。“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这是对“虚实”的概念界定。“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笠翁提倡“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无陪客,幻设姓名以代之,则虚不似虚,实不成实”,当前对于一些以“戏说”为主要方式的历史题材剧的批评,焦点也就多在于此。
“词采第二”
笠翁对以前剧本评价能体现他自己的艺术取向,他认为,《西厢》“全本不懈,多瑜鲜瑕”;《琵琶》“得一胜而王,命也”;《荆》、《刘》、《拜》、《杀》“全赖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论可矣”。
“贵显浅”
这个命题的提出,仍是从观众角度出发,即作传奇之前,必须明确受众群体,为之量体裁衣。“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后得其意思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新时期以来,创作了许多很具哲理性的戏曲剧本,含义确实深刻了,可是票房效果并不见好,恐怕也都存在不够“显浅”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笠翁认为元曲是学习写作剧本的最佳范本。
“重机趣”
笠翁认为,凡事在于意象精神,一灵不灭,自然生机勃发,填词要有贯穿如细笋藕丝般的灵气。“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强调了曲作者的悟性和禀赋,其实这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直观”、“妙悟”的特点,“机趣”是从灵性中来的。
“戒浮泛”
“戒浮泛”与“贵显浅”是一对必须很好把握的矛盾,关键在于“宜从脚色起见”,“常谈俗语,有当用于此者,有当用于彼者”,语言需要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而情是曲中贯穿的主线,既是灵魂,又是能够作为与其他事物的细致区别,也是笠翁认为容易把握的,要达到“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总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舍景言情”,是“舍难就易”的。
“忌填塞”
笠翁再三强调传奇“贵浅不贵深”,十分重视戏曲演出的剧场效果,填塞典故、脂粉、直书,就极其影响观看效果。“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这部分论述,其实已经初涉观众学的一些内容了。这一节中,笠翁同意金圣叹的观点,即肯定《西厢》、《水浒》的文学价值,也是亮明了自己的艺术取向,这在如今看来,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地位不言而明,但在明末清初,对它们的重视则不得不算是一种独具的慧眼。
“音律第三”
笠翁认为填词与分股、限字、调声叶律的文体相比较而言,填词在操作上的难度是极大的,能“布置得宜,安顿极妥”,便“千幸万幸”了,要顾得词品和人情就更难了,所以“总诸体百家而论之,觉文字之难,未有过于填词者。”关于在创作上的误区,笠翁以《南西厢》对《北西厢》的改编为例,指出《南西厢》在对西厢故事的搬演推广上作了贡献,但在“词曲情文”上则没能体现出原著的才情,是抑雅就俗的,所以“有如狗尾续貂”,丧失了原著的精神,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改编标准,也是词家所重的标准:宫调尽合、字格尽符、声音尽叶。
对于名著的改编,笠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对创作而言,是值得推崇的,他认为“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时流下?彼文足以传世,业有明征;我力足以降人,尚无实据。以无据敌有征,其败可立见也。”但是现在大概是因为对剧本的需求太过迫切,所以动辄搬演、翻演名著,成果是丰富了,实质能否保证就不得而知了。而对于不同审美层次的作品,要有区别对待的态度,审美层次的高低并不一定等同于存在价值的有无,有一定的审美层次,就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这一点在戏剧批评上是需要明确的,但要实事求是地对剧作的审美层次和存在价值作出判断。
“恪守词韵”
这一节中,笠翁认为“合谱合韵方可言才”,说明他还是强调戏曲在词韵上的规范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古代诗歌的一种形态,戏曲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形式规范,压韵既能体现动听的音乐性,又能便于表演者记忆,有着主客观的审美意义。
“凛遵曲谱”
“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这看似矛盾,实则辩证。传统也好,规范也好,毫无疑问,是一种陷阱,但所谓创新者,必须经历落入陷阱——跳出陷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逾越,几可视为艺术规律,曲谱也正是这样一种有妙用的“陷阱”。
在本节的结尾,笠翁写到对于制曲的出新“善恶在实,不在名也”,由此句想到如今一些新剧目标榜自我“创新”、“突破”,宣传口径各显神通,其实比之建国前的一些宣传语“环球第一”、“青衣须生泰斗”等等还有不及之处,是否“创新”,是否“突破”,甚至是“善”是“恶”,在实不在名。
“鱼模当分”、“廉监当避”、“拗句难好”、“合韵易重”、“慎用上声”、“少填入韵”“别解务头”
这几部分讲的是填词制曲的一些具体操作,“当”、“宜”、“难”、“易”、“慎”、“少”等都是相对的用词,应该理解为针对初学者而发,并非是绝对的金科玉律。用韵的合适优劣与否,直接影响到能否写出好句,关键在于能否悦耳,是否上口。
“宾白第四”
针对“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的问题,笠翁特将宾白专列出来论述。笠翁认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宾白与曲词在艺术上是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的,“文与文自相触发”。
“声务铿锵”
笠翁强调,“宾白之学,首务铿锵”,能“人人乐听”,始终是从表演角度出发要求的。这一节中,他还十分幽默地解决了连用平仄而声欠铿锵的问题,即“用一上声之字介乎其间,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两句三句皆去声、入声,而间一上声之字,则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听之不知其连用数仄者。”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便利地解决实际问题,笠翁指出这一便利的方法后,自信地认为:“一传之后,则遍地金声,求一瓦缶之鸣而不可得矣。”
“语求肖似”
这一节中,笠翁道出了自己以制曲为人生至乐的追求,可以在其中享受到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欢乐。同时提出“肖似”的概念,目的是“勿使雷同”,以生活的真实统一艺术的真实,而情感的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又强调“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
“词别繁简”
这里指出“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是不利于戏曲创作的,而自己则是“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完全是以登场演出为主要目的的。有人批评笠翁“填词既为填词,即当以词为主。宾白既名宾白,明言白乃其宾,奈何反客为主”,并不承认宾白的地位,其实仍是以文学视角和标准来衡量戏曲,这是当时无可避免、不必指责的局限,因为即使直到现在,人们评价戏曲剧本仍有这种倾向。
这一节中,笠翁还从宾白创作谈到了一般文学创作都需要提倡的个性化规律:“文字短长,视其个人之笔性。”笠翁对于宾白写作的重视,使得戏曲创作者开始从单一的文学作者向全方位、全能的戏曲编导发展,从而提高了对戏曲作者全能素质的要求。
“字分南北”
这节内容上强调的是“白随曲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方言与南北曲协调的问题。京剧的字音曾经方言驳杂,在上个世纪之交逐步定型,谭鑫培即在规范京剧字音上作出了京剧创始者的贡献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实践了笠翁“字分南北”的理论。
“文贵洁净”
笠翁说:“凡作传奇,当于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矣。”我认为这是艺术出精品的规律,艺术作品创作完毕以后,没有时间的考验,不可能自命为“精品”。至于什么是洁净,并不是以文字少多来定评的。
“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
“意取尖新”与前面论述过的“重机趣”其实是一个道理,目的就是“移人”,考虑的还是观众的接受,“少用方言”也是如此,但笠翁指的是当时通行全国的传奇,如果现在各地方剧种也这样效法,就有些形而上学了,没有方言,地方剧种的特色岂不是丧失无几,只剩声腔大源流而已。
“科诨第五”
笠翁把科诨定位在“养精益神”,作用是“驱睡魔”。
“戒淫亵”
在论述科诨问题上,笠翁第一步就强调了尺寸和技巧,遵循的实际上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标准,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本人“风流道学”的特点。
“忌俗恶”
笠翁曲话中对于“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这样辩证的提法很多,且一般都举出实例来证明。
“重关系”
“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这几句提到忠孝节义,不能简单地责之宣扬封建道德,而当意会为一种内在需要表达的思想,不过是借忠孝节义举例而已。笠翁提到的简雍、东方朔插科打诨的典故,都是“笑中有思索”的优秀范例,这也是科诨不易达到的较高境界。
“贵自然”
科诨也以自然为贵,而非矫揉造作的,“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这源自中华传统审美习惯,戏曲创作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否则会失去观众的承认。
“格局第六”
此处论及的是作剧的一般格式。其中“近日传奇,一味趋新,无论可变者变,即断断当仍者,亦加改窜以示新奇。余谓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很有现实意义,用到对现在很多的“创新剧目”的评价上,也十分贴切,艺术是否创新,不是贴一个“创新”的标签就行了,重形不重意,艺术生命是不会长久的。
“家门”、“冲场”、“出脚色”、“小收煞”、“大收煞”
这一系列的程序是传奇创作的基本格式,正如笠翁所言,“传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听人自为政者”,“遇情事变更,势难仍旧,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不是必须墨守成规的。笠翁曲话虽名为“闲情偶寄”,其实也处处在为同道的后学者十分热情地提供经验。
“填词余论”
最后一段话中,“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神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意乎哉?”,从这里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过分推敲词句与作家本意其实容易入歧,最终成为一种臆度。的确赏文有时在于意会,而无一字可言,尤其是中国传统审美习惯受禅宗的影响很大,对文学艺术的体会经常是“妙悟”而得。
《演习部》
“选剧第一”
在“词曲部”中,笠翁论述的主要是文学剧本创作方面的问题,因为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除了文本价值以外,其更多的艺术性体现在舞台表演上,所以,笠翁在“演习部”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开门见山地提出戏曲创作的目的性。为了实现能够“登场”的目的,需要按照艺术的规律、科学的方法,训练出合格的演员,才能真正在舞台上表现出创作者的意图来。因此,在“演习部”中,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笠翁有很多论述涉及到戏曲教育的若干问题,至今依然能使戏曲教育工作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在“选剧第一”的绪论部分,笠翁专门强调了“顾曲周郎”的作用。他认为,“最有识见之客,亦作矮人观场,人言此本最佳,而辄随声附和,见单即点,不问情理之有无,以致牛鬼蛇神,塞满氍毹之上。极长词赋之人,偏与文章为难,明知此剧最好,但恐偶违时好,呼名即避,不顾才士之屈伸,遂使锦篇绣帙,沉埋瓿瓮之间。”这样的情况是“尤可怪者”。笠翁并不把当时有的戏曲演出艺术性低到“瓦缶雷鸣,金石绝响”的原因简单归到“歌者投胎之误”和“优师指路之迷”上,而是认为这都是“顾曲周郎之过也”。用今天的话讲,“顾曲周郎”就是内行的、懂得欣赏戏曲艺术的精英人士,他们欣赏戏曲的趣味和态度,有时会对普通观众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导向性的作用,因此,笠翁态度坚决地认为,对于艺术性不高的戏曲作品,应该“使要津之上,得一二风雅之人,凡见此等无情之剧,或弃而不点,或演不终篇,而斥之使罢”,这样,才会“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因为“观者求精,则演者不敢浪习”。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笠翁很重视观众对观剧后的反馈,而且是有正确鉴别力的反馈,观众的需要就是戏曲演出的市场需要,但要注意,必须是健康的市场需要才是戏曲演出应当顺应的。今天有不少有识之士惊呼“戏剧理论批评的缺席”和原创剧目的实际不受欢迎时,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笠翁当年对此类现象的看法,应该是能有所启发的,作为当代“顾曲周郎”主体的戏剧理论批评工作者们,又是体现健康需要的观众主体,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和职责,要有“主持风雅”的责任感,客观地评价当代的、特别是原创作品的艺术质量,在舆论上给予广大观众正确的审美情趣的引导,惟其如此,“黄绢色丝之曲,外孙齑臼之词”的艺术精品才会“不求而至”,而不是恐“违时好”的“随声附和”,那就有如“矮人观场”。
“别古今”
为了能够很好的“登场”,选好的剧本付排和教学是笠翁摆在第一位考虑的。对于“古本”和“今本”的作用,笠翁认为要准确的对待,既不厚今薄古,也不厚古薄今,而在教授歌童的时候,需要遵循“开手学戏,必宗古本”、“旧曲既熟,必须间以新词”的先后步骤。在这一小节中,笠翁再次提出了“欲使梨园风气丕变维新,必得一二缙绅长者,主持公道,俾词之佳者必传,剧之陋者必黜”,这里的缙绅长者,和前面提到的顾曲周郎的责任实际是一样的,都起到一种引导艺术风气的作用。
“剂冷热”
这一小节中“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一语道出了抒情性是戏曲艺术的一大特点,因而戏曲才能成其为“剧诗”。
“变调第二”
有关传奇的“变”的,笠翁提出了两点思想,第一是必须变,“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第二是如何变,“贵在仿佛大都”,有“天然生动之趣”,这两点内容会使人很容易想起梅兰芳先生有关戏曲改革“移步不换形”的思想,尽管“移步不换形”是梅先生多年从事戏曲创新实践的体会,但在笠翁戏曲理论中还是能够发现惊人相似的论述,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对于“旧剧”的态度,笠翁“喜”的是其形式的美观完善,“惧”的是内容太过熟悉,其实观剧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主观审美行为,完全可以只挑想看的看。
“缩长为短”
对于戏曲演出的时间,笠翁认为,完全可以根据观众的生活和审美习惯灵活掌握的,并在本节中提出了“缩长为短”的具体操作方法,即用对白和独白的形式交代原本冗长拖沓的剧情,或是以演折子戏的方法,“不用全本”,或是根据古本,编一些“稍稍扩充之”的“新剧”,介乎“全本”和“零出”之间,我们似乎可以在这当中窥得今天舞台上仍然活跃的“本戏”、“连台本戏”和“折子戏”的演出雏形。
“变旧成新”
把一个陈旧的剧本,通过一番拆洗,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笠翁的原则是:“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味”,而实际的操作是以改科诨、宾白为切入口,对老剧本拾遗补缺,这对我们当前整理和改造传统剧目,有着很好的启示,“女娲氏炼石补天,天尚可补,况其他乎”,只是在于有没有“五色石”,由此可见,笠翁是很赞成对戏曲乃至于文学创作的革新的,革新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这种革新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授曲第三”
“解明曲意”
笠翁在这一节中指出的“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师或不解,不妨转询文人,得其义而唱”,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对演员文化素质的要求,不解曲意,“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曲所言何事”,最后导致只能唱“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的“无情之曲”,这是不可能达到高水平的艺术标准的,“变死音为活曲,化歌者为文人,只在能解二字”,演员的演唱惟有“能解”,方能内外合一,这也可以说是初步涉及到了体验和表现的统一问题。
“调熟字音”、“字忌模糊”、“曲分言和”、“锣鼓忌杂”、“吹合宜低”
这几节中,笠翁还是在授曲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根据反切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字头、字尾、字腹的概念;举例说明锣鼓安排的正确位置;以及明确了伴奏音乐与声乐的主次关系,这些问题既是初学者需要掌握的要领,又是舞台演出时应该遵循的艺术规范。
“教白第四”
笠翁在“词曲部”中就特别重视宾白在加强戏剧性方面的关键作用,这里又特别指出了宾白教学的难度,他认为,梨园之中,工说白者“百中仅可一二”,与“十之必有二三”的善唱曲者相比,是少的可怜的,这样的人,“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则其所传之师,乃一读书明理之人也”,所以笠翁也就特别强调教授宾白之人,必须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高低抑扬”、“缓急顿挫”
对于单一的句子诵读,正字为主,衬字为客,主高而扬,客低而抑,是笠翁提出的念白原则,其实也就是现代语法语法重音与逻辑重音的概念。而长篇大幅叙事之文,则需要“高低相错,缓急得宜”,字、词、句之间要有恰当的对比关系,而不是“水平调”,也就是现在戏曲中的俗语“一道汤”。关于念白注意高低抑扬和缓急顿挫的问题,在教学上,笠翁也提供了标注脚本的具体方法,真是又有理论,又有操作,即便是现在应用,也十分方便。
“脱套第五”
去除陋习,即是脱离俗套,就是一种革新,文学史上的历次复古运动其实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对戏曲而言,则不论是西子捧心,还是东施之颦,都是不能雷同搬用的。
“衣冠恶习”
齐如山先生曾提出,国剧需要遵循四条艺术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无动不舞”,舞蹈动作在中国戏曲中的渊源由来已久,李笠翁处于明清之际,那时的戏曲主要形态——传奇,歌舞也是其中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因而,传奇的舞台服装也需要适合舞台上舞蹈表演的实际需要,所以笠翁才会认为,在“歌台舞榭之上”的“妇人之服,贵在轻柔,而今日舞衣,其坚硬如盔甲,云肩大而且厚,面夹两层之外……”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解者”,应该是“易以轻软之衣”,并且明确表示,“予非能创新,但能复古”。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的,如今的戏曲舞台上,这种服装上的“不可解者”仍然再度复活,有的新编剧目,借用西方的经典传说,女主人公的服装不但“坚硬如盔甲”,不但“云肩大而且厚,面夹两层之外”,连水袖都宽硕无比,自不必说整套服装的重量了,穿着这样的演出服,还要要求演员载歌载舞的进行表演,简直是在考验演员的武工基础,恐怕观众看了都会和演员一起捏把汗,这样的“复古”,就不是创新了,而是在笠翁早就批判过的歧途上重蹈覆辙,成为一种新的“衣冠恶习”。
“声音恶习”、“语言恶习”、“科诨恶习”
以上几节所反映的,都是在笠翁生活的年代,戏曲舞台上的各种不良的演出陋习,这些陋习往往都是由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讹传讹,最终约定俗成的原因造成的,笠翁所批判的这些恶习,都仍应该作为我们今天在舞台演出时的警示。
小结:以札记的形式,逐字逐句地梳理阅读《笠翁曲话》的感受,尽量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而对于一些显而易见,且大家公认的问题没有一一赘述,有些联系现状的想法也并不一定与相关的篇章有直接的联系,可以算是借题发挥的。当然,逐字逐句,细则细矣,却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好在自己可以用吉光片羽这样的语词来藻饰每段札记中的所谓的“思想火花”。
具体描述
读后感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