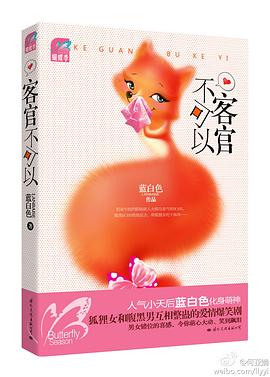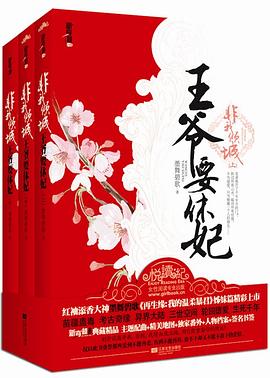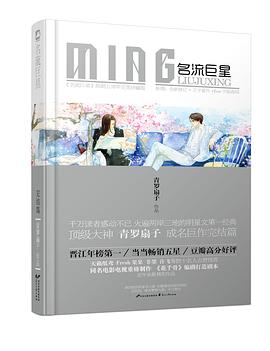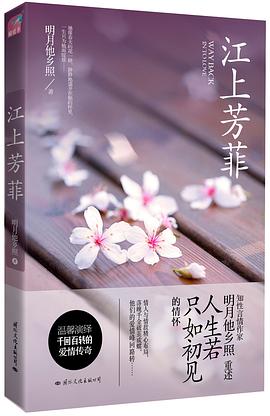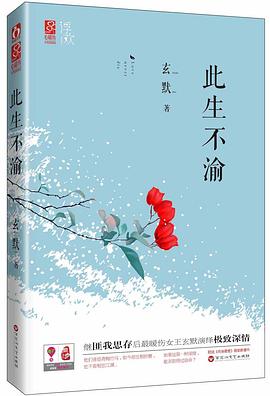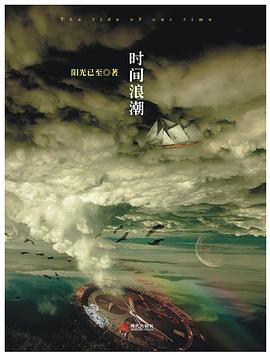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浮生未歇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衣露申 生於80年代。天蠍座。學過法律,當過教師,目前靠寫字為生。
熱愛八卦,耽於幻想。傳媒大軍裏螻蟻一枚,酷愛睡覺和打麻將,人生最大理想就是將兩者結閤為一體。寫故事,純粹興之所至,消遣自己,娛樂旁人。
衣露申,英文的illusion,意思是,幻覺。
衣露申,不過是美好的托詞。那些我們斷然不信的東西都可稱為衣露申,那些讓我們沉溺不醒的夢也是衣露申。誰說文字又不是一種幻覺?
什麼見字如見人,什麼立此存照,統統都是衣露申。
已齣版作品:《我們都辜負瞭愛》《開到荼靡花事瞭》《一捧玫瑰灰》《假使從未墮落》
浮生未歇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浮生未歇》內容簡介:人一身渾濁,卻在身外尋找淨土,憤怒這世界的不潔。這座城裏滿是笑話,它是誰的摩耶,又是誰的索多瑪?甘尚川原本是S城紀委書記的掌上明珠,在十八歲之前,她是亦舒筆下的玫瑰,是王菲吟唱的安琪兒,是穿著玻璃鞋的公主。可是,她的人生隨著父親的鋃鐺入獄,母親的驟然發瘋從此改寫。厄運接踵而來,她被騙進瞭S城最奢華的銷金窟——醉生夢死,遇見此生最大的噩夢,S城地下王國的主人陸東皓。一夕之間從天真少女淪為仇人禁臠的甘尚川,經曆羞辱與死亡的洗禮,重生為滿懷仇恨的妖嬈女子。十年後的她,沿著昔日逃亡的路綫迴歸,頂著層層麵具遊走於昔日侮辱、侵害、背負過她的男人之間,嚮他們設下足以顛覆一切的生死迷局。
浮生未歇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點擊這裡下載
發表於2025-01-08
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浮生未歇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醒來時的一記陽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醒來時的一記陽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因為愛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因為愛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倦尋芳(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倦尋芳(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薄暮晨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薄暮晨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金樽幽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金樽幽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客官不可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客官不可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若不是因為愛著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若不是因為愛著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鳳隱天下(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鳳隱天下(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晨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晨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非我傾城(全三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非我傾城(全三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浮生未歇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誰拿流年亂瞭浮生,又藉浮生亂瞭紅塵。此生若能得幸福安穩,誰又願顛沛流離? 不算長的篇章,在小說中“推薦”於我算是較高的評價。 或許會有人認為情節過於劇情化,當然我亦是如此認為。即便如此,卻依然有隻無形的手,牽引著一氣兒讀完。
評分作者不止一次在書中提及對亦舒的喜歡,我隻看過《喜寶》,但亦舒殘酷版愛情是蠻帶感的。 在小說描寫中,一方麵為那些赤裸裸又犀利的字眼感到過癮,一方麵又為那些點到為止留有想象空間的描述激動不已。對女主那段不堪的過去,並沒有濃墨重彩,照理淪落風塵、流離失所都是...
評分政治,是這個故事繞不開的一個話題。這個強硬的話題,讓略微狗血的故事有瞭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背景,為本書加分不少。也許政治這個話題,男人更喜歡。我認為,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抑或是文化,都是政治的延伸,都是為瞭保證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和持續化。
評分看衣露申的文很久瞭,還記得08年看瞭她的第一篇小說《開到荼靡花事瞭》,同樣是高乾文,但裏麵的女主蘇紫至今讓我印象深刻。跟很多曇花一現的作者不一樣的是,衣露申一直都有作品齣來,雖然時間隔得比較久,但每一本都有驚喜。看她的文有種跟著作者一起成長的感覺。
評分十八歲之前的甘尚川想起在天涯上看的一則八卦。有一個留學生爆料,自己的一女同學是當今某當權者的孫女,純潔的如一張白紙,被同一個人騙過好多次還不自知,即使被自己身邊的好友提點、告誡過瞭,卻仍然一如既往地對人好,如果美好的人,連女生都不忍傷害她。即使她的情敵,對...
圖書標籤: 衣露申 浮生未歇 小說 言情 現代言情 都市 網絡小說 現代
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浮生未歇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搞瞭半天我最喜歡的居然是景然 大概同情他失去的最多吧 雖然得到的也不少 但畢竟去者不可留
評分挺好看。
評分捨棄之前的一切,隻為與你共度時光!
評分挺喜歡的一個作者~~求仁得仁的幸福~~~
評分我的菜
浮生未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隻要我還在,隻要你還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隻要我還在,隻要你還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韆零一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韆零一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誰把風聲聽成離彆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誰把風聲聽成離彆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愛情往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愛情往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名流巨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名流巨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泡沫之夏 3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泡沫之夏 3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豪門強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豪門強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隨情所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隨情所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江上芳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江上芳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餘愛繞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餘愛繞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念之差,情動一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念之差,情動一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軟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軟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天驕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驕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不悔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不悔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絲絲扣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絲絲扣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六十章蜜方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六十章蜜方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原來我們都是愛著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原來我們都是愛著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位女心理師的情感救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位女心理師的情感救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此生不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此生不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時間浪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時間浪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