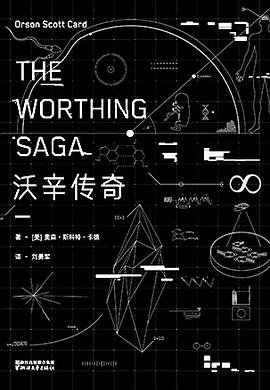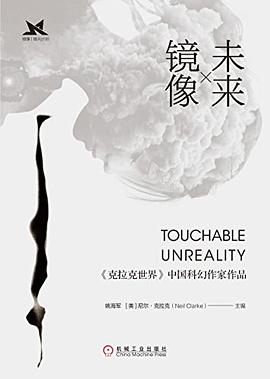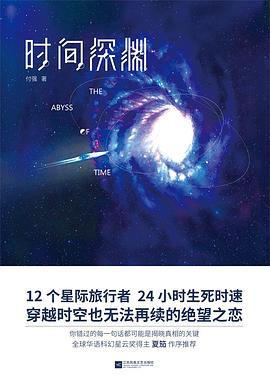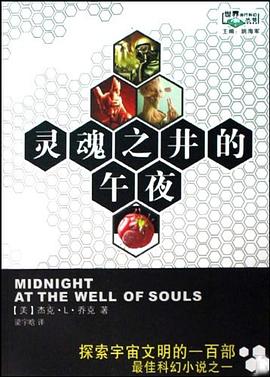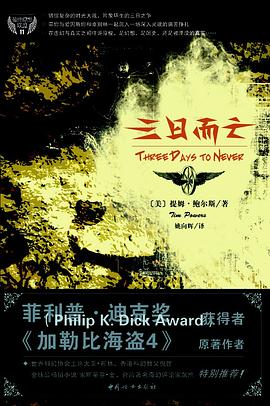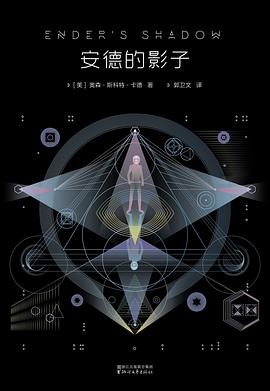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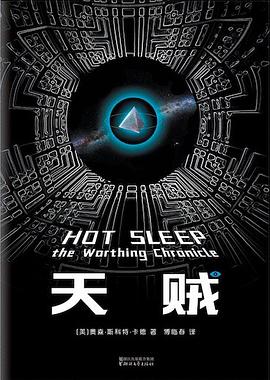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天賊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奧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 】
★1951年齣生於華盛頓州。在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長大。
美國作傢、評論傢、公眾演說傢、散文作傢、專欄作傢、
反對同性婚姻的政治傢,同時也是摩爾門教擁護者和終身執業成員。
當今美國科幻界最受人矚目的 人物之一。
美國科幻史上唯一兩年內連續兩次將“雨果奬”和“星雲奬”兩大科幻奬盡收囊中的作者。
★作為科幻小說傢十分多産,共有12個係列, 《天賊》是他首部科幻小說。
目前和妻子一起定居於北卡羅來納州,為當地一份報紙撰寫專欄文章,
空餘時間在陽颱上喂養鳥、鬆鼠、花栗鼠、負鼠和浣熊。
★代錶作:
《天賊》
《沃辛傳奇》
《安德的遊戲》
《安德的代言》
《安德的影子》
《背叛之星》
天賊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內容簡介】
詹森·沃辛有一雙可以看穿人類心靈的藍色眼睛,
他的天賦讓他被選中,成為一名星艦艦長,
帶領其他333人,穿越星際去創造一個新世界……
沃辛的故事是卡德希望韆萬不要絕版的故事。
《天賊》是他第一本科幻小說, 此後,他開始瞭長達12年關於沃辛的寫作;
沃辛之後,安德的故事纔問世。
【編輯推薦】
《天賊》是《安德的遊戲》的作者奧森·斯科特·卡德的科幻處女作;
卡德所有創作的初心; 他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天賊》的影子。
【名人推薦】
我所有的故事始於天賊。——奧森·斯科特·卡德
天賊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29
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天賊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沃辛傳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沃辛傳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背叛之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背叛之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安德的禮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安德的禮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消失的殖民星球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消失的殖民星球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未來的序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未來的序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上帝眼中的微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上帝眼中的微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聖迭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聖迭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安德的遊戲·三部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安德的遊戲·三部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陶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陶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獵人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獵人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賊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著名科幻小說傢奧森•斯科特•卡德是美國科幻史上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是唯一一位在兩年內,以《安德的遊戲》和《死者代言人》蟬聯“雨果奬”和“星雲奬”兩大科幻奬的作傢。《天賊》正是開啓他科幻之路的處女作,卡德錶示:“我所有的故事始於天賊。” 作為科幻小說傢,...
評分《天賊》是卡德的最早期作品之一,正如卡德自己所說“所有的靈感都源於《天賊》”,因此這本書也帶有著強烈的作者個人風格,另外,該作品創作於1979年,限製於於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很多在當時讀起來非常“高新”的科學技術描寫已經於現代社會成為現實,(恰如卡德本人在《如...
評分你說到讀者讀的是經過譯者詮釋的故事,我對這個方麵也深有同感。 我喜歡把自己翻譯的過程比作“乘坐肥皂泡在作者的世界裏飛行”,各種光綫都會影響我的視野,我所見的世界未必是它真正的樣子,我隻能盡最大努力去體會它。 偶爾肥皂泡的錶麵會接觸到一片湖水,和水麵融閤。那隻...
評分著名科幻小說傢奧森•斯科特•卡德是美國科幻史上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是唯一一位在兩年內,以《安德的遊戲》和《死者代言人》蟬聯“雨果奬”和“星雲奬”兩大科幻奬的作傢。《天賊》正是開啓他科幻之路的處女作,卡德錶示:“我所有的故事始於天賊。” 作為科幻小說傢,...
評分你說到讀者讀的是經過譯者詮釋的故事,我對這個方麵也深有同感。 我喜歡把自己翻譯的過程比作“乘坐肥皂泡在作者的世界裏飛行”,各種光綫都會影響我的視野,我所見的世界未必是它真正的樣子,我隻能盡最大努力去體會它。 偶爾肥皂泡的錶麵會接觸到一片湖水,和水麵融閤。那隻...
圖書標籤: 科幻 奧森·斯科特·卡德 科幻小說 美國 小說 好書,值得一讀 我想讀這本書 想讀,一定很精彩!
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賊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安德的影子,卡德好喜歡寫天纔,這下寫瞭一個族群
評分卡德的科幻小說一貫是主角光環太強,再加上各種不顧邏輯的開掛。不講理的小說是經受不起時間考驗的。這種“特色風格”從他的第一部SF《天賊》就很明顯瞭,到《安德的遊戲》成瞭“集大成”之作。作為資深與狂熱的摩門教徒,卡德的政治理念與哲學觀點看似廣博寬容,實則狹隘無比。
評分開始的情節依稀有基地的影子,不過後半部分和科幻沒啥關係瞭,但還是個不錯的故事。
評分力薦
評分卡德的沃辛係列
天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蠱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蠱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宇宙墓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宇宙墓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玩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玩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菲利普·迪剋的電子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菲利普·迪剋的電子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未來鏡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未來鏡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重生之超級戰艦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重生之超級戰艦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時間深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時間深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活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活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少年衛斯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少年衛斯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靈魂之井的午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靈魂之井的午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三日而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三日而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血音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血音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叢林之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叢林之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我,機器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機器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安德的影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安德的影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小靈通漫遊未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小靈通漫遊未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迷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迷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威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威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影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影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地底奇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地底奇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