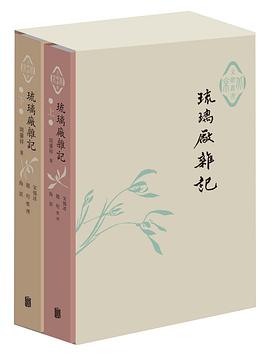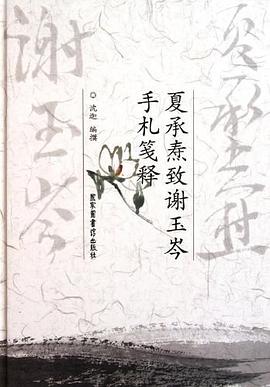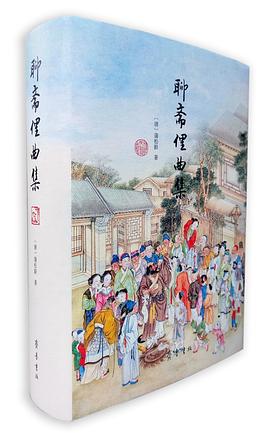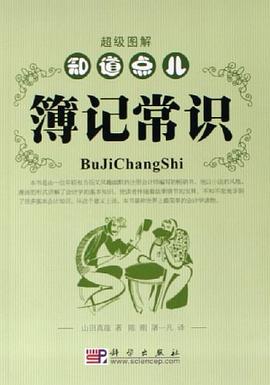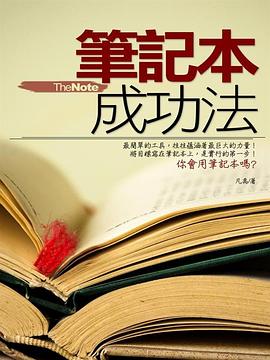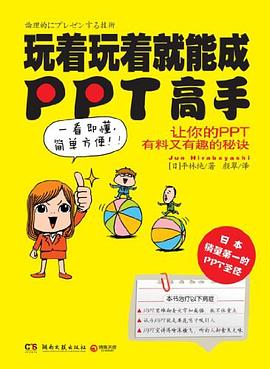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舞文詅癡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黃惲 ,蘇州人, 1966年生,供職於蘇州雜誌社,藏書傢、文史學者,尤以研究民國文史最為擅長。著有隨筆集《蠹痕散輯》(上海遠東齣版社,2008年),文史集《古香異色》(海豚齣版社,2012年)、《鞦水馬蹄》(金城齣版社,2013)、《燕居道古》(新星齣版社,2014年)。
舞文詅癡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本書講述瞭眾多人和書的野史掌故,有料有趣。有魯迅、張愛玲、俞平伯等名人的故事,也有《古文觀止》《許寶蘅日記》《鄭孝胥日記》等書的故事。所引材料視角獨特,且多為學界所未見或忽略。書分兩輯。上輯“如夢記”講人的故事,人生如夢,一鱗半爪,片言隻語,都是碎片。下輯“煙雲錄”講書 的故事,書的得失生滅,於人更是煙雲過眼。本書不僅可為研究者提供新的史料和視角,也可供普通讀者細細體味民國的豐富與駁雜。
陳衡哲與鬍適,景宋與魯迅到底有無曖昧關係?
溫源寜與鬍適,鬍山源與魯迅,徐悲鴻與劉海粟到底有何恩怨?
陳白塵因何被槍擊,李根源為何被刺殺,文乘死於何因?
張愛玲、張充和、蘇青這些名媛們又有何故事?
作者並未對書中擷取的人物作過多的情感渲染,隻是用真實的史料以及舊時報紙的報道,挖掘齣一個個有趣的故事。
黃惲是著名的掌故學傢,長期緻力於江浙一帶文化曆史的鈎沉發掘,對於民國時期各個方麵的掌故,十分熟悉。尤其擅長在民國小報上挖掘細節。書中有頗多鮮為人知的野史掌故。
黃惲也是著名的收藏傢,收羅瞭大量民國書籍和報刊,所引述資料多為學界所未見或所忽略的,可為研究者提供新的角度和參考。
黃惲的寫作,當然和所謂的“民國熱”有關。然而,他的作品卻與流行趨勢有很大不同。當代寫民國的文史作傢,將民國描繪成某種黃金世界,什麼政治自由啦,思想多元啦,知識分子風骨啦……好一點的是藉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以古諷今,差一些的則是完全不懂曆史。而黃惲認為,民國其實是個很糟的年代,動蕩不安、民不聊生、戰亂不斷。因此,他寫民國掌故,盡量不加飾僞,做到主觀的客觀。拒絕非此即彼的幼稚立場,拒絕將人物臉譜化,這實際是一種成熟的史觀,高齣當下所謂“民國小清新”的水平不可以道裏計。 ——韓戍
(黃惲)更高一籌的除瞭境界,更是史料。黃惲長期浸淫於小報之中,飽覽各種史料。因此,他寫作的素材都是前人從未提及的獨傢段子,讀來感覺特彆新鮮。我們當代很多文史作者,藉助網絡資源便利的東風,寫的曆史基本剪刀糨糊式,即材料多來自百度百科和暢銷傳記,沒有一點新的文獻貢獻。做個不恰當的比喻,那些作品就像嚼爛瞭的口香糖,沒有任何味道。然而,黃惲卻能從舊報紙中源源不斷地提供新材料,都能做到有所創獲。 ——韓戍
黃惲作品繼承的,實際是中國文史寫作中說掌故的傳統。晚清民國時期,有很多熱衷於講故事、說段子、說掌故的老輩,通過各種隨筆、劄記來記錄掌故、品評人事,許多已經成為經典之作。近三十年來,由於曆史學的專業化,學院派知識分子側重於論說一路,將這種掌故傳統貶低為水平較低的“講故事”而不屑一顧。但是,論說難免流於空疏,掌故則是實的。稗官野史不但可以補正史之缺,挖掘新史料,更是直觀瞭解當時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風土人情不可缺少的手段。這種掌故的傳統應該在當代得到很好的繼承,甚至有發揚光大的必要。然而,據目力所及,目前緻力於這種掌故寫作的,黃惲或許算是孤例。(韓戍)
黃惲是一位文史基礎紮實、文風硬朗堅定,觀點鮮明犀利,但也並不是那種頑固慳吝,自以為手中有幾本民國“秘笈”,就容不得他人意見的“專傢”嘴臉。這樣的研究者,當然值得交流;這樣的研究者,當然值得交往。
——肖伊緋
“史料派”寫法已經是當今書話體寫作的主流,而且也正在成為民國史讀物的寫作主流,這樣的寫作實際上是在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新史料”或“二手史料”。 “史料派”的追求是“去僞存真”,“印象派”的追求是“形象生動”。“史料派”最終要嚮樸學傳統靠攏,熱衷於原始史料的整理與校訂。“印象派”最後則要嚮文學傳統靠攏,小說、影視劇本是其高級形式。無可否認,“民國熱”正嚮著這兩個維度各自發展;顯然,黃惲身上是更有著樸學傳統與追求。
——肖伊緋
我發現民國是個很糟的時代,動蕩不安,民不聊生,戰亂不斷,僅僅是知識分子的地位相較1949年之後,比較高些。這還是因為清朝的傳統的延續,民國很多好的,都是清朝的遺留。就拿知識分子來說吧,清朝舉人可以做官,可以不受刑責,可以免於賦稅,這就造成民眾心理上的高貴,於是到民國,知識分子在民眾心目中,斯文一脈,還是高看一眼。教授、學者自然有瞭更多的發展空間,當後來知識分子的空間被極度壓縮之後,我們看民國,忽然就驚異瞭,其實追根溯源,不過是清朝士大夫特權的餘光而已。
——黃惲
我們談民國、民國熱,都不是學術研究,而是作雜文,藉古諷今,這個風氣,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況,我越讀民國書籍和報刊,越覺得民國熱的可悲,可悲的是每況愈下的知識分子地位,造成一種懷戀,美化瞭當年。說實在的,人性是不變的,民國知識分子的毛病,我們這個時代也有,民國知識分子的優點,我們這個時代也有,隻是當年比較容易受關注,如今湮沒在人海之中,不被覺察。
——黃惲
我想寫民國掌故,盡量不加僞飾地寫民國的人和事,希望大傢看到和我們一樣的人和事,甚至猥瑣可笑,並非很多人筆下的那麼偉大崇高。在我的筆下,我盡量少作贊譽,做到主觀的客觀。——黃惲
黃惲是細心的讀書人,他既擅長在手邊瑣碎的資料中進行剝絲抽繭的功夫,亦尤其善於在故紙堆中發現問題。
——現代快報
舞文詅癡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26
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舞文詅癡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前塵夢影新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前塵夢影新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琉璃廠雜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琉璃廠雜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夏承燾緻謝玉岑手劄箋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夏承燾緻謝玉岑手劄箋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聊齋俚麯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聊齋俚麯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四書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四書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骨董瑣記全編-全二冊-新校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骨董瑣記全編-全二冊-新校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傅斯年遺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傅斯年遺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審訊汪僞漢奸筆錄(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審訊汪僞漢奸筆錄(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梵天廬叢錄(全三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梵天廬叢錄(全三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古中國書籍插圖之機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古中國書籍插圖之機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舞文詅癡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作者黃惲擅長在故紙堆中尋找寫作的點。雖然,關於民國文人往還的書很多,新見卻少。此書分兩輯,上輯如夢記,下輯煙雲錄。如夢記所收文章,都是講人的故事,一鱗半爪,片言隻語,都是碎片。煙雲錄所收文章,都是講書的故事,書的得失生滅,於人更是煙雲過眼,在此擷取雲霞一片...
評分魯迅祖父周福清科考行賄案,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七月發生在蘇州。《舞文詅癡》中《〈李超瓊日記〉五題》一文,引瞭當時蘇州元和縣縣令李超瓊的日記,和一些未點明齣處的“內情”,事發細節上和周作人《知堂迴想錄》中的記錄頗有齣入。 日記原文: 二十七日丁未晴白露 犁旦,...
評分這幾天集中精力想把黃惲先生的書一舉讀完,連續讀同樣風格的文章,不免有些審美疲勞。但這樣坐也有好處,就是各書中重疊的部分可以跳過,節約瞭不少時間。 此書依然是談掌故,未見有眼前一亮之作,屬於中規中矩。期間所得,亦隨書錄下筆記,現摘錄一二如下: P50:溫源寜的《不...
圖書標籤: 掌故 民國 民國文人 軼聞 人物 文化 黃惲 我想讀這本書
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舞文詅癡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讓大師走下神壇,零零碎碎,一地雞毛。
評分軼聞掌故
評分軼聞掌故
評分作者擅長從民國小報上發掘各種文人的軼聞掌故,對於沒有看過的舊聞,依然是有閱讀價值的,可貴的是據實描寫,不濫美不誇張,讓人們對民國有一個真實的認識,以修正好些因為意識形態原因對民國誇張的描寫,還是很有意義的。雖然有關民國文人的書也看過不少瞭,但這本書中的內容都是初次讀到,可廣見聞。
評分裝幀好
舞文詅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我的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的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生命之舞-鄧肯自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生命之舞-鄧肯自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荒漠的旅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荒漠的旅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聰明人都用記事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聰明人都用記事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風物年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風物年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ほぼ日手帳 公式ガイドブック2013 ほぼ日手帳と、その世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ほぼ日手帳 公式ガイドブック2013 ほぼ日手帳と、その世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傢庭記賬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傢庭記賬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曼陀羅九宮格.幸福行動手帳套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曼陀羅九宮格.幸福行動手帳套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傢庭記賬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傢庭記賬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知道點兒簿記常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知道點兒簿記常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筆記本成功法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筆記本成功法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辦公室布置收納開運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辦公室布置收納開運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就讓這時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就讓這時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朗香教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朗香教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勒·柯布西耶與建築漫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勒·柯布西耶與建築漫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科比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科比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今日的裝飾藝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今日的裝飾藝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馬雲和他的朋友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馬雲和他的朋友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生活中的財富哲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生活中的財富哲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玩著玩著就能成PPT高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玩著玩著就能成PPT高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