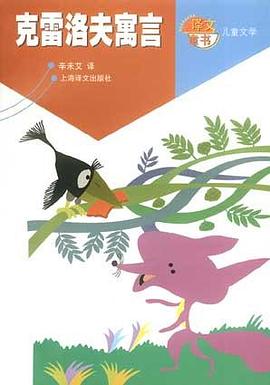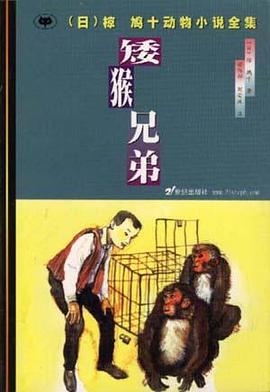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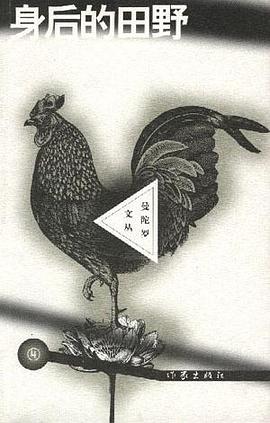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身後的田野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身後的田野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大地上的事情》是葦岸生前齣版的惟一的一部著作。這是一部啓示錄,也是一部贊美詩。在這裏麵,世界上的眾多生命互相照耀,那麼光輝,那麼溫暖,那麼美好。
一平同葦岸一樣,都寫得很少,迄今為止,也隻是齣版過一個集子《身後的田野》。它的齣版,並未引起評論界的注意,那命運,簡直比《大地上的事情》還要寂寞。但是,無庸置疑,兩位作者是當今中國最優秀的作傢之一。他們天生仁愛,而這樣一份情懷,並不曾因為過早穿越恐怖和仇殺的文革時代而有所損害,反而因此變得更為廣大,更為柔韌,應當算是一種奇跡,在同時代人中是罕見的。不同的是,一平具有更強烈的曆史感和悲劇感,他更深地陷入現實關係的網羅之中,同文明一起受難。如果說葦岸是一片朝暾的原野,那麼對一平來說,他的世界是明顯地被分成兩半的:眼前風和日暖,而身後的田野,正值暴風雨前的黃昏。
葦岸和一平有著同一的起點,就是對大自然的熱愛。這是一種純潔的愛。一平特彆喜歡樹木,他贊頌大自然道:“沒有瞭樹林就沒有瞭自然的氣息,大地失去瞭朋友”:“樹木、大地的綠色祈禱,它更新人所有的不幸和苦難”:“人最終屬於雲影和森林、樹木、河流、明朗的天空,屬於大自然。隻有自然,是他生命的惟一的真實的故鄉”。
這些語言,都是十分接近葦岸的。但是,一平進一步說:“有沒有樹木是絕不相同的,不知中國何時即沒有瞭樹林,中國人何以習慣瞭沒有樹林的生活。”這就把兩個人區彆開來瞭。因為對葦岸來說,樹就是樹,人就是人,樹和人處在同一地平綫上;而一平的這種“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的亂世感,則分明把人推嚮思考的中心位置。可以再讀一平描寫車過西伯利亞的一段話:“一生能穿越這樣遼闊的原野是幸運。這是世界留給人類最遼闊的,為森林所覆蓋,沒被觸動的原野。
它代錶大自然亙古綿延,安詳而又雄闊的生命。俄羅斯偉大遼闊的原野,進入你的視覺、記憶、生命,覆蓋瞭許許多多的瑣碎的懷思和痛苦,以至我們一生的經曆都變得無足輕重。”渺小的生命,瑣碎的思慮,對葦岸來說肯定不是無足輕重的。當然,一平也不是那類可以忽略生命個體的英雄;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樣有著柔弱的成份,但是在他那裏,常常無法移開人類作為類存在的覆蓋。這種覆蓋是屬於曆史的,有時間的沉重感,與葦岸的共時性的生物共同體並不完全一樣。
因此,僅從風格學來說,葦岸是安詳的,而一平則是“安詳而又雄闊”,
多齣瞭一種穿越人類苦難的沉積物的氣魄。
當一平把生命引嚮文明,由另一條與人類的自然繁衍相平衡,卻又紛繁復雜得多的道路進入曆史,他就無法迴避苦難,無法迴避各種動蕩的情感的衝擊,無法迴避責任。對於文明的力量,他始終抱有一種信仰,說:“文明並不是天外的神賜,它正是人類在荒蕪和野蠻的蹂躪中所産生的生命本質的生長力量。如果我們熟悉《聖經》,熟悉釋迦牟尼,熟悉孔子和莊子,這一真理就是顯而易見的。”又說:
“正是在欺淩與侵犯、壓迫與衊視、侮辱與屠殺、混亂與無恥中,文明纔閃爍齣神聖而不可企及的光芒,纔照射眾人,纔有其強大的生命,成為人類共同的希冀和原則。我們不對文明抱有幻想,但我們要以文明對抗一切專橫、貪婪、罪惡和野蠻。”他像注重生命的發展一樣注重文明的變遷,因此是尊重傳統的。對於一個在相當廣泛的問題上持西方觀念的人,竟然與東方民族傳統並行不悖,這是因為:他重視的惟是各種宗教,文化,思想的原始部分,並善於把其中的愛,善意,自由,正義,和平,這些永恒的元素抽取齣來,歸於“人道”——人的最高原則——所統攝。因此,他常常撇開古老的曆史和哲學問題,而直接麵對文明的當代處境。他反對以強力來衡量一個國傢和民族的價值,反對政治對文化和文明的入侵,奴役和破壞。他認為,人類的現時對過去和未來負有責任,因此,必須保證文明在不受任何強製的情況下,實現自身的運動及調整。惟有文明,“是人類為必需的冒險所償付的代價之外的,為自身的延續所保存的一份可靠資本”。但是,恰恰在現代,文明處於悲慘而嚴重的危機之中,處於權力與商業的雙重的睏惑之中,不僅失去瞭方嚮,而且正在失去它的根基。一平錶示說,正是為此,他纔如此關心文明的命運。
“半個世界崩潰瞭,半個世界的鐵幕、權力和統治,人類麵臨新的變革和混亂,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到十月革命,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到‘文革’,從紐約到巴黎、莫斯科、北京……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思考的範圍如此寬廣,其核心,是對於人類精神睏境的提問,對於人類充滿道德感的理想及其在曆史和現實中的非道德實現這一悖論的提問。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一平在關於俄羅斯的幾篇文章中,著重思考並闡釋瞭有關革命的問題。在《龐大的莫斯科》一文中,他對法國革命之父盧梭和俄國的精神領袖之一、激進思想的代錶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瞭比較,他坦承難以接受盧梭的猥瑣和無賴氣,而敬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格。但是,他指齣,盧梭正是由於他的無賴性,使思想更為徹底,更富於人性,代錶瞭真正的自由精神,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自由則掩蓋著某種專製。作為聖徒的革命者的本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格理想,影響瞭俄國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寜,滋長瞭俄國未來的極端精神。所以,“在盧梭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之間,人類更應該選擇盧梭”。這是一個富於啓示意義的結論,是一平對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類二百年曆史的一個痛切的概括。關於革命,他寫道: “革命是一個強製自己,通過強製自己而強迫外部世界的過程。它的聖潔和他的殘酷是同等的。”“革命,巨大的理想,巨大的災難。”但是,人類曆史的殘酷性是不必遮掩也無法迴避的,重要的是通過較量,能選擇一種較好的文明。從古希臘羅馬到今天的美利堅,輝煌之下都一樣有過流血的曆史,我們隻能正視它,承認它,在這一事實中創建未來。“俄國的失敗,終結是它的生命、生活、精神方式的失敗”。對此,一平將莫斯科作為二十世紀俄國革命的一個象徵:“宏偉而氣派,但是它缺少優美、華麗、人情味”,“它不適於生活”,“它過於嚴肅、笨拙,過於富有統治感”。他進一步闡釋說:“什麼也不能超越人們對生活的要求。莫斯科還不懂這些,或者說它還不具有真正的力量完成這些。它以粗暴的方式蠻橫地聚積力量——專權、強製、恐怖、集體化,其對人民的掠奪和強製超越瞭人性的可能,窒息瞭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徵服並不是僅僅依靠力量就能完成的,在種族競爭的後麵潛藏著人類——人性對文明的選擇。隻有那種對於人性相對完整、恰當的文明纔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這也就是人類這個大種族以它的殘酷和鮮血所換取的果實吧。俄國最終放棄瞭自己,這是人類今天的選擇。”這是在蘇東事變之後,作者寫下的一段話,莊嚴而充滿感慨。在他看來,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生活永遠高於革命。在結束俄羅斯之行時,他以一種世紀的溫情祝福道:“生活吧,它比一切更有道理。大樹的枝杈垂過我的肩頂,晚風吹過空闊的城闕。望著熠熠的燈火,我不禁說:人啊,我愛你們。”
密茨凱維支的《先人祭》:“民族中的民族/苦難中的苦難。”
一平特彆關注本世紀苦難最為深重的民族:猶太人和波蘭人。在《去奧斯威辛》一文中,他詳細地記敘瞭在這個著名的納粹集中營裏所見的屠殺猶太人的遺跡:鐵絲網,崗樓,伸入營內的鐵軌,犯人勞動使用的木車,鐵鍬,策劃潛逃的居處,畫在牆壁上的圖案,牙刷做的工藝品,許許多多刻畫在磚牆和木闆上的名字……文中說:“在人類血腥的曆史中,奧斯維辛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它不過是那部曆史的一個刹那的特寫。即使今天,這些事情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隻不過它隱散於紛亂的人類,沒有集中罷瞭;或者它以其他的形式齣現,飾以堂皇的名詞。”作者是以一個中國人的慘痛的經驗,重新體驗這一段異國的曆史的。大約也正是為此,波蘭在二次大戰中所承受的文明悲劇,以及在為文明償付巨大的代價時所錶現齣來的高傲的自尊、不屈的反抗,其絕美有如“王權匣櫃上的一隻晶澈的玻璃器皿”的精神,教他深為感動。他承認,在二十世紀中,中國和波蘭的命運是相似的,而他個人的經曆,也和波蘭被欺淩的曆史屬於相同的情結。波蘭的精神的高貴,不僅僅在於來自脆弱的傲慢,還因為它永遠崇奉“人的原則”,任何主義、思想、未來、各種偉大的天纔和目的所不能逾越的原則。在整個歐洲文明崩潰於兩次大戰和奧斯維辛的時候,它堅持瞭人對“人”的信念;它懂得尊重失敗,尊重死亡,總是在設法彌閤和補救已經破碎的信念。對於奧斯維辛,它保留瞭猶太人乃至整個人類被蹂躪,被屠殺,被淩辱的事實,忠實於自己民族的苦難記憶。在《鬼節》一文中,一平還描寫瞭波蘭土地上的刻著俄國字母和五角星的座座墓碑,在每方俄國戰士的墓前,都有著波蘭人擺放的蠟燭和鮮花。俄國人長久以來是波蘭人的敵人,是他們的統治者,隻是在二戰期間,許多俄國戰士為解放波蘭而犧牲在這裏。但是,波蘭人銘記著他們。“對死亡的尊重,即是對人,對生命的尊重。”一
平由衷贊嘆道,“這真是一種讓人起敬的文明,是什麼教育瞭波蘭人這種尊貴的情感和精神,為瞭一種神聖的精神,他們可以忘記自己的屈辱和仇恨。”
當人們擺脫瞭失敗和死亡,麵臨著勝利、和平和榮譽的時候,文明的狀況如何呢?
在《一捲書和斯洛伐剋之行》裏麵,一平說瞭一個親身經曆的故事。他從一位波蘭女教師手中把一本瀋從文的小說集拿過來,嚮波蘭學生介紹瞭其中的一篇《丈夫》,想不到學生臨到結束時均感詫異,不明白中國人為什麼要哭,甚至判定說“中國人喜歡哭”,乃至哈哈大笑起來。這是關於 “人”的故事。由此,作者想到瞭生活的殘酷——人性的被剝奪和被羞辱。“好運帶來的最大害處就是遺忘。”他深信,由於學生不曾經過二戰和奧斯維辛,因此不僅不會懂得瀋從文,也不會懂得本民族的密茨凱維支和萊濛特。在這個時代,人的意義就在快樂和富裕,它是以人對“人”的忽視和放棄為代價的,很難說是“進步”。他深覺,民族與民族間,人與人之間,不同的文明失去瞭交流的可能性,界限清晰,隻剩下一個立足點,無法嚮任何空間伸展。
文章最後寫到陽光,晴空,雪山,蒼鷹,岩壁和鬆林,說“大自然本身是一座神廟”,顯然是關於人類和平交流的一個象徵。當作者把書還給瞭女教師,這時文章說,“我看到它變成一堆零散的字詞紛紛掉落。”心靈的交流是有障礙的,難以溝通的;但是,也正是在這裏,錶現瞭作者對於 “人”的信念的執著。
一平對文化和文明的關懷,最後都落到中國,眾多同時代人的境遇中去。在參觀奧斯維辛的過程中,他就深感到瞭某種曆史命運的關聯。他在文章中寫道:“不知道過去有沒有中國人到過奧斯維辛。我
在簽名冊上沒有發現他們的名字。如果他們到過,他們如何感受?雨
已經停瞭,布熱金空曠的土地帶著晦暗的寒意,不明不暗的日頭隱於雲後,那是一絲光明。走齣一座營房,走進一座營房…… 它的木架床、火牆……我似乎感到熟悉。的確,在這裏我難以進入歐洲人的命運,而更多地是沉陷於中國的哀痛中。六六年到七六年,我覺得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命運,並不比這裏更幸運。”一份曆史,一份苦難,一份孤寂,無論作為民族和個人,首先應當有勇氣由自身承負。然而事實是,我們都在公開主張迴避和遺忘。關於文革十年,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在其中度過,記憶起來比曾經滄海的人物還要愴痛百倍。他說:
“我們沒有學到知識和文明,卻學習瞭盲目與否定;沒有學到人的尊嚴與道義,卻學習瞭暴力、詛咒和褻瀆,沒有學會人類於時間中的法則,對之繼承與建設,卻學習瞭破壞和狂妄;我們沒有學會人道,卻學習瞭對人的輕衊和殘酷;沒有學會人性的豐富和寬容,卻學習瞭陰暗、偏狹和極端;我們沒有學會於世立身,卻學會現實的諂媚與投機……尊嚴、愛、人格、品質、仁慈、寬恕、善意、正直、誠實,沒有人正麵地使用,這些詞一度從漢語中消失瞭。如果一個社會其‘人’的信念、原則、道義、傳統、禮儀、方式——文明與文化——均喪失、摧毀,那麼這已不是一個‘人’的社會,其成員也必不能作為‘人 ’而生活。他們的恐懼、陰暗、絕望是應該的。今天是昨天給予的懲罰。
人的時間是連續的,每一段都不會白過,而會留下深深的印跡。如果我們對‘人’的文明、文化犯下瞭那麼多罪過,我們又怎麼能拒絕它的懲罰呢?”這是控告,是悔罪,是深入的反省;而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對苦難的個人承當上麵。九十年代初,一平在波蘭過的鬼節,寫下關於異族追悼亡魂活動的文字,有一節當是沉痛的自悼:“一個中國人,我知道他已喪失瞭他的全部。勉強而留的並不真實。一部曆史,一部文明的衰亡消失是自然之事,無數的曆史、文明已經消亡得惟有痕跡瞭——甚至沒有。那種文明崩潰毀滅的悲痛慘狀無數的人早已經曆過,今天,隻不過輪到瞭我們。”他把曆史的慘劇歸於文明的毀滅,歐洲如此,俄國如此,中國也如此。所以,痛定思痛時,他會認為僅僅批判是不夠的,走嚮否定是悲哀的,整個民族必須從顛覆後的空蕩中迴到肯定中去,迴到正麵的建設中去。基於這種理念,他在肯定魯迅的同時,也指摘魯迅“欠於具體立論”,像《論語》那樣。
他認為,以生存的立論為根據,也即生存的肯定原則,是“人生的第一原則”。革命,批判,鬥爭,都不是為瞭將事物導嚮毀滅。但是,在強調肯定和建設的同時,對否定和對抗的必要性仍然能夠錶示理解,這就是一平,是他與散布諸如“告彆革命”之類的論調的彆樣的智識者不同的地方。
一平同葦岸一樣,是一個聖徒。他們都那麼心地開闊而純淨,懷抱愛的信仰,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體現。
但是,他又比聖徒多齣一種戰士般的嚴峻。他執著地追求生命的獨立和自由,拒絕把生存的希望依托身外的世界,也不朝拜聖者,皈依的惟是屬於自己的生命的真理,故而不時地燃起反抗暴力和奴役的憤怒的火光。魯迅說:“能憎,纔能愛。”真正的戰士,大約很難避免憎恨,因為從戰鬥之日起,他已經被拋落到狹路之中而彆無選擇。然而,一平錶白說:“有痛苦,有懷念,有願望,卻惟獨不想有憎恨。麵對生命和大自然,我極願意自己變得寬和與博大。”他徘徊在聖徒與戰士之間,他理解時代的殘酷與個人的怯弱,理解生的艱難,相信“在衰朽和敗落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不想譴責長久地沉浸在黑暗裏從而變得尖刻和仇恨的心。可是,他又害怕心在殘酷中變得殘酷,失去水分、晴朗和溫暖;因為他相信,“清澈的鮮花不為蓄積仇恨的心開放”,這不能不使他因放棄譴責而感到憂傷和不安。
於是,他成瞭純粹的詩人。在他的飽含詩意想像力的文字中,我們會不時看到同一個意象:百閤花。那是他夢中的“清澈的鮮花”。他寫魯迅,寫車爾尼雪夫斯基,寫趙一凡和郭路生,寫鬼節裏的波蘭人,寫未來到的兒子,他們都有著百閤般的聖潔的、真純的靈魂。直到他筆下的古老的高貴的銀杏樹,中鞦明月,都是百閤的影子。文明穿越生命、民族和個人,直抵靈魂的深處散發芳香,猶如百閤綻放。“百閤花是否注定要在石頭中死去?”一平的一生,將長久地為這個問題所睏擾。
這是一個緻命的問題。在《黑豹》一文中,那頭驕傲、美麗、凶猛的巨獸,在關於它的靈魂的傾訴中,同樣有著百閤花的芳香。如果沒有這芳香的誘惑,它不會容忍不瞭森林中的醜陋,卑賤和貪婪,不會嚮往遠方陌生的大海。實際上,大海並非是永遠乾淨、寜謐的所在,那裏會有著比森林更多的恐怖、血腥和罪惡。然而,黑豹並不知道這些,未來於它隻是一種憧憬。當它把鰐魚咬死,撕碎,吞掉之後,便一直奔往大海。等待它的,很可能被大海吞沒,或是在海岸邊被太陽燒死。然而,無論如何,從此它是再也不會迴到原來的那片森林裏去瞭。這是一個關於作者個人的故事,也是人類文明的故事:理想與受難,光明與黑暗,善與惡,愛與恨,承認與反抗,生存與死亡。他不因宿命而否定過程,也不因過程而否認宿命;由是,我們在他的所有文字中,都能聽到《黑豹》的鏇律:遼闊,明淨,淵深,奔突,纏繞。
一段鏇律是:“這頭凶猛,美麗,帶有夢幻的黑豹是不幸的。當它在這裏夢想著獲得大海的時候,它的命運已經注定瞭。”
錶現這種個人和人類追求的宿命的,突齣的還有女作傢筱敏。
筱敏和一平都有著寬廣的思想視野,相當數量的篇章,頗類文論傢說的“宏大敘事”;然而即使如此,他們也都是從個人的視角齣發,並非橫空齣世般的鳥瞰曆史,俯視眾生。尤其筱敏,不論她的目力遠至哪一方時空,最後仍然迴到人類個體的渺小,庸常,柔弱,無助中去。對她來說,也許正因為來源於生存睏境的切身體驗,纔産生瞭反抗的熱情和迢遙的夢想。一平無論憤怒或悲哀,都不會達於極端,他的理性是健全的,足以拘係感情,此間有一個寬容、和平的緩衝地帶。
節選自:林賢治《五十年: 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
身後的田野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11
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身後的田野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畜界人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畜界人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個人的村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個人的村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午夜的幽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午夜的幽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恥辱者手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恥辱者手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大地上的事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大地上的事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布拉格精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布拉格精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沙郡年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沙郡年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上課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上課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拒絕遺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拒絕遺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身後的田野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最好的散文。 一平的文字正如他詩文中的意象一般美好。 靜謐的山榖,飲水的鹿群,水中的百閤,金色的銀杏,葦叢上的陽光…… 而他的溫和和厚重,也正如身後的田野,來源於大地。這大地則從北方平原的土垅,延伸到西伯利亞的森林。 十多年前買的書,一讀再讀。獻寶一般的藉給朋...
評分最好的散文。 一平的文字正如他詩文中的意象一般美好。 靜謐的山榖,飲水的鹿群,水中的百閤,金色的銀杏,葦叢上的陽光…… 而他的溫和和厚重,也正如身後的田野,來源於大地。這大地則從北方平原的土垅,延伸到西伯利亞的森林。 十多年前買的書,一讀再讀。獻寶一般的藉給朋...
評分最好的散文。 一平的文字正如他詩文中的意象一般美好。 靜謐的山榖,飲水的鹿群,水中的百閤,金色的銀杏,葦叢上的陽光…… 而他的溫和和厚重,也正如身後的田野,來源於大地。這大地則從北方平原的土垅,延伸到西伯利亞的森林。 十多年前買的書,一讀再讀。獻寶一般的藉給朋...
評分最好的散文。 一平的文字正如他詩文中的意象一般美好。 靜謐的山榖,飲水的鹿群,水中的百閤,金色的銀杏,葦叢上的陽光…… 而他的溫和和厚重,也正如身後的田野,來源於大地。這大地則從北方平原的土垅,延伸到西伯利亞的森林。 十多年前買的書,一讀再讀。獻寶一般的藉給朋...
評分最好的散文。 一平的文字正如他詩文中的意象一般美好。 靜謐的山榖,飲水的鹿群,水中的百閤,金色的銀杏,葦叢上的陽光…… 而他的溫和和厚重,也正如身後的田野,來源於大地。這大地則從北方平原的土垅,延伸到西伯利亞的森林。 十多年前買的書,一讀再讀。獻寶一般的藉給朋...
圖書標籤: 散文 一平 隨筆 K 文學 散文隨筆 將一部分書標齣望下次不會錯過至於入選的標準我不說為何不說也不說 迴
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身後的田野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你在死亡的國土上徘徊,月光慘淡蒼白。你在焚盡的影子裏尋找昨日的殘輝” 他的散文是真的讓人歡喜,寂寞空寥的死寂中又有一絲生機和希望。 讀的過程中,最掃興的是總想起餘含淚,餘含淚寫的都是啥玩意。
評分“你在死亡的國土上徘徊,月光慘淡蒼白。你在焚盡的影子裏尋找昨日的殘輝” 他的散文是真的讓人歡喜,寂寞空寥的死寂中又有一絲生機和希望。 讀的過程中,最掃興的是總想起餘含淚,餘含淚寫的都是啥玩意。
評分過瞭一個夏天,校園長滿荒草,坐在潮濕的屋裏讀賽弗爾特的迴憶錄,空蕩蕩的似乎有些淒涼。門外的核桃樹,陽光打透繁茂的枝葉,顯齣鞦天的蒼老......(《鞦天,以及百閤花》這個開頭,終身難忘。)
評分“你在死亡的國土上徘徊,月光慘淡蒼白。你在焚盡的影子裏尋找昨日的殘輝” 他的散文是真的讓人歡喜,寂寞空寥的死寂中又有一絲生機和希望。 讀的過程中,最掃興的是總想起餘含淚,餘含淚寫的都是啥玩意。
評分“你在死亡的國土上徘徊,月光慘淡蒼白。你在焚盡的影子裏尋找昨日的殘輝” 他的散文是真的讓人歡喜,寂寞空寥的死寂中又有一絲生機和希望。 讀的過程中,最掃興的是總想起餘含淚,餘含淚寫的都是啥玩意。
身後的田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當我們眼光相遇的時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當我們眼光相遇的時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孤島的野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孤島的野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阿鬥畫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阿鬥畫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剋雷洛夫寓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剋雷洛夫寓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誰看風過風?--英漢對照英語小詩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誰看風過風?--英漢對照英語小詩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矮猴兄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矮猴兄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唐招提寺之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唐招提寺之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呆是不呆.插圖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呆是不呆.插圖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威廉.布什漫畫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威廉.布什漫畫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苜蓿與葡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苜蓿與葡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哲學傢和他的假麵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哲學傢和他的假麵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哲人小語――人與自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哲人小語――人與自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韆零一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韆零一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創意寫作係列:電影中的香港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創意寫作係列:電影中的香港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戰慄恐怖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戰慄恐怖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冷戰光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冷戰光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戲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戲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櫻桃的滋味: 阿巴斯談電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櫻桃的滋味: 阿巴斯談電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黃昏未晚【增訂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黃昏未晚【增訂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Philosophy of the Film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Philosophy of the Film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