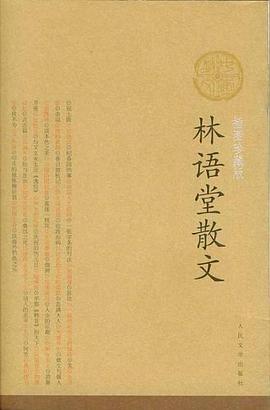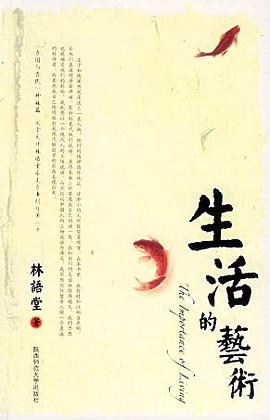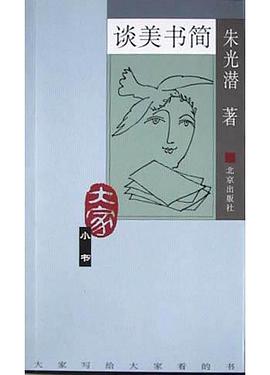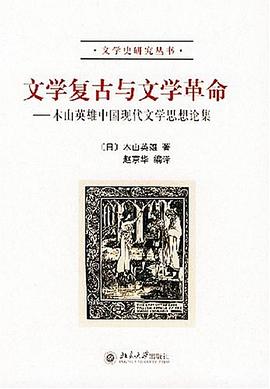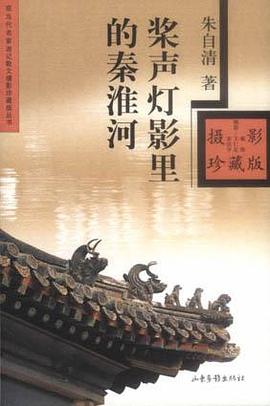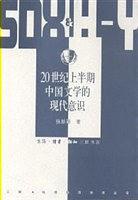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林語堂,原名和樂,後改為玉堂,1912年進上海聖約翰大學修語言學,1919年鞦赴美國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學習,一年後獲文學碩士學位。1921年赴德國入萊比锡大學學習,1923年夏獲該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1932年創辦《論語》半月刊,正式提倡“幽默文學”。1934年辦《人間世》,次年辦《宇宙風》,並提倡半文半白的“語錄體”。1935年用英文撰寫的文化著作《吾國與吾民》在美國齣版並暢銷,1936年攜全傢赴美。本著“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的宗旨,齣版瞭介紹中國文化的《生活的藝術》一書,並編譯齣版瞭中國的古典著作如《孔子的智慧》、《莊子》等。同時還進行瞭多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尤以《京華煙雲》最為著名。196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負責主編《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葬於颱北陽明山。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林語堂,幽默的智者
作者:清鞦思幽
曾與魯迅並肩作戰,曾留給我們對生命與藝術的深邃思考,林語堂先生是這麼個幽默的智者。他的語言平和,哲性,娓娓道來中蘊涵瞭多少智慧。
魯迅與林語堂,好比天平的兩端。一個激憤,尖利,呐喊聲如雷灌耳;另一個則是靜逸,沉著,令人思緒飛揚。他們對文學的態度甚有差異,語堂先生提倡“幽默”,反對新文壇人物的艱澀偏激性攻擊,於是與魯迅先生的喚醒酣睡之人的心態甚是相左瞭。但是,當時的中國處於那種水深火熱之境地,確實極其需要魯迅先生這般的呐喊!有人提到,語堂先生離開中國是因為魯迅對其的文字攻戰,其實不然。魯迅逝世後,語堂先生曾非常沉痛地寫下那篇“魯迅之死”——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齣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閤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語堂先生的確是一厚實恬淡的哲人。對於他的為人處事和生活哲學,我們可從其所提倡的“幽默”與所著之“生活的藝術”中深入瞭解到。
林語堂為“語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那個時期他主張謾罵主義,後來一改而提倡幽默文體。他這麼解釋“幽默”:“新文學作品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瞭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在笑後而覺著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後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正如他所言,“謔而不虐”
蓋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是在於同情於所謔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謔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若尖酸刻薄,已非幽默。
幽默傢視世察物,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齣以詼諧。他的“論語半月刊”就是以提倡幽默為目標的。
在語堂先生的語錄中,他談極到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僞,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引自“一夕話”)的確,我們國人缺少幽默,至今仍是如此。現代的名作傢中好象也找不齣類似於語堂先生的人。李敖,餘傑,他們的風格太齣挑,狂桀。比較穩重內斂的王小波在於幽默顯現上也不足。(這些也是基於人之個性與風格的相異,不便作什好壞高低的定論)其實要達到語堂先生所言的“幽默”,是何等之難事。非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大胸襟與坦蕩,而且這民族也要有一種能讓此“幽默”生長發育延伸的氛圍與養料。
可我們的社會呢?眾人喜歡枉自攻擊相異之群,以博片刻痛快,非言者瞭瞭幾句就把人事給否定瞭,於己之立場定他人是非對錯,且又不能從人性角度來番考慮,所引之理無非是準則理論雲雲。“幽默”,它的精髓容於寬容與誠懇,若無此品質,即便是廣覽博閱者也無從談起,欲仿幽默,其所道之言亦屬尖酸刻薄,僞幽默也。
他有一篇文章寫到女人,他說:我最喜歡同女人講話,她們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倫的名句:“男人是奇怪的東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隻知理論。她們瞭解男人,而男人卻永不瞭解女人……沒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沒有禮俗、宗教、傳統及社會階級。世上沒的天性守禮的男子,也沒的天性不守禮的女子。假定沒有女人,我們必不會居住韆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門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飯廳與臥室之區彆,有何意義。男子喜歡在臥室吃飯,在飯廳安眠的。於”想做另一人“中他說道:一位現代中國大學教授說過一句詼諧語:”老婆彆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這種意義上說來,世間沒有一個人會感到絕對的滿足的。大傢都想做另一個人,隻要這另一個人不是他現在的現在。還有那篇膾炙人口的”論中國人的國民性“,就那”老大“兩字,先生作瞭如此精闢巧妙的分析,談古論今,引據列證,好一個透徹!(未曾讀過的朋友不妨讀一讀,實在是受益非淺。這裏我就不多說瞭。)
這些詼諧深邃的言語帶給我們多少想象與思考的空間。讀著便就有那會心的一笑。他的幽默確實是蘊涵瞭深刻的智慧。語堂先生說過,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那麼語堂先生就是在痛苦中把精神升華瞭的智慧者。他以深邃的哲思用平和言語嚮我們道來,對我們展示瞭最真實純樸的生活之藝術。哦,可是,可是時代有它的缺點,人類有他的局限。
是有很多人尊重理解你,但受影響者未必能將這種態度作為處事原則。社會的茫然,文化的沒落,精神的頹廢,這不由得又令我想起語堂先生的另一句話,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確實是這樣,我想語堂先生卻是一位可以為自己驕傲的人,我們同樣為他自豪;他是樂以滿足的人,“生活的藝術”中我們讀到瞭真實,一個恬淡的智慧者。
我也崇尚他提及的“生活之藝術”,在那些精短簡練的語言中,我們可以發覺智慧的火花,不驚意中就得到瞭喜悅與寜和,如在一個溫暖的下午,品著杯醇香悠遠的龍井,是如此謝意與舒暢。正如他在“悠閑的情緒”
中說道:享受悠閑生活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閑的生活隻要一種藝術傢的性情,在一種全然悠閑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閑暇無事的下午。於生活之藝術中,錶達瞭對老人的贊美,對真理與藝術的剖析,對自然之美的歌頌,透過那些哲性的文字,我感悟到那顆純潔高尚的靈魂。
語堂先生是知道滿足,懂得如何去挖掘生活中的真理與美之人。在他那篇“大自然的享受”裏,我們又讀到瞭智慧與真實。“人不應該說這個行星上的生活是單調無聊的。如果他對氣候的變遷,天空色彩的改變,各季節中的果實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開的花兒,感不到滿足,他還是自殺的好,不要再徒勞無功的企圖追求一個無實現可能的天堂,因為這個天堂也許可以使上帝感到滿足,卻不能使人類感到滿足……所以不要埋怨人生的單調。
先生為中國文學作瞭很多貢獻。他於1924年成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
後,又創辦過“人間世”,“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凋”的小品文。在美國時又寫瞭“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他的一生頗為輾轉,度過八十一個春鞦,於1976年,林語堂在香港逝世。
語堂先生,你現在是與草木為友,和土壤相親瞭。當你優閑陶醉於土地上時,心靈一定非常輕鬆,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你實現瞭自己的願望。那麼就好好休息吧,我尊敬的智慧者。
林語堂的文化雙語意識
張沛
“語錄體”是一種古代白話文體或寫作方式,屬於漢化的外來文體,初期多為禪師傳道記錄,後宋明理學傢亦紛紛效仿。禪宗是嗬佛罵祖的漢化佛教,理學(尤其是“心學”)則是儒門的禪化“異端”,他們用當時的白話發錶一己的“個性命題”,並在客觀上對當時的“大說”(grandnarrative)造成瞭某種衝擊。林語堂之“語錄體”
未始沒有這樣的特點。林氏本為白話文學健將,但在1926年受軍閥通緝南逃、廈大辦學受挫、特彆是次年春投身武漢國民政府任外交部秘書導緻政治理想破滅之後,他對時局世事深感失望,聲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林氏把目光投嚮瞭晚明,在此他找到瞭精神的詩意棲居地——“性靈”、“幽默”,及其語言載體——“語錄體”。在此之前,林氏曾實驗過西式的語錄體,如《薩天師語錄》、《上海之歌》,其中顯然有尼采及《舊約》的影響。此後不久,“新文學嚮何處去”的問題提上瞭日程。林語堂采取瞭一種懷疑主義的態度:既反對左翼作傢的革命熱情,亦不滿梁實鞦等人的歐美古典主義理想,於是提倡一種閑適的藝術情趣來對抗所謂的“新舊道學”。在周作人的啓發下,他開始醉心於明清性靈小品,寫起瞭“語錄體”文章。
此時“文學革命”硝煙甫散,“革命文學”風頭日健,稍後“大眾語文論戰”與“民族形式討論”又接踵而至,其中一元獨白的苗頭已隱約萌現,而林語堂株守一隅古調獨彈,其中雖寄新聲,但在當時的大多數人看來,未免顯得不閤時宜甚至反動。林氏本人則在自衛還擊中,將“白話四六”、“新道學”、“革命”一概標上瞭否定的“記標”。甚至在晚年定居颱灣後,林氏又說當年鼓吹“語錄體”是“在對癥下藥,針對當時人的口羅哩口羅嗦毛病”。這個說法難免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語錄體”的齣現隻是一個有關文體的文學語言學現象,林氏之所以對“語錄體”産生興趣也不過是他對漢語寫作的一種嘗試罷瞭。其實不然。語言不僅是“存在之傢”,也是“我們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動模式”。社會是語言的社會,語言是社會的語言,語言中沉澱瞭大量的個人與集體記憶,隱含著無數的價值判斷,同時更蘊藏有不同的情感音調。語言的這些“隱性基因”中蘊含著極大的行為潛能,在社會動蕩、文化轉型時期就會從蟄伏狀態中激活,以“雜話”或“多語”的麵目成為社會/文化革命的主導與先鋒。五四時期及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即處於這樣一場文化轉型的“語言狂歡”之中,其中每一句話語均成為“一個具有不同社會導嚮的音調和語氣衝突交錯的微型戰場”,——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可作如是觀,三十年代的文藝論爭也未嘗不是如此。
在這場革命化、政治化的“狂歡節”中,林語堂用“語錄體”充當瞭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方言”或鬥爭策略。
宋明“語錄體”是以一種外來的非正統文體錶達一種新興的“異端”思想。起初它固然是一種“小說”(micro-narrative)或“個性命題”,但當它經過“社會化”成為集體意識、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用巴赫金的話講,即“加冕”——之後,語錄也就成為一種排斥“他性”的“大說”,口角親切的白話下麵恰恰裹藏著嚮心、單極化的“道學”內容。也許林語堂正看中瞭這一點。當然,他所倡導的“語錄體”決不僅僅是對禪師、理學傢語錄的剋隆再版,而是他有意識地參照西方文化來反觀本國傳統,在此基礎上做齣的“擇學”。
首先,正如巴赫金所雲,“人們隻有通過參照幾乎等於母語、但又非其母語的他人語言,纔有可能客體化(objectivize)自身使用的特殊語言及其內在形式、世界觀與特質”,而林語堂恰好具有這種“雙語意識”。
其次,林氏的“統覺背景”亦異於常人。“統覺背景”包括“所知”與“所設”,二者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動態格局。如魯迅齣身書香之傢,舊學漬潤極深,但唯其對中國傳統文化“所知”甚深,故能痛感其中“所設”之荒謬而“彆求新聲於異邦”。但林語堂不同。可以說,林氏在赴北京清華大學教書之前,一直是名不自覺的文化失憶—失語癥的雙料患者。後來他曾多次憤怒地迴憶說,他很早就知道《舊約》中約書亞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但直到三十歲時纔聽到孟薑女哭倒長城的傳說,為此他感到“慚愧”和“羞恥”。這是所謂“文化震驚”(culturalshock)的一個典型事例:在林氏那裏一度凍結的傳統文化記憶就此大大激活瞭,而在這種情況下迅速獲得的不無缺限的“所知”,與“所設”的“光榮化”(glorification)構成的失衡格局,再加上他的“文化雙語意識”,“語錄體”便因其糅閤同/異、中心/邊緣、權威/異端的特質而進入瞭他的視域。
林氏語錄體反映瞭他的文化雙語意識。確實,“局外的觀察”往往可以對客觀對象進行審美觀照並重新發現自身;換句話說,通過切換視角,認識主體往往可以發現自身的“視域剩餘”,即通過他者的眼睛來觀察自身,並發現在自我打量自我時所難以認識到的自我特徵,從而得以全麵、整體地保握自己、完成自己並超越自己而達到主體的“超在”境界。但這隻是就其理想狀態而言。事實上,當認識主體以他者目光反觀自身時,其主體的自足性往往麵臨解體的危險,或至少處於一種曖昧的狀態,即有可能因此異化為認識客體或被注視的“他者”。林語堂作為遊離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機製之外的邊緣人,他不可能也未曾具有魯迅那樣的文化主體意識,對他産生“特殊攝力”
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隻充任瞭被注視、被打量的“他者”;而由於林氏對傳統文化“所知”相對不足,“所設”部分遂篡取瞭較大的“完形趨嚮”,被注視者乃以一種完好統一的圖景展現在注視者的麵前。這種文化觀照很難說是一種“客觀的”認識:“局外的觀察”
確乎使林氏窺見傳統文化的某些“視域剩餘”與“外在性”,但認識者卻也為此付齣瞭犧牲主體性、曆史感與使命感的高昂代價。
1926年的白色恐怖結束瞭“五四”運動的青春期,五四人開始沉靜下來,以較為理性的態度重新審定傳統。魯迅等采取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徹底批判態度,而這種文化批判意識的語言錶現就是對文言、古文的徹底否定;白話與革命、創新、進步等正麵價值觀獲得瞭等價的關係,並成為此後幾十年間的主導話語,這一本為反對“文言—舊文化”的“個性命題”便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排斥“他性”的“大說”和“集體意識”,乃至在破壞舊偶像的同時自身又成為新的偶像,在“加冕”為這場“革命狂歡節”的一元獨白之後逐漸異化為他所代錶的“反傳統”、“反權威”自由精神的對立麵,其中奧妙頗足思量。
在這個意義上講,林語堂提倡“語錄體”也許是對這種一元獨白傾嚮的警惕與反撥。林氏的“語錄體”類似巴赫金所說的一種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方言”,在逐漸成形的一元獨白的社會語境下構成瞭一種否定和批判的力量。當然,一切文化批判均不免受到“市場法則”
的無形操縱而可能淪為批判對象的同謀,批判主體亦或因與眾不同而成為社會文化市場上的珍玩(阿多諾),但這隻是一種可能的結果而非批判者的初衷。林氏之提倡“性靈”、“幽默”及其配套語言措施———“語錄體”,其實也正體現瞭他反對偶像崇拜的懷疑主義精神。但這並不說明魯迅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是錯誤的。魯迅深知孱頭的“中庸之道”無法推動曆史在“正反閤”的陣痛中勝利前進,因此“矯枉必須過正”;這正是魯迅的悲壯選擇。這一點,像遊離於中國文化主體機製之外的林語堂是難以體會得到的。真正偉大的人格、思想與作品,應該在引發各代共鳴的同時,首先成為它那個時代的主鏇律。我們不是不需要多元對話,恰恰相反,多元對話是社會文化保持活力與革命性的前提與動力,但缺乏主鏇律的對話也會“走調”,徒聞喧囂,但實際上卻成為聾人間的自說自話。林語堂選擇“語錄體”
為自己的語言—精神傢園,固然有反撥、矯正的初衷,但在一個反撥時機遠未到來的時刻祭齣這一法寶,宜乎哉受到時人的冷落,而自己的思想也隨之定格,未能達到新的更高層次的統一,他的懷疑主義因此也止於自適自足而缺少建設性,——這對於今天我們仍處於文化轉型陣痛之中的國傢和民族來講,未嘗沒有現實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
最早提“幽默”的人
從風格上講,林語堂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閑適幽默。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使用“幽默”一詞的人。20年代他就積極提倡“幽默”,但應者不多,沒有形成氣候。30年代《論語》創刊以後,他又重新強調“幽默”,並大力創作幽默閑適小品文,這一次則得到瞭較多人的呼應。最初他隻是把“幽默”當作一種語言風格來看待。後來他則把“幽默”理解成“一種心理狀態,進而言之是一川觀點,一種對人生的看法。”他還說“幽默是人類心靈舒展的花朵,它是心靈的放縱或者是放縱的心靈。”可見,林語堂先生已不再把幽默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手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種與特定的文化心理緊密相連的社會行為。林語堂先生正是以這樣的一種幽默觀來看待中國人的幽默的。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寫過這麼一件事。婁時的中國政府曾下令禁止其下屬機關在上海的分部把辦事機構設在外國租界內,而那些在上海辦事的部長們,既不願撤齣租界,也不敢冒犯政府的禁令,於是就把在租界內的辦事機關都換成瞭貿易管理局的牌子。這種花20美金換一塊招牌的作法,既在錶麵上撤掉瞭辦事機構,又讓部長的官府留在瞭租界裏,真是皆大歡喜。在林語堂看來這種花20美金換一塊招牌的作法,實在是一種大大的幽默。這樣看來,林語堂的所謂“幽默”,不是粗鄙顯露的笑話,而是幽默中有睿智,灑脫中顯凝重。
林語堂的散文往往以一種超脫與悠閑的心境來旁觀世情。用平淡的話語去贊揚美文。這樣便形成一種莊諧並用如“私房娓語”式的“閑適筆調”。林語堂散文的語言雜收並蓄,各色兼用,像舊時公文的程式用語,時下流行的政治口號等等,都可以在他散文中看到。這實際上是體現瞭林語堂先生的文學語言觀念。他主張文學語言可以將文言、白話、上來語及方言俗語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所謂“白話的文言”式的特殊語言。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01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林語堂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金庸散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金庸散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周作人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周作人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林語堂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人的智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人的智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生活的藝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生活的藝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談美書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談美書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朝花夕拾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朝花夕拾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梁實鞦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梁實鞦散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流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流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林語堂的幽默 文/張素聞 紳士的講演,應當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這是林語堂的幽默,他當時參加一個學校的畢業典禮,學校安排瞭很多長長的講演,上午十一點半,纔輪到他,他上颱就講瞭這麼一句,幾十年過去,大傢還在笑。林語堂還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
評分我也曾經多次思考,究竟為什麼要讀書?當然,這裏所說的讀書,並不是為瞭應付考試和獲得學分而學的教科書或輔導書,而是在閑暇時候自主地去讀的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所看的文學、美學、哲學之類的閑書,纔是真正意義上的讀書。讀書不是為瞭故作高雅,不是為瞭炫耀淵博...
評分林語堂的幽默 文/張素聞 紳士的講演,應當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這是林語堂的幽默,他當時參加一個學校的畢業典禮,學校安排瞭很多長長的講演,上午十一點半,纔輪到他,他上颱就講瞭這麼一句,幾十年過去,大傢還在笑。林語堂還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
評分我也曾經多次思考,究竟為什麼要讀書?當然,這裏所說的讀書,並不是為瞭應付考試和獲得學分而學的教科書或輔導書,而是在閑暇時候自主地去讀的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所看的文學、美學、哲學之類的閑書,纔是真正意義上的讀書。讀書不是為瞭故作高雅,不是為瞭炫耀淵博...
圖書標籤: 林語堂 散文 文學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中國文學 隨筆 現當代文學 中國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多好的書 居然有人不喜歡他
評分其實有些觀點不太認同 尤其是關於讀書的 但是懶得寫書評瞭。。。
評分看瞭幾月終於看完,散文看起來就是慢
評分裏麵有幾篇真是笑裂瞭好麼!!
評分看瞭幾月終於看完,散文看起來就是慢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林語堂經典作品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沉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沉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財主底兒女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財主底兒女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轉摺的時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轉摺的時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現代中國小說十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中國小說十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魯迅作品十五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魯迅作品十五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新文學大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新文學大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竹林的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林的故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青春之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青春之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為瞭忘卻的集體記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為瞭忘卻的集體記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青春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青春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雌性的草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雌性的草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洞房·少女小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洞房·少女小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