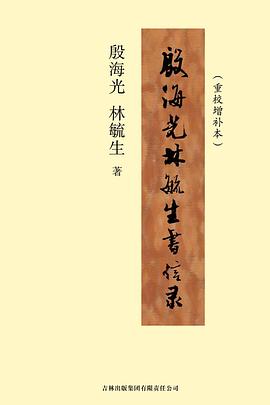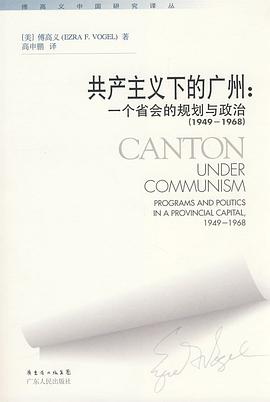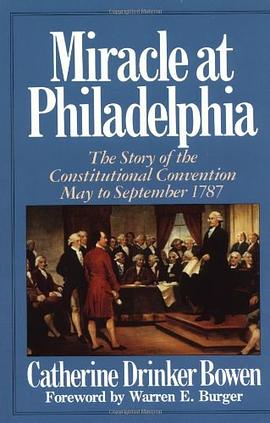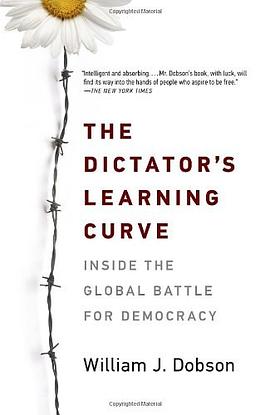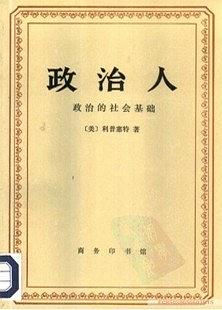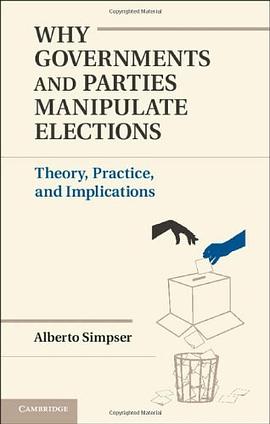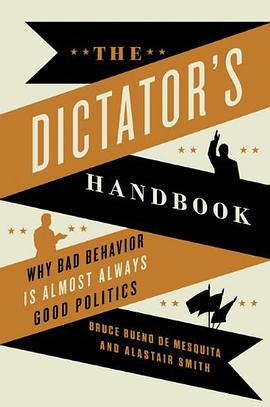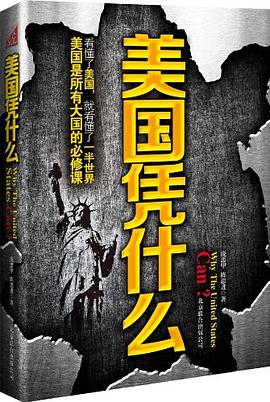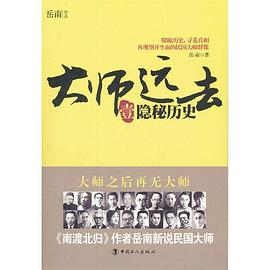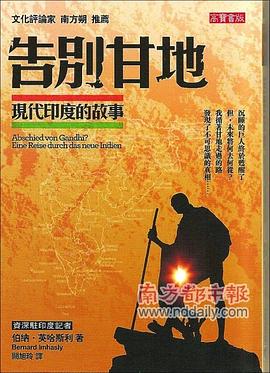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著者简介
雷震家書 电子书 图书目录
下载链接1
下载链接2
下载链接3
发表于2025-02-09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喜欢 雷震家書 电子书 的读者还喜欢
-
 宋教仁传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宋教仁传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中国文化的展望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中国文化的展望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改良与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改良与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傅斯年遺札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傅斯年遺札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流产的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流产的革命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假想的"满大人"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假想的"满大人"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王明年谱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王明年谱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雷震家書 电子书 读后感
图书标签: 雷震 知识分子 思想 台湾 民主 政治 书信 胡适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图书描述
雷震,戰後臺灣政治/媒介史上最奇詭、最壯闊的一則傳奇。曾是蔣介石倚重的紅頂智囊,但在威權年代,堅持民主憲政,成為對抗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報人與政治家。他創辦《自由中國》,鼓吹自由民主,並曾籌組「中國民主黨」,挑戰當時當權者所主導政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最後被捕入獄,當時蔣介石總統甚至親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於十年。儘管人生際遇和政治生涯多舛多折,但雷震當年的主張,如今多已獲得時間驗證,一一實現。1960 年雷震遭國民黨逮捕入獄後,曾寫下四百萬字《回憶錄》,卻為軍監沒收;1988 年,政壇興起平反風,雷家成立雷案平反後援會,不久卻驚聞雷震在獄中寫就遭沒收的百萬字回憶錄,被軍方焚燬,所留下的雷震手稿,幾乎付諸闕如,所幸雷震在出獄後曾追溯部分回憶錄內容,才不致使後人無從追憶他極富歷史價值的一生。
十年牢獄,讓雷震錯過了心愛子女的成長,也無法在他們身邊指點人生道路、敦促他們努力向上,只能透過一紙紙家書,傳遞他對妻兒的關切與情感。《雷震家書》包含雷震獄中家書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現雷震不為人知的生活面,及其作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觀。
《作者簡介》
雷震
1897 生於浙江長興。
1916 赴日求學,在東京經張繼、戴傳賢介紹,加入國民黨。
1926 自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入研究院研究《憲法》。
1927 返國任母校浙江省立三中校長,未久即去職,進入國民政府法制局任編審,並與時任局長之王世杰結為知己。
1933任教育部總務司長,當時之教育部長為王世杰,雷震即在此時與胡適等學界人士締交。
1939國民參政會設川康建設期成會,由蔣介石委員長兼會長,雷震兼主任秘書。八月,任國民黨監察委員。
1947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並獲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獲國民政府授予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用户评价
2年前讀過,補記
评分2年前讀過,補記
评分2年前讀過,補記
评分2年前讀過,補記
评分2年前讀過,補記
雷震家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分享链接
相关图书
-
 经济民主导言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经济民主导言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Miracle At Philadelphia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Miracle At Philadelphia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论投票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论投票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巩固第三波民主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巩固第三波民主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政治的回归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政治的回归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政治人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政治人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Why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Manipulate Election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Why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Manipulate Election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民主和资本主义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民主和资本主义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The Dictator's Handbook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The Dictator's Handbook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聯邦論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聯邦論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美国凭什么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美国凭什么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大改革家雍正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大改革家雍正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Democracy's Fourth Wav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Democracy's Fourth Wav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大师远去·壹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大师远去·壹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辛亥人物碑传集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辛亥人物碑传集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告别甘地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告别甘地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