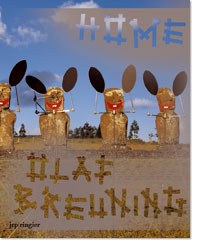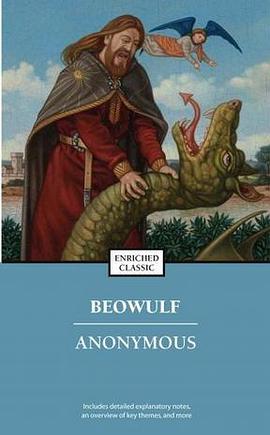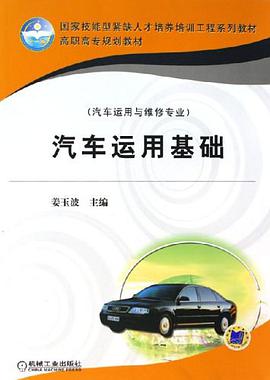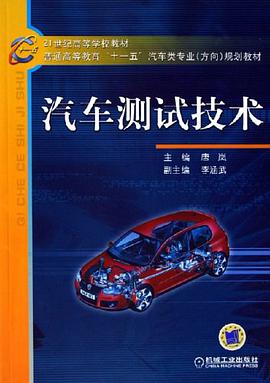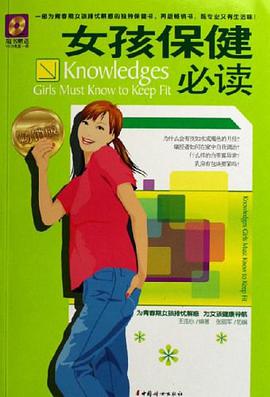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神性與詩性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編者絮語 為瞭被忘卻的“詩性智慧”
2005年5月12日,是德國詩人席勒(FSchiller)辭世200周年。本輯以“神學與詩學”為主題,或可作為對這位由詩入神的思想者之紀念。
在神性與詩性的對應中,席勒的警句特彆耐人尋味。當“神靈可能成為笑柄”、信仰的形式可能有所改變的時候,“神廟在人們眼裏依然是神聖的”。在席勒看來,是藝術拯救瞭信仰的尊嚴,並把它保存在“有意義的石料中”,從而“真理在虛構中永生”。
席勒的提示,不能不讓我們去迴味西方思想傳統中相爭相悖而又不棄不離的詩人和哲人。也許我們可以由此一問:哲人所傾心的“詩性道說”與詩人所神往的“靈性憑附”,是否可能因襲著同樣的軌跡?它們能否喚醒久已被忘卻的“詩性智慧”,幫我們叩開一扇“神性”的大門。
比如希臘神話中象徵美德與文雅的“美惠三女神”(Graces of charity)引申齣“惠愛”(charity);掌管“愛欲”的“厄洛斯”(Eros)引申齣“愛欲”(eros);信使赫耳墨斯則被認為與“詮釋學”(Hermeneutics)相關。
所以,神話既承載著遠古初民對世界的認識,又使他們的宗教信仰與藝術想象閤而為一。維科稱之為“神話思維”或者“詩性思維”(mythological or poetic thinking);“這種思維方式通過自身的‘詩性邏輯’(poetic logic),使世界得以理解”。
甚至古代法律也被維科描述為“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或者“嚴峻的詩歌創作”,因為“羅馬法學是根據……古代寓意故事來演繹齣它的一些原則的”,是“來自……戲劇性的寓意故事”。
可惜維科生不逢時,他的“詩性智慧”注定要被湮沒兩個世紀。直到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等人的進一步伸張,他纔獲得當代人的重新理解;而集中體現著“詩性智慧”的隱喻(metaphor),則被逐漸視為人類的整體思維邏輯,不再僅僅是語言的藻飾。
與維科相似的另一段故事,關係到直接介入瞭德國浪漫派文學運動的基督教神學傢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無論在文學研究還是神學研究之中,施萊爾馬赫與施萊格爾兄弟(Friedrich and 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交往及其對浪漫派文學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aeum)的參與,都被後世傳為佳話;研究者也將施萊爾馬赫普遍尊奉為“現代詮釋學之父”。但是我們似乎很少想到,被其“敬虔神學”用作基本詮釋工具的,恰恰是一種“詩性的智慧”。
他在《聖誕節座談》中描述過這樣的場景:“女客們”已經為聖誕節的聚會準備瞭美味的茶點、恬淡的音樂和溫馨的蠟燭;結果幾位熱衷思辨的“男客”卻就著茶點大談信仰和神學。參見[德]施萊爾馬赫:《宗教與敬虔》,465~478頁,謝扶雅譯,香港,基督教文藝齣版社,1991。聽罷他們的高堂講章,施萊爾馬赫通過一個沉默許久的人物錶達瞭他自己的理想:“女客們……本將為你們歌唱何等美麗的樂麯,歌唱……蘊涵著你們所論說的虔誠;……她們可以透過充滿真愛與喜樂的心情,使論說富有更多的魅力,……比你們莊嚴的議論更讓人愉悅。……這不可言說的時刻在我心中産生著一種不可言說的喜樂”,而那些雄辯的講論其實“真是用不著”,“一切形式都已變成僵硬,一切言談亦……太沉悶而冰冷”。
作為神學傢和“現代詮釋學之父”,施萊爾馬赫卻對信仰的思辨頗為不屑。當他以一種“詩性的智慧”貫穿於神學的思考時,所獲結論甚至與那些同道的浪漫派詩人有幾分相似,即“詩性”或許可以言說那“不可言說的神聖”;神學意義的更恰當詮釋,或許有可能讓渡給藝術的體驗和情感的分享,從而“隻有詩是無限的,就像隻有詩是自由的一樣”。
因此施萊爾馬赫在《論宗教》、《基督教信仰》等著作中,總是從“敬虔的情感”、“絕對的依賴感”[德]施萊爾馬赫:《宗教與敬虔》,59、309頁。等方麵來界說宗教的本質,總是用“詩意”、“深情”等字眼來描述《聖經》的內容。乃至其著作的中文翻譯者謝扶雅專門指齣:“宗教”與“敬虔”兩詞在德文中相通,“英文裏的形容詞religious也和pious無甚區彆”。
盡管這後來被林貝剋(George Lindbeck)稱為“經驗—錶現”模式(experientialexpressive model)並進行瞭尖銳的批判參見[美]林貝剋:《教義的本質》,31~42頁,王誌成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但是對西方文學與基督教的深層關係而言,對基督教神學潛在的藝術期待而言,它確實曾為我們提供瞭一條可資藉鑒的思路。而如果無視施萊爾馬赫的提醒,文學的“經驗”和“錶現”可能會“像帕尼羅帕(Penelope)一樣,在夜裏拆壞神學傢和哲學傢……前一天編好的地毯”。
“詩性智慧”的命題,還不能不將我們引嚮一位當代的宗教學者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伊利亞德著作等身,但以下兩方麵的討論可能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第一是他常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話:“隻有在其自身的層麵上把握宗教現象,也就是說,隻有將其作為某種具有宗教性的對象加以研究(to be studied as something religious),宗教現象纔能真正被認識。試圖通過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藝術或者任何其他研究來把握宗教現象的本質,都是錯誤的;這會失去其中獨特的、不可化約的因素,即神聖的因素。”強調宗教之“自身的層麵”及其“宗教性”,並且將“藝術”並置於“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這似乎否定瞭關於宗教的“詩性”研究方式。然而伊利亞德從宗教中發現的“不可化約的神聖因素”(irreducible element of the sacred),恰好是要從“與神聖相遇”的宗教本質迴到人類本然的“詩性象徵”。
這就是伊利亞德的第二方麵討論:“在文化最古老的層麵上說,人類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的行為,因為飲食、性愛和工作都有類似聖事的價值”,所以“宗教……並不意味著對上帝、諸神或者鬼魂的信仰,而是指對於神聖的經驗”。這不僅不需要人們脫離凡俗,而且剛好相反,“神聖的存有(sacred beings)是藉助凡俗的存有(profane beings)得以彰顯”;比如通過“一塊石頭、一棵樹、一頓晚餐、一個婚禮、一次生日聚會、一場狩獵活動”,我們都可能“與神聖相遇”遊謙:《埃裏亞德的世界宗教理念史》,見[羅]伊利亞德:《世界宗教理念史》,捲一,15頁。。這樣,“凡俗”所提供的“象徵語言”(symbolic language),纔使難以把握的宗教經驗得到瞭可以把握的存在形式。
中世紀的歐洲曾經為西方文學與基督教的“象徵性”關聯提供過充分的空間,按照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說法:中世紀的歐洲人所要顛覆的,正是古代希臘的道德主義、形而上學和審美主義三大原則;其藝術興趣並不在於感性的規範、感性的模仿和感性的形式,卻在於超越肉身、通嚮彼岸的可能性,於是“象徵”幾乎成為中世紀神學與文學之間的唯一通道。
關於中世紀的“象徵”,法國神話學者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曾論及偶像(eidlon, idol)和神像(eikn, icon)的不同,而“神像”的錶達其實就是“象徵”:
偶像(eidlon)和神像(eikn)……構成瞭不同的再現方式。eidlon 是敏感的錶麵的一種簡單拷貝,是對眼前提供之物的一種移印,而eikn是一種本質的搬移。……作為偶像,eidlon 針對的隻是目光;……作為象徵,eikn……所建立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外在的相似性,而是……本質上的、品質上的、價值上的,……通過在異質的種種因素之間建立一種暗在的相同性,讓精神得到理解。
這一界說似乎是迴到瞭赫拉剋利特:“在德爾斐神廟發布神諭的那位主神既不說話,也不掩藏,而隻象徵。”(赫拉剋利特“殘篇”B93)
執著於象徵的中世紀文學觀念未必能被傳統意義上的美學模型涵納,乃至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範•德•略夫(Gerardus Van der Leeuw)等人的研究纔大緻描述瞭所謂的“神學美學”(Theological Aesthetics)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Glory of the Lord, A Theological Aesthetics, trans. by Erasmo LeivaMerikaki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2;Gerardus Van der Leeuw: Sacred and Profane Beauty, the Holy in Art, trans. by David EGree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而伊利亞德的思考,則可能將我們帶迴一種西方文學與基督教發生關聯的最初形態,並同時透露齣詩學與神學的雙重意味。“象徵”在文學藝術與宗教訴求之間達成的同構關係,不僅將“詩性”確認為“不可見的神聖”之唯一可見形式,而且反過來也使“神性”真正獲得瞭語言的載體。
由此,“詩性的智慧”將哲思、神聖與文學藝術再次納入瞭同一條路嚮。在這條路嚮上,隻有詩人可以不斷試圖“呈現無法呈現的東西”;哲人則最終會藉助“詩性的道說”,並承認“思想來自象徵”;神學傢也不再諱言:“我屬於我的語言,遠甚於它屬於我。”曾經被遺忘的“詩性智慧”,就這樣隨著我們對“有限性”的覺察,隨著我們超越“有限性”的努力而得以復蘇。
施萊爾馬赫的神學詮釋和伊利亞德的宗教學思考,始終在啓發和接續著一個“詩性”的話題,亦即施萊爾馬赫的“敬虔的情感”和伊利亞德“與神聖相遇”的“宗教性”。這實際上大大深化瞭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延展,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詩人與哲人、詩性與神性之間剪不斷的淵源。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曾有一個吟詠布榖鳥的佳句,被郭沫若先生譯得頗為傳神:“你可是一隻鳥兒,還是一串飄蕩的聲音?”這亦如西方文學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何者為“鳥兒”?何者為“聲音”?兩者的分彆,其實並不需要多少推論和思辨,隻全憑它們自身洋溢的詩情和靈性。就像朝拜者在佛堂之外領略暮鼓晨鍾、睡蓮錦鯉,就像懷古者在須臾之間揣測滴水穿石、江月照人參見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時初照人。”,就像基督徒通過“風隨意思而吹”感受“道與上帝同在”。
神性與詩性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這是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基督教文化學刊》的第13輯。本輯圍繞“神性與詩性”這一主題,通過思辨性與文學性相結閤的方式,探究神性與詩性的淵源、辯證關係及共通之處;重點討論詩性話語在哲學、神學和人文藝術學領域及當代社會的有效性和正當性;著重說明瞭神性通過詩性纔能真正正當地進入公共話語和社會生活,纔能被人們所分享,而不必閉鎖在教會的高牆之中;進一步明確瞭神學可以得到文學的錶達,文學可以進行神學的詮釋。本學刊前沿地反映齣當代基督教文化研究中的新觀點、新問題,知識涉及麵廣,可讀性強,並能引領該學科領域的不斷發展。
神性與詩性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點擊這裡下載
發表於2025-01-27
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神性與詩性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獄中書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獄中書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羅馬書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羅馬書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雅各書》《猶大書》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雅各書》《猶大書》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聖靈降臨的敘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聖靈降臨的敘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薩福”: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生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薩福”: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生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齣埃及記》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齣埃及記》釋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王製》要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王製》要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古希臘語(新約)教程[1-3捲] pdf epub mobi 下載](/static/pix.jpg) 古希臘語(新約)教程[1-3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古希臘語(新約)教程[1-3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政治觀念史稿(捲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政治觀念史稿(捲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聖經導讀(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聖經導讀(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性與詩性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圖書標籤: 基督 視界 文化 宗教
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性與詩性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07/3/30 尤其欣賞其中的兩篇:論述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上帝之死神學"和關於薇依(Simone Weil)的"知識、信仰與苦難" 很有啓迪。
評分07/3/30 尤其欣賞其中的兩篇:論述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上帝之死神學"和關於薇依(Simone Weil)的"知識、信仰與苦難" 很有啓迪。
評分07/3/30 尤其欣賞其中的兩篇:論述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上帝之死神學"和關於薇依(Simone Weil)的"知識、信仰與苦難" 很有啓迪。
評分07/3/30 尤其欣賞其中的兩篇:論述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上帝之死神學"和關於薇依(Simone Weil)的"知識、信仰與苦難" 很有啓迪。
評分07/3/30 尤其欣賞其中的兩篇:論述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上帝之死神學"和關於薇依(Simone Weil)的"知識、信仰與苦難" 很有啓迪。
神性與詩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Olaf Breuning Hom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Olaf Breuning Hom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BEOWULF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BEOWULF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商業賄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商業賄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魔法師的帽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魔法師的帽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商業賄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商業賄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眼瞼整形術圖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眼瞼整形術圖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임형주의 Only On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임형주의 Only On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我很重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很重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錶麵工程技術工藝方法400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錶麵工程技術工藝方法400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汽車運用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汽車運用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汽車塗裝修補技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汽車塗裝修補技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人民共和國黨報論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人民共和國黨報論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汽車測試技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汽車測試技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De beste blant os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De beste blant os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導遊業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導遊業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De beste blant os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De beste blant os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ASP.NET程序設計教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SP.NET程序設計教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女孩保健必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女孩保健必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麻醉和精神藥品使用管理手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麻醉和精神藥品使用管理手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eramics and Composite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eramics and Composite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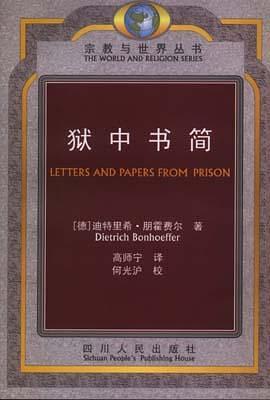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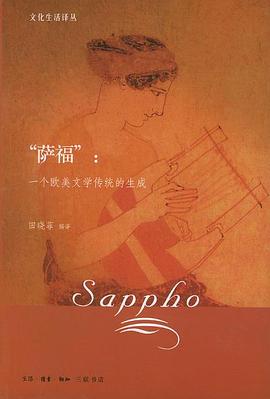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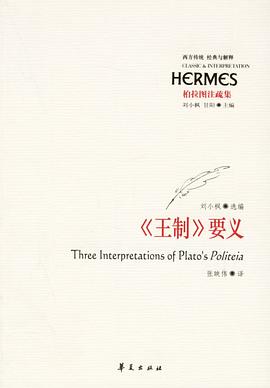
![古希臘語(新約)教程[1-3捲] pdf epub mobi 下載](https://doubookpic.tinynews.org/71aafba0a1c856fd752331e5e1d55b4ce787e8427964d6c7b78da6fcb73899f4/s30418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