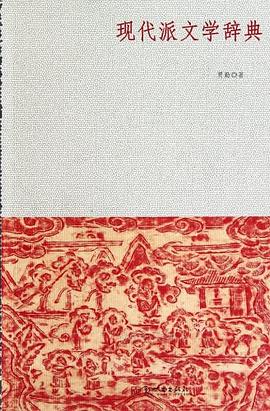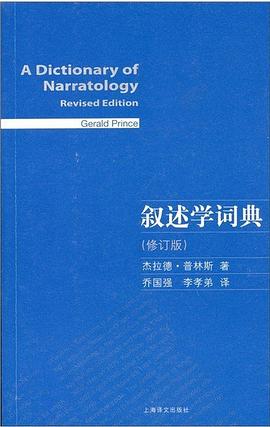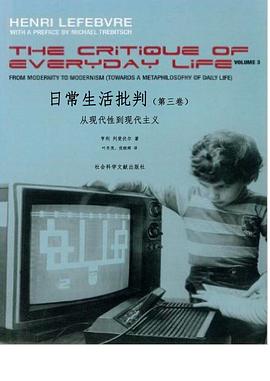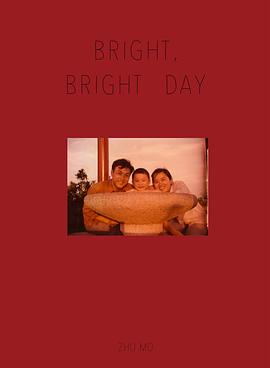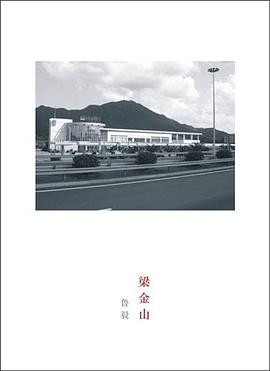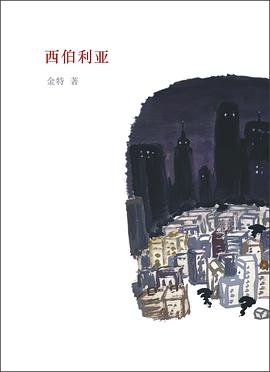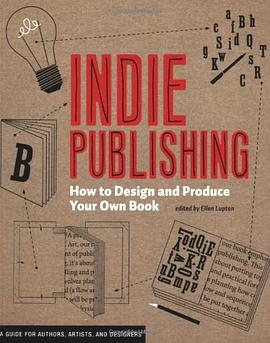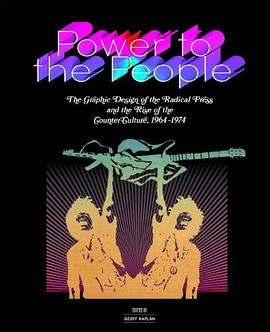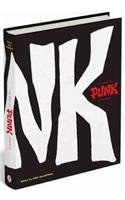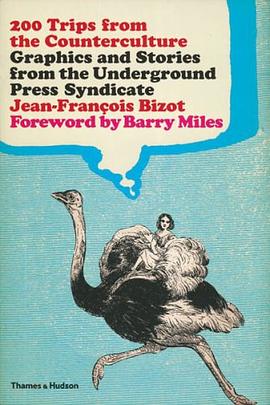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著者简介
须弥,生于雷州半岛。同济大学哲学硕士,曾供职于《艺术世界》杂志社,现为《飞地》编辑总监。著有诗集《环形病史》、《鸟坐禅与乌居摆》,诗文本“身体三部曲”(《身体地图》《物居诗》《乌钟摆》)等。
环形病史 电子书 图书目录
下载链接1
下载链接2
下载链接3
发表于2025-04-10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喜欢 环形病史 电子书 的读者还喜欢
-
 现代派文学辞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现代派文学辞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shining4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shining4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从存有到生活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从存有到生活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梦想的诗学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梦想的诗学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叙述学词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叙述学词典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马拉美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马拉美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日常生活批判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日常生活批判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东方,西方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东方,西方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历史之名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历史之名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隐匿的神学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隐匿的神学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环形病史 电子书 读后感
图书标签: 须弥 诗歌 独立出版 当代文学 师友著作 中国文学 不是出版基金 X须弥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图书描述
与长诗《环形病史》的开阔与异质性不同,短诗中的深圳红孩抒情、柔软而纯粹,却完全不像是个“红色的孩子”——根据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说法,(红色)血液占优势的多血质性格之人,大多表现为热情外向,而我们的这位诗人在他的短诗里则更像是黑胆汁占优势的抑郁质性格:敏感、内倾、观察细致。
他经常提到猫,这种动物如幽灵般闪现于众多诗篇里。不管是他那组《四拍曲》里被命名为“绝句”系列的几首,还是那组庞大的《此刻》,猫都是居住在里头的常客。不管是“人与人相互编织。我说自焚,你说别墅。我说猫,你说术。一则独幕剧”(《绝句•夏》),还是“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噼噼啪啪的/猫趴在过道上/我牙疼/张不开嘴/有歌声/从过道那边/传来,像古代/某种暗器”(《此刻83》)这只魅影般的猫似乎无处不在,它在作者的生活和对生活的叙述中,时不时闪现出来:
像以前一样/还是在/老院子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你/
阳光中/有雨洒下/猫就在不远处/假装入寐/
它跟我一样/对这种鬼天气/早已习以为常/
只是在同样的场景下/五年前拍的照片中/你和它都只露了半个身子
——《此刻136》
一个被还原的场景(老院子、坏天气和拍照事件)再度由作者置入到现场中,曾经的和现在被描述的情境重叠在一起而造就出一种恍惚感,但不重叠的部分却提示出诗要叙述的重心所在:那只猫,参与到对情境的建构中,和那个“她”一样参与了对镜像和事件的建构,而不同之处恰在于猫和“她”的一致之处,“只露了半个身子”,可以理解为猫和人共同分担了一个完整的客体形象吗?或者说,如今的拍摄和记忆中的场景发生的窜位,恰恰泄露了“此刻”的秘密?普通场景无以自名和自明,猫却在这里起到了提示的作用——叙述遗漏的部分,却正是诗之为诗的所在?
深圳红孩类似的“猫之诗”为数不少,譬如“猫的孤单/学不来。为了接近/我趴在床上/弯成猫形”(《此刻321》)中的对孤独体认的叙述,以及“猫一只只地死了/在房间里/我一只只地/捡起来/挂到墙上/我都快哭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猫尸/还是冰凉的”中的另类体验,本质上还是在处理一种孤独和不安的情绪,这里面的焦虑和无助感借助猫这种动物的特质而变得立体起来,相比于情绪的时降时落来说,一只猫平坦的腹部或许会是这架不稳定运行的直升机最好的停机坪。
另外两首诗,我们拿来对读或许也会很有意思。《此刻84》中,安静而神秘的那只房东的黑猫和“我”对观,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被称为是“迷人的”;同样是写小动物,《仿写术——致科塔萨尔》中却出现了一只更加奇特的兔子,这只兔子应该是科塔萨尔《动物寓言集》里头《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那只被吐出的兔子的近亲,只不过深圳红孩馈赠对象的居住地,由科塔萨尔的“小姐”的正牌巴黎,挪到了“东方巴黎”(多么具有怀旧气息的一个称呼)上海。更有趣的是,诗人犯起诗的自恋,迷人的自己有只“迷人的猫”,而那个吐出兔子的人,却常被大家称为“迷人的特塔萨尔”。
最后回头来说一说前面所提到过的长诗《环形病史》。这是一个混杂着各种经验和判断的文本,它的丰富性和阅读挑战,似乎远远超过作者的那些短诗。在这首诗里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多声部的合奏,它既是精神层面的个人史叙事,又是某种宏大叙事的缝隙中泄露出的病痛和呻吟。不管是诗一开头的“那遗传的/身体和病土地/它们与时间一起/烙刻在族谱上”,以及以类似于注释形式出现的、实则同样是诗主体部分的“我一出生就病了……至今未愈”,还有第八部分的《这一家人的爱和怕》,都显示着某种效果上颇为突兀的色彩,这色彩笼罩在诗的背景上空,像涂抹在病历上的处方墨水,诊断着这个时代历史意识和记忆的可怕缺失,以及焦虑的深渊下,那恐惧与爱、希望与绝望。
寻梦不遇之夜/有些浑浊/像女人/的屁股。/ 他说/他的手/不知该/放在何处/“阴茎已丢失……”
——《环形病史之二:往事书3》
我们见过坦克/在镜头里移动,还有枪声/ 穿绿衣服的人/人群中,人头在旋转
——《环形病史之二:往事书5》
黑暗中妈妈的声音/毛绒绒的,像吹在鼻子上的热气/妹妹随手摘下一片/芒果树叶,悄悄对我说:/“我爱妈妈……/但我怕爸爸”/哦,钢条爸爸,我也怕/士兵爷爷却是面条/可以将自己反复打开/哥哥像爷爷,虽然爱打架/但却喜欢小动物,比如蚂蚁/我们是蚂蚁兄弟/我爱奶奶,但她走了/我怕带走她的东西/我怕蛇,也怕山鬼/鬼怕爷爷,还有社会主义/妈妈像我们,怕爸爸/但也爱爸爸/哦,暴力爸爸/但我们更怕穷/就像怕弯曲的小东西/表叔说他只怕坦克/和敲门声。爷爷不说话,爱做梦/爷爷是八路军,什么都不怕
——《环形病史之八:这一家人的爱和怕》
最初的“阉割恐惧”起源于人的童年生活中对父权的认知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双重作用,“阴茎已丢失”不仅意味着(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阉割恐惧,还在意志方面带来焦虑和某种后遗症:坦克、枪声和此前对日常生活物事及情态的描述,似乎都在表达一种互文关系,也即欲望、暴力、权势和生活本身的无力感在“阉割”人,使人陷入恐慌和无力感当中。这种“存在性不安”经由历史叙事和日常还原而具体了起来。
这种互文关系一直贯穿整首长诗,包括《这一家人的怕和爱》部分。这部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谱,对家国叙事的审视是大的语境,结合长诗第一部分的“当我说起‘家族’这个名词时,它却总是以‘国族’的形象出现”(《一、出生记1.3》),这种审视尤其图穷匕见。家族/民族(妈妈)、政权/国家(爸爸)、军队/暴力机构(爷爷)、单纯的主流热血青年(哥哥)、伦理象征(奶奶)、勇敢的叛逆者(表叔,作者试图在暗示他是二十余年前的广场学生)——当然,这样的明显对应处理未必精确而准确——,他们互相纠葛缠绕。这里头作者的意图因为这种缠绕关系而变得更加隐微和复杂,不再是二元论的评判,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了一个多层次文本应该具备的特性。
整首诗似乎就落在“怕和爱”这样一个主题上。后期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如何自如地处理愿望和厌恶的问题”,诗歌在这里僭行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再思考,而作为历史与现实中单体的个人,对往事的记忆以及这种记忆中所呈现出的可贵的历史意识,似是颤栗的恐惧中仅存的能力了。
于某种程度而言,《环形病史》像是病灶上切下的病体样本,作为一种时代体认和个人经验历史的畸变剖面,虽然掺杂进诸多非公共性的体验式叙述,但在整体把握上却依然有很强的宏观色彩。但这种宏观性并不妨碍它和深圳红孩的系列短诗《此刻》的呼应和在气质上的一致性。《此刻》是对“此刻”这个瞬间的集中把握,而《环形病史》则试图将这个瞬间拉长为一种由历时性而共时性的、被存储了的记忆。曼德尔施塔姆说,“飞逝的瞬间可以经受数世纪的压力,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永远维持同一个‘此时此刻’。你只需懂得如何从时间的土壤提取这‘此时此刻’而不要伤害其根茎就行了,否则它会枯萎而死”,深圳红孩提取了他的“此时此刻”,并已经和正在不断用创造的热情来避免它的萎谢。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用户评价
不是每首都好,但好的那几首好到尖叫
评分不是每首都好,但好的那几首好到尖叫
评分不是每首都好,但好的那几首好到尖叫
评分不是每首都好,但好的那几首好到尖叫
评分不是每首都好,但好的那几首好到尖叫
环形病史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分享链接
相关图书
-
 空日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空日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左撇子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左撇子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How to Make Book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How to Make Book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the sea vol. 1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the sea vol. 1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131.131131311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131.131131311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Zine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Zines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大峡谷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大峡谷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梁金山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梁金山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西伯利亚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西伯利亚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十万个为什么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十万个为什么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夏宇简体字诗集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夏宇简体字诗集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Indie Publishing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Indie Publishing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Power to the Peopl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Power to the Peopl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The Best of Punk Magazin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The Best of Punk Magazin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Destroy All Monsters Magazine 1976-1979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Destroy All Monsters Magazine 1976-1979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Publish Your Photography Book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Publish Your Photography Book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π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π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200 Trips from the Counter-Cultur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200 Trips from the Counter-Culture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朝圣者之旅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朝圣者之旅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
 悲伤无法逆转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悲伤无法逆转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