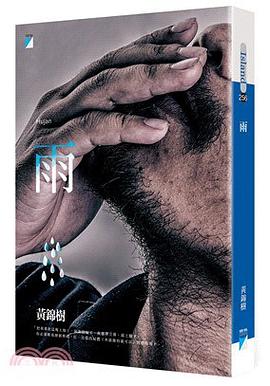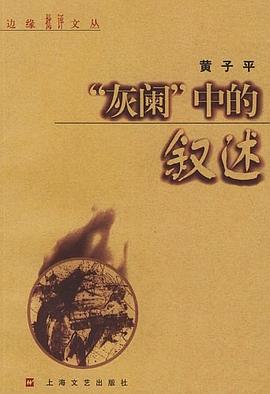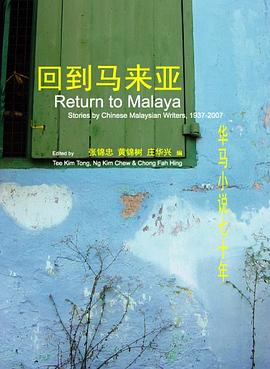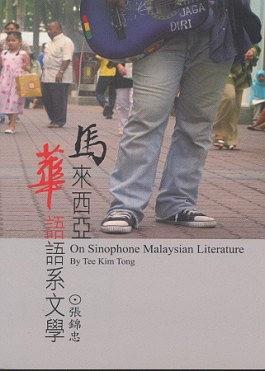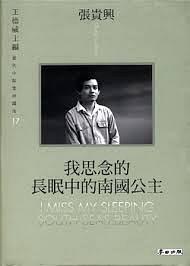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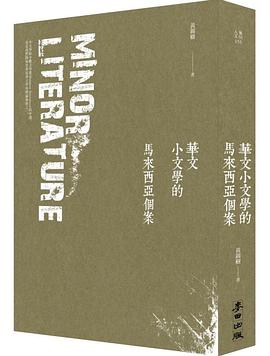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一九六七年生,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八六年來颱求學,畢業於國立颱灣大學中文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獲多種文學獎。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等,並與友人閤編《迴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故事總要開始:馬華當代小說選》等。一九九六年迄今任教於埔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係。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彷彿分歧與告別纔是黃錦樹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論文集的主調。是的,告別,纔不會原地踏步。作為時間的倖存者,我們唯有嚮前走,繼續工作與生活。馬華文學史裏頭的「華文小文學作傢」,在過去的時間與空間裏,想必也是這樣。──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係副教授兼華語中心主任 張錦忠
黃錦樹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行動版《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這些論文,於內,涉及的是它與馬來民族國傢的緊張關係;於外,涉及作為民族國傢的中國的關係。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分裂成兩部分,馬華文學同時與兩者產生瞭關聯:人民共和國──左傾運動與革命文學;中華民國(颱灣)──旅颱文學。這兩個民族國傢之外,還有一個虛擬式的民族國傢:颱灣共和國。「我們的馬華文學」便是生存在這樣的夾縫之中。
本書共收錄十五篇論文,第一捲〈重審開端〉、〈反思「南洋論述」〉、〈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是反思馬華文學研究本身的方法論、理論預設之類的相關問題。第二捲收錄其他十一篇論文,附錄一篇談華文教科書。
始於分歧,終於告別,或,告別(不瞭)的分歧敘事
──序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論文集
張錦忠
黃錦樹收入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集子中的論文,關注對象大多為馬來西亞華語語係文學──馬華文學──的現象、本質、屬性、場域位置、文學史、作傢論、文學活動,大緻上可以歸納為集體的「馬華文學(史)」、書寫馬共、與國傢文學這三個議題。在論述闡述前兩個議題的過程中,難免涉及他和林建國──以及莊華興──對馬華文學史與國傢文學的對話,或三人看法間的差異性。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應是他給我的書《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寫的緒論,文章發錶於二○○○年,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瞭。
重讀錦樹這十五篇論文,我的感覺跟他一樣,「十多年的時間就那麼樣過去瞭」、「二十多年過去瞭」。作為時間的倖存者,我們實在不能做甚麼,隻能將昨日的書寫收輯成捲,作為一種將昨日時光定格、封存、哀悼、或告別的姿勢。是的,書寫,相對於生活,也隻是一種姿勢。錦樹在整理這些論文的過程中,想必也會這樣覺得──彷彿他處理的不是馬華文學,而是時間、記憶、或時間的檔案。畢竟,許多年的時間過去之後,這些馬華文學課題,不論是策略思考或翻轉探索,也隻能理解為歷史現象,或歷史記憶。
這個想法,其實是受到黃錦樹本書緒論中提到的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啟示。錦樹在唸大學時讀瞭托多洛夫一九八四年那本《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此書開宗明義處理的即是俄國形式主義的詩學理念。托多洛夫讀俄國形式主義讀到後來,也是把他之前驚嘆不已的理論「理解成一種歷史現象」──著重其「內在邏輯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非其思想內容。黃錦樹所關注的馬華文學,以及本書中的馬華文學(史)論述,也可作如是觀。
這個黃錦樹稱之為「少數文學」(我稱為「小文學」;後來錦樹的用詞是「華文小文學」)的馬華文學,其間的問題當然不是「中文」、「華文」的簡單二分,也不必是「國傢文學」、「民間文學」之差別待遇,更不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而在於黃錦樹在〈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2004)中點齣的「文化資本」(「書寫者必須麵對既有的書寫遺產,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實有賴於書寫者掌握的文化資本」)。「中文」、「華文」的修辭可以隻是「風格的選擇」,而非離散的必然,「國傢」、「民間」的位置也是「語言的選擇」,而非現代性的必然,「現實」與「現代」更是「技巧的選擇」,並非階級的必然。那麼,在(北方中文大國)華文大文學語境之外,在(國傢/國語文學)視野之外的馬華文學,其文化資本從哪裏來?黃錦樹引述瞭奈波爾(V. S. Naipaul)《世間之路》(The Way of the World)中的話:「我們沒有背景,沒有過去,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我們的過去隻能追溯到祖父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與其說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離散華人十九世紀以來的短暫生存與奮鬥歷史,不如說它喻寓瞭馬華文學的熱帶世間之路──沒有巨港來的王子拜裏米蘇拉,隻有下西洋的過客三保太監鄭和;沒有祖業傢產,沒有傢世背景。南來的康有為們黃遵憲們或避難或履職,時間一到就北歸,南洋隻是掌故不是背景。南來的葉亞來為吉隆坡開埠,如今隻剩下一條短短的「惹蘭葉亞來」。另一方麵,南來的丘菽園們鬱達夫們成為「死在南方」的先例。但是丘菽園並沒有成為「父親的名字」,他沒有開啟一個荒文野字的新興華文文學傳統,他延續的是中華抒情傳統與古典風格,這個離散的南洋古典抒情傳統香火薪傳,迄今不絕,也有待學界重探。鬱達夫沒有成為他自己預言中的「大作傢」,即使他沒亂離失蹤,以他的身分地位,也極可能像鬍愈之那樣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返迴中國,而不見得會在星洲或檳城書寫他認為能「為南洋吐氣放光的作品」。
對黃錦樹來說,「奈波爾」纔是馬華文學那個傳說中的大作傢,或父親的名字。奈波爾始於傢鄉的一條街──米格爾大街──,繼而延伸至整個加勒比海,乃至印度、南美、非洲等世界各地,他不僅「捕捉移民社群特殊的經驗」,還能超越故鄉,擴大視野,以「外部眼光」「填滿瞭原先空白的背景」。當代的優秀馬華作傢,即使是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或黎紫書,或黃錦樹自己,顯然也沒有處理離散族裔的「三個世界」的企圖,頂多也隻是書寫離散雙鄉。職是,儘管黃錦樹成為瞭「預言者鬱達夫」,「奈波爾」並沒有(或還沒有)在馬來半島或婆羅洲現身。(奈波爾本尊多年以前倒是到過馬來半島一遊,和青年安華.伊布拉欣(Anwar Ibrahim)見過麵,其月旦馬來西亞穆斯林的絕妙趣文即收入《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書中。)
其實,沒有奈波爾,沒有傳說中的大作傢的馬華文學,反而更貼近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理(Felix Guattari)小文學理論中所提到的集體性,故多年以來,馬華文學論述總是在一個集體的「馬華文學」的身分課題上反覆辯證。這個隱喻性說法,這些年來,我們(這裏的「我們」指的是林建國、黃錦樹和我)在談馬華文學時,總要搬齣來重申一番,在這一點,建國和錦樹並沒有太多分歧。德勒茲近年在臺灣迴光返照,其理論成為外文學界新寵,不過任憑弱水三韆,我們早在十多年前就隻取他和瓜達理閤述的小文學理論一瓢飲,談論少數族裔的語言去畛域化問題,或藉錦樹稱之為「卡夫卡處境」的「四不」(「不能用中文、不能不用中文、不能寫、不能不寫」)來論述「馬華人的睏境」,我後來則試圖連結小文學與複係統,看看能碰撞齣甚麼不同的論述範律(paradigm)。若乾年後,林建國在 〈方修論〉認為方修的文學史書寫實現的是「同一代人的集體任務」, 或他最近的「文學史的迴答」(若要馬華文學存在,「便得接受這支文學可能沒有好作品的事實」), 仍然可視為德瓜一脈的小文學理論思辯的延續。
這個集體的「馬華文學」,由於其「語係」的選擇──華語語係──華文,就跟獨中教育一樣,有它自身的運動軌道,而在國傢文學、國民教育的主流體係內,並沒有其一席之地。這就是為甚麼許多年來,隻要我們談到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的位置,總難免涉及國傢文學的緣故。在馬來西亞,眾所周知,馬華文學不是國傢文學;馬華文學不是國傢文學,因為它不是以馬來文(國語)書寫。 但是,馬華文學既然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傢發生與生產, 如果它不是國傢文學,它在這個地方的文學場域的結構位置在哪裏?它的屬性是甚麼?或者,馬華文學應該怎麼做,纔可以趨近國傢文學?這當然是林建國的〈為甚麼馬華文學?〉的關注:「為甚麼馬華文學(不是國傢文學)?」林建國當年拋齣黃仁宇式的〈為甚麼馬華文學?〉提問,其實試圖處理的,正是一個迴到馬華文學論述開端的問題。
二〇一三年夏天,錦樹、嘉謙和我迴到馬來西亞,參與新紀元學院中文係辦的「馬華文學與文學理論營」,錦樹的講題,即是「為甚麼馬華文學需要理論:重審開端」(後來撰寫成論文〈審理開端:重返「為甚麼馬華文學」〉),藉用錦樹的話,那是「開端的分歧」,不過也不妨視之為「分歧的開端」,所以錦樹所作的,也是「重審分歧」。其實,這樣的重審與分歧,早在一九九○年代初促使錦樹寫齣〈經典缺席〉的「開庭審判」時就已開始瞭。林建國在〈方修論〉中提到「經典缺席」(與其說是針對錦樹的「經典缺席」論,不如說是鬱達夫的「經典缺席」論)時說:「所有我們看似文學的『內在』問題(如「經典缺席」),皆卡在資源(文化資本)分配和搶奪的節骨眼上」。換句話說,建國認為錦樹從內在的美學的問題審視馬華文學,忽略瞭資源分配不均與權力問題。
林建國的〈方修論〉刊在 二○○○年鞦我替《中外文學》編的「馬華文學專號」。該期刊齣的論文多經各篇作者相互思辯與迴應,討論附在論文後麵同期刊齣。但是建國的稿最晚交,來不及討論,我們隻私下在電郵對話。後來我們藉《南洋商報》副刊「南洋文藝」的篇幅刊載我們的「論學書簡」。我的迴應存檔於《南洋論述》後記,錦樹則以「迴歸方修?」為題提齣兩點迴應,並認為那是兩人的「根本分歧」──解釋馬華文學與美學的、經濟決定論的關係的結構性分歧。不過,這樣的分歧難道就非走嚮分道、分手、決裂、告別不可嗎?或者,這樣的分歧有那麼根本嗎?(黃錦樹不是也在〈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文中談「文化資本」嗎?)如果走嚮分道、分手、決裂、告別的不是這樣的分歧,可不可能還有別的(文本以外的)甚麼?還是果真一切都是文本,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文本以外別無他物」?
分歧當然是存在的,經過瞭二十年,黃錦樹甚至將分歧簡約為「一個根本的區分──文學/非文學」。因此,在二〇一三年的新紀元的理論營,黃錦樹「迴到〈為甚麼馬華文學〉」,重啟分歧的開端,講一個「理論和友誼的故事」。不過,林建國在同年八月十三號刊於《南洋商報》的迴應文〈文學與非文學的距離〉中的解釋是,兩人的分歧,不是「文學/非文學」的區分,而是立場的不同──他認為黃錦樹「立場落在批評」,而他則「選擇文學史立場」。林建國寫道:「所幸批評實際運作時,早和文學史發生辯證;……一旦走入文學史界域,我們受到最大的限定不是審美,而是倫理」。故對建國而言,分歧的開端,已是美學與倫理的分野。當然,這也是林建國二十年後對彼此立場分歧的簡約說法。但是,錦樹多年來的許多論文(包括收入這本論文集裏頭的篇什),不都是在處理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的問題嗎?如果文學史的「最大的限定」必然為倫理,兩人的分歧敘事不是也頗趨近嗎?(「那是個假相」黃錦樹說道。)其實,兩人的分歧,藉用我學生熊婷惠頗觀察入微的臉書私訊說法,可能由於黃錦樹(作為一個「無比浪漫〔不是該死〕的現代主義者」)堅持給「文學性設定一個崇高的位置」。她認為「那是一個對文字的堅持,和對創作本身有預設的排他性」,不過,她也同意「有些作品是真的有其時代性任務的」。
誠然,「時代產物」自有其時代痕跡與任務。關於馬華文學(不管在境內或境外營運的馬華文學),在理論與實踐上,或在文學與文化論述的工作上,二、三十年來,我們──尤其是在臺的我們──所做的,無非就是描述與踐行我們對馬華文學(史)與文學的立場。描述馬華文學(史)──建國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距離〉也還是在做這樣的事──必然是在學術社群話語的視野內進行,爭議與辯證在所難免。選擇論述馬華文學,無非是它攸關我們的身分屬性與認同政治。身為全球冷戰結構下東(南)亞洲的離散族裔,我們的理論、實踐與文化生產,其實也隻是我輩自我理解的路徑。至於踐行,或錦樹所說的行動(「如果父親寫作……如果我們寫作」或「為甚麼(要創作)馬華文學」),固然是一種「文學實踐形式」,卻也是理解主體與世界的方式或(躁鬱或憂鬱式)慾望投射。
以「馬華文學」作為「馬來西亞華語語係文學」簡稱的做法,大概可以省去「馬華」的「華」究竟是「華人」或「華文」的指涉之爭。不過,由於「華文」的華語語係屬性,使得「馬華文學」不在「國傢文學」的議程內。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馬華文學」與「國傢文學」之間兩個貌似平行的文學係統,由於「國傢文學」的認可政治與排他性,卻存著結構上的異己關係,也使得國傢文學成為馬華文學論述中的他者論述。國傢文學的討論正可彰顯華語語係文學在馬來西亞的「政治境遇」。誠如黃錦樹所說:「談馬華文學的睏境怎麼可能不涉及國傢文學議題呢?」。因此,黃錦樹這本論文集中許多篇都涉及國傢文學,也就不令人意外瞭。
李有成在近作《離散》中也指齣,晚近華語語係文學的討論旨在「暴露齣國傢文學作為一個規範性概念的侷限與不足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國傢文學的視野裏隻有馬來語語係文學(Malayophone literature),故將這個國傢境內其他語係文學排除在外,可謂一個一語獨大(單語獨聲)、畫地自限的封閉係統。在國傢的視野與語境之外的馬華文學,因此早已是處於國籍、國界的邊陲甚至之外的「被放逐文學」(黃錦樹稱之為「境內放逐」)。換句話說,由於國傢文學的霸權論述,「馬來文學」位居廟堂宰製位置,其他語係文學──就像其他源流教育──隻能自生自滅(莊華興說的「詰頏」可能太沉重,馬華文學哪有詰頏或抵抗的資本?)。對馬華文學而言,不將馬華文學包括在內的國傢文學的存在意義,其實也隻是「馬華文學的對照組」而已。另一方麵,作為「馬華文學的對照組」,就算馬華文學無意趨近國傢文學,國傢文學的存在,總已是在提醒馬華文學的「在野屬性」、民間色彩、邊陲位置、社群性質、語係歸類,甚至民族文化政治角色。
莊華興可能是當代馬華學界對國傢文學的議題、操作與踐行最為關注的人,除瞭華巫巫華雙嚮翻譯(「翻譯馬華/翻譯馬來」)之外,自己也兼以馬來文書寫小說。由於他自身的實踐經驗,華興提齣「土生性馬華(文學)」的概念「以取代本土性/地方性論述」,並建議馬華作傢將自己的書寫IOS「升級」為雙聲Siri(或培養第二專長),成為「華馬雙語作傢」──朝嚮華馬雙語創作努力,旨在「匯入國傢文學主流」(即「迴歸國傢文學」)與突破馬華文學的睏境。這當然是個弔詭的說法。以當今日教育現況而言,國民中學畢業的非馬來裔的馬來文/國語應當是頗佳的,如有文學創作慾望的話,用馬來文創作應當沒問題,但獨中生呢,恐怕馬來文優異者不多吧。馬華作傢除瞭碧澄與華興自己等少數人外,多半不會去召喚一個異族魂來和民族魂共居一室(不是說「峇哈撒者族魂也」嗎?)。非不為也,實難為也。當然,將馬華作傢的雙語文學錶現(兼具馬華/華馬屬性)作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異托邦,也不是壞事。二○○四年底,華興和錦樹即在《星洲日報》針對國傢文學的議題分別寫瞭幾篇文章交換意見,錶述彼此分歧的看法與不同的立場;這些文章後來收錄在華興編/著的《國傢文學:宰製與迴應》書中。
當年莊華興預言道:「就目前主觀條件與客觀形勢衡量,雙語創作正是時候」, 可是十多年過去瞭,今天馬華作傢的雙語創作大好形勢並未冒現,華興所說的一個「多語-國傢文學」仍然是烏有鄉的話語。我戲言的「峇峇文藝復興」當然也還是子虛寓言。今年夏天,錦樹、嘉謙和我趁到新紀元學院參加「馬華文學與文學理論營」之便,約華興在加影的「富爸爸餐室」(老友許友彬說PappaRich該譯做「老子有錢」,妙哉斯譯)喝咖啡敘舊,大傢談笑甚歡,顯然生命中有些情誼是大於論學的立場,而立場的分歧未必一定要告別情誼。即使是「論述上的敵人」,也沒有必要因立場有所分歧而形同陌路,或造成心頭的芥蒂。
彷彿分歧與告別纔是黃錦樹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論文集的主調。是的,告別,纔不會原地踏步。作為時間的倖存者,我們唯有嚮前走,繼續工作與生活。馬華文學史裏頭的「華文小文學作傢」,在過去的時間與空間裏,想必也是這樣。他們不是覺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覺得永遠寫不好;但是他們的作品寫得好或不好,其實是讀者和批評傢的事。身為寫作者,他們唯有嚮前走,繼續書寫與生活。換句話說,華文小文學作傢,唯有告別「不是覺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覺得永遠寫不好」的「馬華人的睏境」,纔不會一直在爛泥河嗚咽。
分歧的不會隻是文學、文學政治或文學史。陳平口述的《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 2003)也是歷史分歧之書。馬共史是馬來西亞的歷史分歧/斷裂敘事,馬共史本身也諸多分歧的內史外史。當各方歷史(histoire/history)轉化成「馬共書寫」(histoire/story)時,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該如何「歷史化」這些記憶文本與文學文本裏頭的暴力怪獸?《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集中近三分之一的論文處理的正是「書寫馬共」的議題。在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閤艾和平協議之前,政府視「馬共」為公共空間的禁忌(馬來西亞的用詞是「敏感問題」),論者鮮少,但九〇年代以來,各種記憶文本與文學文本紛紛冒現,論者仍然不多,黃錦樹創作「馬共小說」之餘,以這幾篇「書寫馬共」論述作為馬華文學的身分屬性與國族認同的「補述」,或「一個想像的左翼南方」的注釋,自有其文學史的重要意義。
這本論文集另一個聚焦之處為「在臺馬華文學」(錦樹曾形容之為「臺灣租藉地」、「旅臺文學特區」)。黃錦樹觀察瞭在臺馬華文學在馬華文學複係統的「既內又外,既外又內」位置之後,提齣在臺馬華文學是「無國籍華文文學」的說法。錦樹的做法不僅是要描述在臺馬華文學的定位,更是繪測一個「第三空間」的可能──「與民族/國傢保持一種創造的緊張性的華文文學」。我自己覺得若擺在國傢文學的意識形態脈絡來看,馬來西亞華語語係文學,或可用「有國無籍」來形容,而「在臺馬華文學」之於臺灣文學,當然也是「既內又外,既外又內」,可視為「有籍無國」,因為基本上那是寫在傢國之外的(再/後)離散書寫。不過,漸漸地,我們也替這些文庫找到一個分歧的開端──「臺灣熱帶文學」──的空間。
我們當然很清楚,「在臺馬華文學」並不是散發臺灣文學獎靈光的產物,而是冷戰時代東西對壘的餘緒,在中、臺、馬的人民共和國-民國-臺灣-大馬聯邦之間的縫隙中開岔展顏。如果沒有冷戰,如果沒有「僑教」與「美援」,「如果父親寫作」,也是在那塊叫或不叫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或北婆羅洲聯閤邦的土地上,以華、巫、和/或英文書寫,在「我們的米格爾大街」──我們的Jalan Besar。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06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小說香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小說香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刻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刻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迴首我們的時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迴首我們的時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抒情與史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抒情與史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靈颱無計逃神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靈颱無計逃神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雨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雨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現代的誘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的誘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灰闌”中的敘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灰闌”中的敘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圖書標籤: 黃錦樹 馬華文學 黃錦樹 民族文學 比較文學 中文文學研究 馬來西亞 少數文學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書中對理論的綜述極多,比如人類學著述的發展曆程,急躁等待聯係馬華文學的段落齣現,這樣的過程中反思到我是不是也將一個異己作為新奇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瞭呢。馬華文學甫建立就是政治性極強的,沒有濃厚的商業目的(現實因素限製),創作者反而安心做一個文學的手工藝者(這個詞讓我有點在意)。跟蕉風有關的,除瞭前言中提到瞭它第一次改版的現代主義趨嚮外,另外就是談韓素音的同時一起提到的南來文人方天白垚的迴觀傢國、忽略大馬本土最尖銳問題的評判。另外發現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天在寫作和人生路途中的獨特性,但是我看到介紹都叫“迴國”,有點意思。
評分書中對理論的綜述極多,比如人類學著述的發展曆程,急躁等待聯係馬華文學的段落齣現,這樣的過程中反思到我是不是也將一個異己作為新奇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瞭呢。馬華文學甫建立就是政治性極強的,沒有濃厚的商業目的(現實因素限製),創作者反而安心做一個文學的手工藝者(這個詞讓我有點在意)。跟蕉風有關的,除瞭前言中提到瞭它第一次改版的現代主義趨嚮外,另外就是談韓素音的同時一起提到的南來文人方天白垚的迴觀傢國、忽略大馬本土最尖銳問題的評判。另外發現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天在寫作和人生路途中的獨特性,但是我看到介紹都叫“迴國”,有點意思。
評分書中對理論的綜述極多,比如人類學著述的發展曆程,急躁等待聯係馬華文學的段落齣現,這樣的過程中反思到我是不是也將一個異己作為新奇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瞭呢。馬華文學甫建立就是政治性極強的,沒有濃厚的商業目的(現實因素限製),創作者反而安心做一個文學的手工藝者(這個詞讓我有點在意)。跟蕉風有關的,除瞭前言中提到瞭它第一次改版的現代主義趨嚮外,另外就是談韓素音的同時一起提到的南來文人方天白垚的迴觀傢國、忽略大馬本土最尖銳問題的評判。另外發現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天在寫作和人生路途中的獨特性,但是我看到介紹都叫“迴國”,有點意思。
評分書中對理論的綜述極多,比如人類學著述的發展曆程,急躁等待聯係馬華文學的段落齣現,這樣的過程中反思到我是不是也將一個異己作為新奇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瞭呢。馬華文學甫建立就是政治性極強的,沒有濃厚的商業目的(現實因素限製),創作者反而安心做一個文學的手工藝者(這個詞讓我有點在意)。跟蕉風有關的,除瞭前言中提到瞭它第一次改版的現代主義趨嚮外,另外就是談韓素音的同時一起提到的南來文人方天白垚的迴觀傢國、忽略大馬本土最尖銳問題的評判。另外發現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天在寫作和人生路途中的獨特性,但是我看到介紹都叫“迴國”,有點意思。
評分書中對理論的綜述極多,比如人類學著述的發展曆程,急躁等待聯係馬華文學的段落齣現,這樣的過程中反思到我是不是也將一個異己作為新奇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瞭呢。馬華文學甫建立就是政治性極強的,沒有濃厚的商業目的(現實因素限製),創作者反而安心做一個文學的手工藝者(這個詞讓我有點在意)。跟蕉風有關的,除瞭前言中提到瞭它第一次改版的現代主義趨嚮外,另外就是談韓素音的同時一起提到的南來文人方天白垚的迴觀傢國、忽略大馬本土最尖銳問題的評判。另外發現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天在寫作和人生路途中的獨特性,但是我看到介紹都叫“迴國”,有點意思。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夢寐以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夢寐以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流動的身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流動的身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卵生年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卵生年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迴到馬來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迴到馬來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故事總要開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故事總要開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我的青春小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的青春小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浮艷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浮艷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馬來西亞華語語係文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馬來西亞華語語係文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蕩漾水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蕩漾水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在逃詩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在逃詩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山神水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山神水魅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清晨校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清晨校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東京有個綠太陽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東京有個綠太陽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跳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跳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因時光無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因時光無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句號後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句號後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考古文學“南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考古文學“南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民國的慢船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民國的慢船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