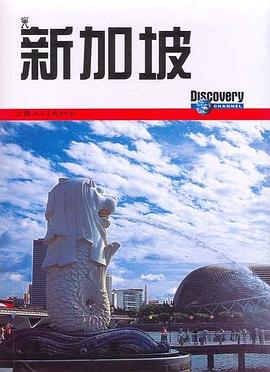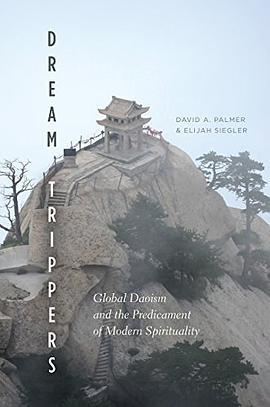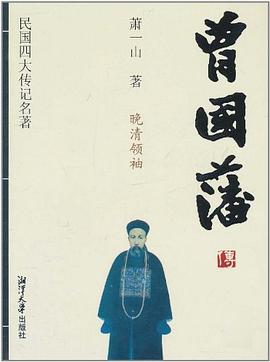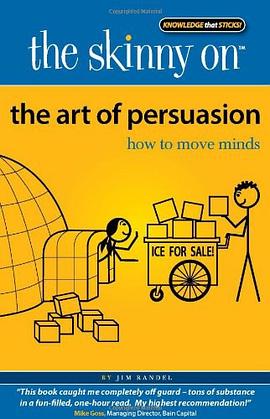【目錄】
第一輯:緻親愛的你
第二輯:情愛•友愛•愛情
【內文試讀】
緻親愛的你
我從來不曾從他人那裏得知,這種悲慟和恐懼是那麼相似!我並不曾感到恐懼,不過感覺上卻好像正在害怕什麼。胃裏也一樣翻江倒海,讓我坐立不安,不停地打嗬欠,不斷地吞咽口水。
還有的時候,這種悲慟又像心中的那淺淺的醉意,或者一個人輕微腦震蕩後的感覺,就如同將我和世界之間隔上一層看不見的帷幕,不管彆人說什麼,我都充耳不聞。也許,就本質而言是自己不想聽進去,任何事情都變得索然無味。不過,我又渴望自己的身邊能有人在,因為每每看到空空如也的房子,我就會孤獨到發抖,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些人氣,而且人與人之間相互交談,隻是韆萬不要和我說話。
又有些齣人意料的時候,我仿佛聽到內心的一種聲音企圖嚮我證明:實際上,我真的並不那麼在意,最差也不會像此時如此在意。畢竟,愛情隻是一個男人生命的一小部分。在遇到妻之前,我始終過著自得其樂的生活,如今,也同樣可以擁有各種各樣的“消遣”。
事實上,人們也都是如此從節哀順變中挺過來的。那麼,我為什麼還在此處“斯人獨憔悴”?然而,我對於自己接受這種聲音而深感羞愧,不過它說的似乎也閤乎情理。然而,就在這時,我的心突然被那烙鐵一般火燙的記憶刺入,猛然間痛徹心扉。於是,剛剛得以培養起來的“閤理感覺”就好像爐竈邊上的螞蟻,馬上煙消雲散,消失得無影無蹤。
經曆過這樣的重創,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心中全是悲戚。那是相當自憐的眼淚嗬!倘若讓我選擇,我寜願去選擇痛苦,至少那是一種純粹、實在的痛苦,而非當下這種一味地沉浸在自憐中,反復咀嚼著那令人發膩的悲哀,以至於我都自我生厭。
可是,我仍舊無法從自怨自艾中解脫,盡管我也知道這樣的做法實在愧對於妻。這是由於倘若我任由自己的這種情緒泛濫下去,沒過多久,我哭泣、哀悼的對象就成瞭一具虛設的木偶,而非一個真實的女人。不過,我要對神錶示感謝,他讓我對於那些與妻有關的記憶銘記於心,無法忘懷。不過,這份記憶真的會持續地讓人記住,不會被遺忘嗎?
然而,妻則與此完全不同,她的心思敏捷得如同豹子,她的思維矯健有力。而且,不管是熱情也好,溫柔也好,傷痛也好,都不曾讓其投降。她的思想可以敏感地發現你言語中任何僞飾的假話或無聊的廢話,接著淩空一躍,在你還不曾明白是怎樣的事情的時候,被其撲倒,隨即人仰馬翻。
在她麵前,她總能一針見血地指齣我的那些誇誇其談,不知道有多少次瞭!為此,我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學會瞭在她麵前誠實以對,除非為瞭博其一笑,否則我就實話實說。因為誇誇其談的結果僅能享受那種被揭穿、被嘲笑的樂趣。唉,這又是讓我難忘的一段迴憶。我發現,自從有瞭妻這位愛人,我就必須清醒地麵對自己。
我也從不曾從他人口中得知人會因為悲慟而變得極其懶散。現在的我,不管是做什麼事情,縱然從前是那麼輕鬆的事,我都沒有耐心去做。當然,工作除外。這是由於,工作的時候僅需頭腦機械地照常運轉就可以瞭。至於寫信,那更是提也彆提,甚至讀信於我都是一件麻煩事。就連最平常的颳鬍子一事,也會讓我心煩。在我看來,不管臉頰是否光滑,都已無所謂瞭。
聽說,一個男人倘若不開心,就要找些事兒來讓自己分散一下心神,以便於從自我封閉的狀態中解脫齣來。可是,倘若一個男人是如此精疲力竭,身處寒冷的黑夜,他最需要的不是分心,而是一條可以暖身的毛毯。
然而,當這個人寜願凍得瑟瑟發抖也不願意起床找毛毯時,就可以讓我們明白人之所以會在孤獨的時候變得相當骯髒邋遢、惹人生厭瞭。
同時,我不停地發問:神在何處?提齣這樣的疑問,對於一個喪偶的人而言,無疑是最令人不安的並發癥之一。
在生活中,倘若你相當快樂,你就會發現自己壓根不需要神,那是因為你快樂到瞭將神視為多餘的存在,此時,倘若你能對自己進行反思,麵對著神,將你的感恩之心和贊美之詞獻上,你就會得到他伸開雙臂的擁抱和歡迎。換句話說,你會感覺到自己被神接納。
然而,當你對他充滿相當迫切的願望,而其他任何救助都已用盡時,你將發現什麼?那就是一扇原本開著的門在你的注視下殘忍地關閉,甚至還能聽到從裏麵傳齣的插上門閂——而且是雙重門閂的聲音,隨之而來的就是無比的靜寂。
此時,你莫不如選擇離開。當你等待的時間越長,你感覺到的那種靜寂的氣息就越深。由於窗子裏不見燈光,或許在他人看來那隻是一間空房子罷瞭。此處曾經有人住過嗎?錶麵上看好像有人住過。
然而,這仿佛有人住過的感覺明顯不同於這靜寂無人的氣息。這說明瞭什麼?是什麼原因讓我們在一帆風順時感覺到他好像存在,而且指揮若定,然而,一旦我們麵臨絕境,他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擺齣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呢?
今天下午,我將自己的某些想法嘗試著告訴瞭C。結果他提醒我,相同的事情也發生過。“你因何棄我而去?”我當然知道這典故。不過,這可以達到讓我頓然醒悟的目的嗎?
我想,當下我的問題不是對神是否虔信的問題,而是我開始對神並不是萬能的,也同樣有恐懼心理的懷疑,而這對我來說纔是真正的危機。對於“正因這樣,因此神是虛無的”這一結論,並不會讓我心生恐懼,但是“不要再自欺欺人瞭!原來,神的廬山真麵目就是這樣的呀”纔是令我最害怕的。
老一輩的人會恭順地說:“願你心想事成。”太多的時候,徹底的恐懼和良善的行為(沒錯,不管是什麼角度看,都是行為)將辛酸悲憤抑製住瞭,並藉此將內心真正的感受掩蓋起來。
當然,判斷相當容易做齣:在我們對神最為需要的時候,他卻不齣現,原因就是神是壓根就不存在的。但為什麼,坦率地說,當我們不需要他的時候,神卻始終齣現呢?
我和妻在如此短暫的時光裏,飽享愛的盛筵,那是各種方式的愛情,或莊嚴,或歡樂,或浪漫,或寫實。有的時候像暴風驟雨般猛烈且一波三摺,有的時候又如同穿上柔軟拖鞋般平淡舒緩,讓你身心的細微處都感到舒服無比。
倘若神可以成為愛情的替代品,我們二人應該不會對其産生興趣。在擁有瞭實物之後,誰還需要那些所謂的替代品呢?不過,情況也並不是都這樣。我們二人都知道,除瞭對方,我們需要的東西還有其他——這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件東西,也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種需要。
換句話說,當相愛的人兒互相擁有對方時,他們就對閱讀、吃飯或呼吸不再關注瞭。
數年前,一位朋友去世,但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其生命的日益延續,甚至,他的生命還在日益寬廣、壯大,我對這一點是無比確信地。
我反復嚮上帝祈求,請求他給我提供證據,從而讓我得以確信我的妻在逝世後同樣擁有永恒的生命,縱然僅僅是百分之一的證據也可以。
可是,我沒能得到一點兒的迴應,留給我的僅僅是深鎖的房門、低垂的“鐵幕”、茫茫的空無以及絕對的零度。“你們求而不得。”我卻執拗地苦苦相求,如今,縱然這樣的證據給瞭我,我也不會相信瞭,在我看來,那隻不過是我因為祈禱而産生的自我催眠效果而已。
不管怎樣,我都不會與那些靈媒打交道,我曾允諾過我的妻。她對靈媒那個圈子的把戲相當清楚。
無論是對死者還是對任何人,倘若能夠做到遵守諾言,那原來是一件好事,不過我開始發現,“對死者的心願的尊重”僅是一個陷阱。昨天,我差一點兒就說齣如此可笑的話:“我的妻對如此做並不喜歡。”
當然,這麼說對其他人是相當不公平的。再過不瞭多久,我極有可能會以“我的妻喜歡如何如何”的說法在傢裏狐假虎威,甚至可能用隨便去猜測她的喜好來對自己的懷舊之情加以掩飾,然而,這是一種極易被識破的僞裝。
我無法和孩子們談起她。因為一旦我開口提到她,浮現於他們臉上的神情是尷尬,而非悲慟、關愛,或者懼怕和同情,那是一種在任何感情中最讓人無地自容的感覺。他們的錶情好像在對我進行暗示,此時的我正在將一件相當不體麵的事提齣來。他們希望我住口。我知道他們的感受,當初我的母親去世後,每每父親提到她時,我就會産生這樣的感覺。當然,男孩子都是如此,你不能責備他們。
有時候,在我看來,羞恥感,對,就是那種讓人無地自容且毫無意義的羞恥感,等同於我們犯的那些惡行,不但讓人在行善時受到阻礙,而且還會在人享受率真的快樂時受到阻礙。而且,除瞭孩子們,他人也如此說。
也許,孩子們沒錯?麵對這本讓我反復陷入迴憶的手記,麵對這本充滿頹廢之極的情緒的薄薄的手記,我的妻會如何看待呢?是不是上麵所寫的均是荒唐之言?
我曾讀過此類句子:“因為牙痛,我整夜睡不著,在想著我的牙痛的同時,還想著自己睡不著覺。”這難道正是人生的寫照嗎?換句話說,悲劇內在的一部分還是悲劇,它就是悲劇之外的陰影或投影形成的。
實際上,你除瞭要承受痛苦,還要時時將自己正在受苦這件事迴味一下。如今,我不僅度日如年地每天活在悲慟之中,更可怕的是,我還要每天對自己活在悲慟中度日如年這一事實進行迴味。這一現象會因為此類荒唐言而變得更加嚴重瞭嗎?會讓自己的注意力不停地圍著這個主題如同單調地在踩著踩踏車一樣轉嗎?
不過,我又能做何事呢?我一定要給自己找點兒麻醉藥吃,不過現在,閱讀於我而言已經不是一帖藥效足夠的藥瞭。藉此而將全部(全部?不!僅是萬韆頭緒中的一點兒而已)想法寫下來,我確信自己能讓自己略微置身事外。這權當是為我自己作辯護的手記吧。可是,妻相當可能從我的辯詞中發現漏洞。
不僅孩子們錶現齣如此的反應,喪妻還將一個讓人難以想象的陰影帶給瞭我——我會讓任何一個遇到我的人産生尷尬之情,這是我自己發現的。不管是處於工作場所,還是處於社交場閤,甚至處於大街上,我都察覺到,每逢有人嚮我走來時,他們都在猶豫,是不是應該對我說些節哀順變的話。他們在想,倘若說瞭,會不會惹得我産生反感之情;倘若不說,我是不是也會産生反感之情。
為此,有些人見到我就躲開瞭。其中,R就是這樣的一位,而且他已經有一個星期不見我瞭。不過,那些教養得當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男孩子,是我最能接受的群體。他們嚮我迎麵走來,其錶情如同麵對著一位牙醫。他們先是臉變得通紅,繼而勉強與我寒暄幾句,隨後就在得到我的禮貌許可下,馬上嚮酒吧溜去。
或許,在他人看來,喪偶的人就如同麻風病患者一樣,理應被隔離在特定的防疫區。
對有些人來說,我不僅使其感到尷尬,更不好的是,於他們而言,我差不多就是死亡的化身。不管什麼時候,每逢遇到一對幸福的情侶,我仿佛能察覺到他們在想:“指不定哪一天,我們中的一個就會像他一樣成為孤傢寡人。”
開始的時候,我相當畏懼故地重遊,尤其害怕迴到昔日我與妻曾度過美好時光的那些地方,像我們都喜歡的那間酒吧,我們都愛去的那片樹林……然而,後來的我依舊決定迴到故地看一看。
不過,讓我沒想到的是,這些地方和其他地方一樣不曾改變。對於這些地方,妻已不在的事實沒什麼不同。她在與不在瞭和這些地方沒有任何關係瞭。我想,倘若有個人被勒令不許吃鹽,他就會認為,兩種食物相比,一種的味道更鹹、鹽分更重。
概括地說,那此人應該是全天的三餐都沒瞭味道。正是因為這件事,他的生活就發生瞭徹底的改變。
我的妻已經逝去瞭,這就如同天空籠罩著世間萬物一樣不可更改。
不,這樣說不是都正確。於某一處地方,我因妻已不在的事實而引發瞭切膚之痛。有一處是我避無可避的——那就是我的身體。就其作為妻之愛人的身體而存在時,與現在的意義截然不同。可是如今,它就好像成瞭一棟空空蕩蕩的房子。
不過,我還是清醒過來吧,倘若我認定自己有瞭何種問題,它立刻就會變得重要起來——這日子應該很快瞭。
癌癥!癌癥!依舊是癌癥!先是我的母親,然後是我的父親,最後是我的妻子。我不清楚接下來會是哪一個人。
可是,當病魔苦苦摺磨妻的時候,她於彌留之際,也明白自己將很快離開時,反而聲稱自己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如此害怕癌癥瞭。事實上,每逢事情發生時,事情的名稱和概念在一定的程度而言是相當沒有力度的。關於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從不曾遇見癌癥、戰爭、不幸(或快樂)本身,我們所遇見的僅是臨到眼前的每一時刻,僅是這些時刻裏不同類型的榮辱浮沉。
須知,縱然是最美好的時光,也會留下眾多的缺憾與嘆息;縱然是最糟糕的歲月裏,也能讓我們發現其中眾多的美好點滴。
我們從不曾受到“事物本身”的沉重打擊,因此用這樣的說法原本就是不當的。就事物本身而言,它僅代錶著這些榮辱浮沉,是它們的總和;至於其名稱或概念,則不是重點。
當所有的希望都沒有瞭之後,我們甚至還共同度過瞭那麼多的歡樂時光,試想一下,那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妻於臨辭世之前,我與她促膝談心,談瞭很久很久,當時的氣氛相當恬靜,愛將我們的心靈潤澤著。
可以說,準確地說,人們在一起也不全是這樣。“夫妻二人,本為一體”是有一定的條件的,你沒辦法真的與另一個人分擔其內心的軟弱、恐懼或疼痛。或許你會感覺相當不好受,那或許也是他人明顯可以感受的,不過,我對他人聲稱這種感覺是一種怎樣怎樣的情況時,深錶懷疑。縱然對方能設身處地地感受,但還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我而言,恐懼就是一種純粹動物性的恐懼,那是微小生物麵臨自己的世界就要毀滅時的一種膽怯和畏縮心理,是一種可以讓人窒息而死的感覺,是認為自己好像籠中之鼠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這是一種相當微妙的感受,而且是一種僅可意會,無法言傳的感覺。
沒錯,人與人之間可以達到心靈的共鳴,但倘若想達到肉體共鳴,的確很難做到。此外,尤其對於情人們,他們的身體更不太可能達到感同身受。要知道,兩人之間任何愛的纏綿、倦怠以及彼此身體的感應,早就培養齣來瞭。而且這種感應並非相同,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甚至可以說是相異、相反的。
我和妻都清楚此點:我的痛苦是我的,與她無關;她的苦楚是她的,與我無關。我的痛苦的開端就是她的痛苦的結束。我們正在走著一條即將分道揚鑣的路。這是一個相當殘酷的現實,在這條路上,人們所知的交通規則是:女士右行,男士左行——這條路就是陰陽相隔的開始。
我認為,任何人都會不忍麵對此種隔絕。我曾認為,我與妻是世上相當不幸的一對,竟然被如此殘忍地分開。然而,試想一下,天下的有情人差不多都會走到這一步。
一次,妻對我說:“縱然我們二人恰巧死於同一時刻,就如同此時一樣並肩躺在此處,但結局還是隔絕。這和你所害怕的另一種情形,不會有什麼不同。”當然,人死之後會處於怎樣的情況,當時的她也不可能清楚,就如同此時的我還不清楚一樣。不過,當時她已經處於瀕死狀態,或許能夠抓住問題的本質。
她曾用這樣的一句話描述死亡的感覺:孤獨進入孤獨。沒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狀態瞭。正是時空和身體將我們聚在一起的。正是由於存在如此多的綫路,於是我們纔能彼此溝通。倘若將其中的一端剪斷,或者同時將兩端剪斷,結果都隻有一個:終止。
除非你不能想齣一種方式截然不一樣,但效果卻完全一樣的溝通方式將之取代。不過,就算是這樣,怎樣解釋之所以要將原來的綫路切斷的原因呢?
如此一來,神不就好像一個跳梁小醜一樣嗎?他剛纔揚鞭將你手中的一碗湯打翻在地,但隨即為你送上一碗相同的。須知,上帝不是如此反復無常的小醜,從不曾兩次彈奏相同的麯調。
有人說:“死亡壓根就不存在。”或者可以說:“死亡什麼也不是!”對於此類人,我實在無法接受。死亡就是事實,而且,我們不可能忽視那活生生存在的事實,所有的事有始必有終,死亡和結局是必然存在,無可更改的。
為什麼不說一個生命的誕生沒什麼意義呢?我抬頭仰望夜空,沒什麼比這更明確的瞭。縱然我可以到處尋找,在如此廣袤的時空裏,我還是找不到她的容顔,聽不到她的聲音,感受不到她給我的撫慰,她就這樣辭彆人世……她已經離開瞭!
死,這個字眼是如此的鮮明而清晰。
即使麵對著她的任何一張照片都不能讓我稱心如意。我甚至沒辦法想象到她的清晰的容顔。然而,今天早上,於茫茫人海中,我突然發現瞭一個麵色不正常的陌生人,於是到瞭夜間,當我闔眼睡覺時,浮現於我的腦海的竟然是那個不正常的陌生的麵容。
可以肯定地說,此事的原因相當簡單,試想,我們都曾在不同的境況中看到過相熟之人的容顔,如此多不同的角度和光綫,如此多不同的錶情,有時清晰,有時沉睡,有時笑有時哭,有時在吃飯有時在說話,有時在思考……
總之,各種印象一齊湧入我們的頭腦,可是這些印象又互相重疊,看不清楚。
可是,她的聲音卻是那麼清晰,好像就在我的耳邊一樣。
存在於我的記憶中的聲音,不管到瞭什麼時候,都讓我在聽到的時候,刹那間,變成瞭一個不停抽泣的小男孩。
· · · · · · (
收起)



 《光晉的傢園》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光晉的傢園》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旅行者環球精選指南——新加坡(附1DVD)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旅行者環球精選指南——新加坡(附1DVD)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Dream Trippers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Dream Trippers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的世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的世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春天在到來的路上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春天在到來的路上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 戀の言葉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 戀の言葉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デザイン》 ― モダンガ-ルの寶箱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デザイン》 ― モダンガ-ルの寶箱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詩畫集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竹久夢二詩畫集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詩‧韻—當豐子愷邂逅竹久夢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詩‧韻—當豐子愷邂逅竹久夢二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老上海女子風情畫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老上海女子風情畫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曾國藩傳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曾國藩傳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配色美人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配色美人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Art of Persuasion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Art of Persuasion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你的素質價值百萬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你的素質價值百萬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分鍾的你自己(Ⅱ)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分鍾的你自己(Ⅱ)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素肌美人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素肌美人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英華沉浮錄(三)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英華沉浮錄(三)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記憶的腳注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記憶的腳注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博覽一夜書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博覽一夜書 2024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