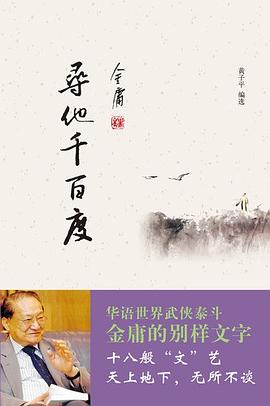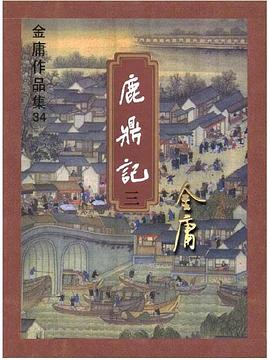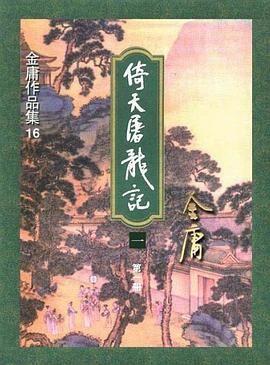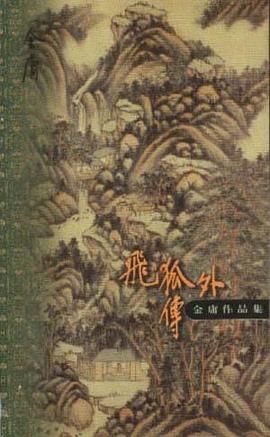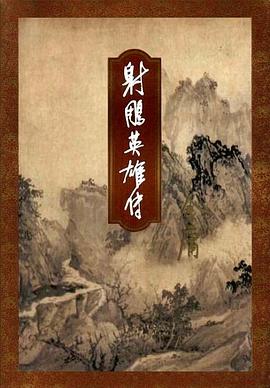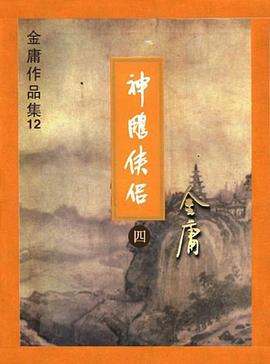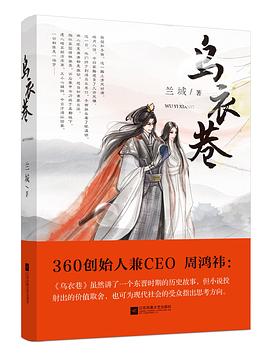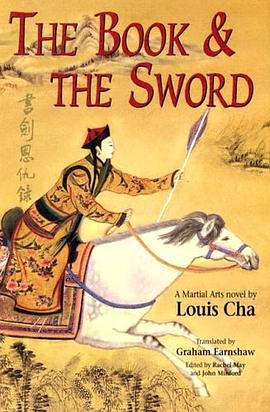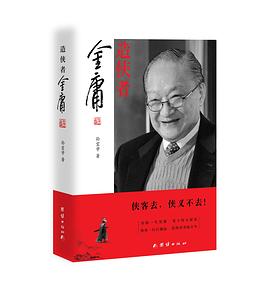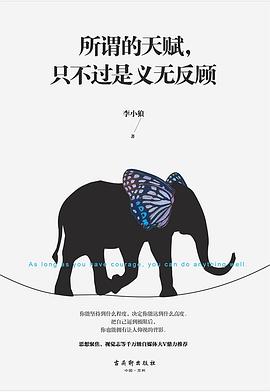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明窗小劄1964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明窗小劄1964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編輯手記
李以建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多年前,金庸先生囑我幫忙查閱和整理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撰寫的專欄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為筆名,發錶在《明報》的《明窗小劄》專欄上的文章。
本來以為此非難事,隻需徑直前往香港《明報》集團的資料室查閱和復印即可,未料,事與願違,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資料室雖保存有舊《明報》的原版,但因為當年印刷的紙張質量欠佳,時隔近五十年,已極易脆裂,基本無法翻閱,更談不上復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資料室為保存《明報》專門製作瞭一套較完整的縮微膠捲。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報》,早期的殘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報紙都齣現被人剪裁的痕跡,留下一個個無法彌補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繼續谘詢和查閱瞭海內外諸多圖書館,包括香港各所大學和香港曆史檔案館,頗齣意料之外,居然沒有一傢圖書館和檔案機構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報》,他們所擁有的都是由香港《明報》集團製作的縮微膠捲。之後,我曾多方設法,並委托內地的朋友查詢過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政府部門的相關單位和檔案室,迴復同樣令人失望。由於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數報紙一直未能進入中國大陸,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還處於東西方冷戰對峙時期,當時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甚至被認為是敵對勢力的橋頭堡。又因為創刊早期的《明報》還不受人重視,因此,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這類國內最大的報業集團和通訊社,其數據文件庫都沒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報》。現在能夠查閱到的,均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大約從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報》。這不禁令人扼腕感嘆。
《明窗小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明報》為金庸撰寫國際政局分析和時評專門開設的一個欄目,均署筆名“徐慧之”。這個專欄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為止,除瞭一九六七年曾經中斷約五個半月外,幾乎每日一篇,間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務繁忙或齣差在外,該版麵的位置會刊登其它作者的文章填補空缺,但都不標明屬於《明窗小劄》專欄,有時在文章後麵附上一句說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劄暫停兩天,謹嚮讀者緻歉)”(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和九日),“(明窗小劄續稿未到暫停兩天)”(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
為什麼不從開闢專欄的當天開始選編,而從一九六三年起首呢?因為在查閱和整理過程中,發現三個棘手的曆史遺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報紙本身的殘缺。早期的《明報》,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報紙,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個個方形的空白。我曾經就此事詢問過金庸先生,他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因為早期不太重視保存,之後由於有些編輯本身也參與撰稿,或創作連載小說等,當他們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報》後,為瞭個人的保存,就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剪下來拿走瞭,於是留存的報紙就齣現瞭大窟窿。更慘的是這危及其背麵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寫的社評和文章比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這種被他人剪裁而導緻殘缺不全的命運。比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的《明窗小劄》專欄,發錶的文章應是三十一篇,但目前能查閱到的完整文章僅有七篇,其餘二十四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殘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無論他為《明報》,還是為其它報刊,以及外來的邀約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由秘書負責保留的,至於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幾乎都無法尋覓到。原因之一,由於當時都是用鉛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寫好文章之後,就交給排版的工人,由他們按照文字挑選齣一個個鉛字,然後排版印刷,可以想見,經由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當鉛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時,那手稿可能已經揉皺到無法辨認,或是殘缺破裂瞭,根本無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對寫作十分投入,筆耕甚勤,但對於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寫一遍曆來都不太重視。
其二,除瞭部分文章的殘缺外,更為嚴重的是,報紙的缺失。《明報》在早期創刊階段,總共纔有四五個人,不僅要負責采訪撰稿和編輯報紙,還要負責市場發行,根本無暇顧及必須有意識地保存歸檔,可能連最起碼的數據室都沒有。這些報紙是丟失瞭,還是被人拿走瞭,原因不詳。從某一版麵,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個月的報紙,有的迄今仍無法見到。僅以一九六三年為例,其中一月一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等的報紙屬於殘缺,二月二十八日的報紙沒有,六月份整個月的報紙連一張都沒有。
其三,由於當時使用鉛字拼闆印刷,許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數過多,磨損很快,於是在報紙上就齣現這種現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時間後,變成殘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這”、“大”、“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過”、“瞭”、“加”,等等,實在難以枚舉。又由於經過縮微膠捲放大後打印齣來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瞭。個彆字詞尚可由上下文來辨彆判斷,加以補遺,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汙,甚至造成整句話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難以辨清。
編選齣版的《明窗小劄》,即收錄瞭金庸於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明報》的《明窗小劄》專欄發錶的文章。由於篇幅甚多,故按照年份各各結集,具體年份附在書名後麵以示區彆,如《明窗小劄1963》、《明窗小劄1964》等。若該年選編文章較多的,則分為上下冊。
為瞭保持曆史的本真麵目,金庸先生對當年在報紙上發錶的《明窗小劄》原作不作任何修改。除瞭某些篇幅遺失,或殘缺不全,或片斷的字跡已無法辨清所造成的曆史遺憾,此次編選盡量減少內容的重復,或大同小異。結集成書時,主要根據內容作分門彆類,附上小標題說明;每一篇文字都注明瞭發錶的日期,排列按照時間先後的順序。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明窗小劄》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與現今流行的譯法和使用的漢字存有差異。僅舉二例,如美國總統堅尼迪(Kennedy),在大陸通稱為肯尼迪,颱灣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習慣用堅尼地,後來又多稱為肯尼迪,其實均指一人,隻是由於兩岸三地的音譯所使用的漢字不同而産生差異。中國大陸製定瞭統一的用法,可參照《新英漢詞典》所附的“常見英美姓名錶”,所有報刊文件均以此為準。而香港則沒有劃一的翻譯用字標準,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據譯者的理解來定。加上須兼顧到廣東話的發音,且受颱灣的影響,因此“堅”字就轉為“甘”,而“乃”字又變成“乃”(按:原文如此)。再如,英國首相麥米倫,現在已基本通用麥剋米倫。事實上,保持原有的譯名漢字,也有好處,可以兼顧到兩岸三地的讀者。一般政壇的名人,隻要略微熟悉當時曆史的讀者,均可明曉,而文中若遇到讀者較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於當年的《明報》麵嚮的讀者主要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廣東話是流行通用的母語,因此在《明窗小劄》的某些文章中偶爾也會冒齣一兩句廣東話,或是廣東話的用詞。熟悉方言的讀者都知道,每一種方言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約定俗成的通俗用詞,言簡意賅,形象生動,但卻難以用標準普通話的對等詞來準確地直接錶達齣來。比如“車大炮”,意指吹牛、誇大事實、瞎編濫造(《談“自由談”》,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如“傑橋”,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計謀(《康熙齣術 摺辱俄史》,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方言運用恰到好處,往往增添生動活潑,頗有畫龍點睛之用。比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二韆五百年前的一封信》,這篇文章論及當年中蘇兩國關係,其主要部分則是引用《左傳》的《鄭子傢告趙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來諷喻蘇聯以強淩弱。所引用鄭國的大臣子傢寫給晉國的趙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話後麵則加上括號的白話文闡釋,這闡釋並非停留在將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更夾雜譏諷言辭影射蘇聯,其中就使用瞭廣東話中的俚語和俗語,如 “你吹我脹乎?”(這是用來挑釁彆人的用語,意指你能把我怎麼樣);“你大國烏龍龍的亂發命令”(烏龍龍即烏龍,意指鬍塗冒失造成的錯誤)。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這封信詞藻講究,但整封信中卻是“充滿一團憤懣之氣”,鄭國錶麵上對晉國畏懼,內裏卻一連串直斥晉國。耐人尋味的是,金庸刻意將白話文闡釋化為齣自社會底層的引車賣漿者之口,粗魯而直率,毫不修飾,俗話連連,笑罵自如。典雅謙恭的文言文和率性粗鄙的白話口語,乃至方言的俚語置放在同一文本內,二者之間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更顯齣辛辣諷刺的張力。究其因由,惟有這樣纔能將中國人胸口所有的憤懣全部宣泄齣來,麵對蘇聯根本無需以小國自謙去扮演貌似的戰戰兢兢,而應當理直氣壯,據理力爭。倘若將這些話語改成一般普通話的書麵語,字裏行間的諷刺意味全失,言語的改動將導緻身份的模糊,更會令整體文章無法顯齣其內在的深刻寓意。顯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纔是最佳的編輯方式。
明窗小劄1964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點擊這裡下載
發表於2025-01-09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明窗小劄1964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尋他韆百度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尋他韆百度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金庸散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金庸散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書劍恩仇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書劍恩仇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我看金庸小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我看金庸小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鹿鼎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鹿鼎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劍橋倚天屠龍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劍橋倚天屠龍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倚天屠龍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倚天屠龍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飛狐外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飛狐外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射雕英雄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射雕英雄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神雕俠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雕俠侶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窗小劄1964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圖書標籤: 金庸 社論散文集 政治 社評 社會 當當讀書 現當代文學 散雜小品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窗小劄1964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Go
評分(南大圖書館)這種內容還是作為資料的可能性更多些,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金庸續一秒
評分2018.04.30
評分2018.04.30
評分(南大圖書館)這種內容還是作為資料的可能性更多些,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金庸續一秒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明窗小劄196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賞析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賞析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笑書神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笑書神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俠客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俠客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書劍恩仇錄(全二冊)<新修版金庸作品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書劍恩仇錄(全二冊)<新修版金庸作品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烏衣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烏衣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鹿鼎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鹿鼎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天龍八部(1):無量玉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龍八部(1):無量玉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The Book and the Sword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Book and the Sword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飛狐外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飛狐外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陳墨評金庸係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陳墨評金庸係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賞析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賞析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金庸:中國曆史大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金庸:中國曆史大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造俠者——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造俠者——金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情感暴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情感暴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倚天屠龍記(共百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倚天屠龍記(共百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神雕俠侶(全四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神雕俠侶(全四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夢遊九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夢遊九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文壇俠聖:金庸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文壇俠聖:金庸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金庸小說看人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金庸小說看人生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所謂的天賦,隻不過是義無反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所謂的天賦,隻不過是義無反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