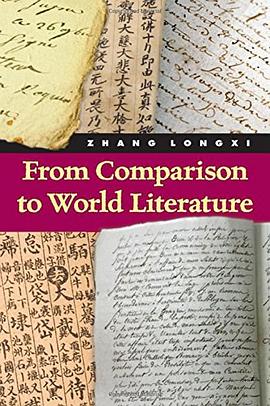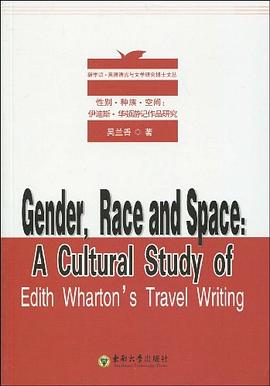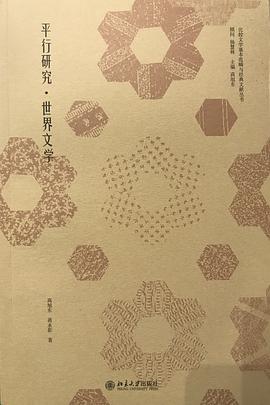具体描述
本書聚焦地方史及區域文化比較
探討「殖民地─帝國體制」朝向「總力戰體制」轉變之1932-1945年間
分踞帝國南北境的臺灣、朝鮮殖民地
如何以不同方式承受或轉化「戰爭帝國」引發的社會變遷?
曾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朝鮮乃至「滿洲國」等,在21世紀後殖民研究中如何相遇?
本書係雙邊研究之結晶,收錄10篇全新論文,並有合作紀要及研究介紹。
兩組學者從地緣政治、文化教養分析、文化政治、生命政治、欲望政治、性別研究、跨界影像、戰爭戲劇、思想史、文化翻譯等視野,
超越「壓迫/抵抗」、「民族抹煞」史觀,
精心獻出十五年戰爭期文化史最新解讀。
編者序
本書韓文版《作為「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力戰與韓國‧臺灣的文化構造》,已於2010年7月由韓國首爾的Greenbee出版社出版。從跨國研究組織結成、會議召開到論文翻譯、譯校、出版,事項繁多。兩年來,擔任「韓國研究小組」召集人的聖公會大學金艾琳教授,樂於承擔,悉心規劃,在此首先要感謝她與我並肩迎接了許多挑戰。此外,所有率直、熱情並以精采論文投入本團隊的韓國、日本、臺灣的學者們,也讓我油然充滿敬意。
此刻,我們將把《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的合作成果,獻給中文讀者們指正。帝國主義的擴張以及帝國主義之間的競逐和征戰,引發了巨大的歷史推力。受到德國影響的日本帝國「總力戰」,不同於過去的傳統戰爭,也不同於已成為今日戰爭基本型態的總體戰(Total War),故而在此次的共同研究中我們特意採取了此一歷史現場上的詞彙。作為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一連串帝國主義擴張行為之巔峰產物,它在1937年到1945年間正式成形。誠如標題所示,它導致的地理疆界、殖民統治權力界線、社會生活以及後殖民意識之變動,乃是「韓國臺灣比較文化硏究會」所有成員的共同關懷。我們嘗試探問的是: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時期,總力戰對被強制捲入其中的不同區位殖民地民族臺灣人、朝鮮人之世界圖景、歷史意識、民族認同、社會結構、日常生活,帶來了哪些衝擊?帝國與殖民地之間權力層位的變化,如何以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力量,影響統治界線與認同想像的位移?面對戰爭帶來的全體變遷,殖民地民眾如何調適、重建其「非常期」下的主體、社會關係、精神意識與日常生活?回應新現實,殖民地知識階層與一般民眾,表露了哪些不同於前期統治階段的憂慮、欲望,他們又如何掙扎、如何浮沈、如何行動?
我們發現,當帝國與殖民地被不可抗拒的總力戰體制拉進一個彼此更為貼近、更為相似的「皇民化」同一性結構之際,廁身帝國內部的被殖民民族,已然面臨到不得不在過往主張的「差異性」與「特殊性」戰略之外,尋求其它有利位置或後殖民戰略的時期。從總力戰開始前到實施後,前仆後繼的全方位變動,在政治、經濟、社會、日常生活,乃至思想、情感與欲望的領域擴延開來。戰時下、變動路、新體制、時局,正是這時代漫天飛舞的代名詞。透過臺、韓本土領域文化活動與文化結構的分析,我們一方面盼望從殖民地相互參照的共時性視野,指出在帝國誘導力、壓力或兩股力量的縫隙間,殖民地透過新的統治力學構造爭取出來的,一些別開生面的戰時殖民地文化政治及其成果。另一方面,在避免以均質化視野約化帝國/殖民地二元關係的前提下,也將針對處於戰時時空力學與殖民權力交叉作用的變動之網中,發生在被殖民者同一民族內部,因階級、年齡、性別、群體移居、個人越界之差異,所產生的各種社會認同、意識形態、生活與行動的分化或龜裂現象,提出更多說明。
任何工作的成辦,都是一群人同心耕耘的結果。從會議召開到中文版推出,本計畫能在臺開花結果,首先要歸功於行政院國科會、清華大學人社院的補助。其次,聯經出版社的肯定,發行人林載爵教授的支持,陳芳明教授「臺灣與東亞叢書」的企劃,編輯沙淑芬小姐的縝密用心,使本書研究目的能夠獲得彰顯。再者,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陳萬益所長的鼓勵、王惠珍教授的協辦、陳素主助理的行政協助,提供了有力後盾。計畫助理黃懿慧、蔡佩均,兩年來在學者聯繫、會務運作、稿件初編、校對、譯稿溝通各方面,盡心盡力的堅持與付出;以及「臺灣研究小組」學者們親身投入反覆往來的譯稿校勘之中,確保了本書的品質。此外,在兩研究團隊間搭起對話平臺的韓臺中日多國學者、翻譯家及學人,李永燮、李貞順、李珠海、李海鷹、焦艶、陳姃湲、裴英姬、山內文登、姜廷沃、李文卿、李善禎等,尤其功不可沒。最後,蔡文斌、石廷宇、郭靜如、陳運陞、吳昱慧、溫惠玉、陳正維、張育薰、徐淑賢等,參與會務或校對的臺文所研究生們,也都是本書的幕後英雄。
謹此感謝各方奧援,並誠摰地以我們這一群人的集體心血,獻給所有關心臺灣和東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們。祈願我們所共有的這世界,更加和平而美好。
選文
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陳偉智
一、前言
本文試圖透過對於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1907-1967)在1943年底於《興南新聞》文藝欄「筆劍進軍」系列中,發表的〈獻給決戰〉一詩的分析,討論戰爭與「文化」的關係,或者更精確的說,在決戰期,臺灣的知識人對於「文化」議題的思考,以及所呈現的世界史歷史意識。
戰爭時期臺灣的文化史,從戰爭動員體制的分析,「皇民文學」或是「興亞文學」的研究,乃至於對民俗文化或是鄉土文化的改造與挪用,歷來已有許多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重新檢視了戰爭期,特別是決戰期的臺灣文化史的複雜意識形態構圖,社會意識的轉變,與新的政治地理空間想像,強調臺灣人作為歷史行動者,其主體性形成的動態過程。
在上述新的歷史研究的脈絡中,吳新榮的位置,乃至其所代表的臺灣南部鹽分地帶(今臺南縣北門佳里一帶)的文學家們,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南部臺灣人的文學社群。決戰時期鹽分地帶同仁的活動與作品,在當代的研究中,往往強調他們在文學與民俗研究上所表現出來的地方特色。換言之,當代的研究者書寫文學史時,是把類似鹽分地帶同仁的活動,作為表現,乃至於保存「臺灣性」或是「民族文化」的個案,放在「抵抗」的系譜中,抵抗戰爭時期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意識形態動員。但這種從後來重建的民族敘事中所設定的抵抗位置,似乎忽略了這些人作品中呈現的時局色彩。
然而,即便是具有顯著的時局色彩,也不能單純地以協力者複製戰爭動員宣傳的評價,就予以否定。類似的狀況,我們也可以在「皇民文學」的討論中發現。但是若不只是簡單的否定,或是委婉地納入文學史的敘事中,歷史學家林瑞明所說的「騷動的靈魂」的存在,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探討戰爭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從後見之明來看,兩次世界大戰作為世界史的重要事件,在世界各地都觸發了不少知識份子思考戰爭的意義,同時也往往產生了重新思考「文化」議題的歷史契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歷史過程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不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中,也同樣觸發了臺灣知識人對於戰爭的思考。作為一個「世界史的」歷史性時刻,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思索著臺灣在歷史當下的狀態。「文化」成為突破這種狀態的思想嘗試,並進而形成一個相對於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基本範疇的獨立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化」以新造詞在臺灣登場,是作為表現或者期待一個與以往的狀態不同的、朝向未來的「現在」,一個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的語言符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戰本身被認為是一個世界史的歷史契機,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在形成,從而「文化」也在這樣的契機中,再次變成一個主題。吳新榮在〈獻給決戰〉中,最後以「啊!這一戰,大東亞之戰/新秩序的建設、新文化的創造」結束,雖然是在既有的戰爭論述設定的論述空間中,使這樣的想法得以呈現。然而吳新榮將戰爭開啟的歷史契機跟「新文化的創造」聯結在一起,進一步顯示「文化」不單只是戰爭動員的手段,更是戰爭的目的,一個具有時間意識自覺的新歷史階段的創造。
本文首先透過對〈獻給決戰〉文本的詮釋,分析其中呈現之以臺灣為中心的泛亞細亞主義空間想像,「文明─民族」為中心的地緣政治,以及對於新歷史階段的企望。接著分析此一文本的誕生過程,並討論吳新榮所鑲嵌於其中的同時代論述空間,以及在文本中反映的臺灣思想史系譜。
二、空白的第四期與歷史的瞬間
吳新榮在晚年發表的〈新詩與我〉一文中,將以往自己的文學活動與作品分為三期,並以之作為詩稿分卷的依據。這三期分別為青年時代於東京留學階段的「浪漫主義期」、1932年返臺後至二次大戰結束期間壯年時代的「理想主義期」、以及之後的老年時代的「現實主義期」。其中第二期的「理想主義期」是吳新榮自日本回臺以後至臺灣光復這一段時期的作品。這一時期吳新榮與朋友組織青風會,進一步發展成「鹽分地帶時代」文學社群,參與了全島性的文藝社團的活動。吳新榮對這一時期作品特色的說明是「我內心已藏有理想主義……這時代的作風比較意氣揚揚」,對外「公然宣言我們愛好自由、鄉土及藝術」,對內「就是糾合熱情的文化人,建設明朗的生活,把握健康的人生,而對立於阿諛強權之輩及低級趣味的黃色奴才。」這一次的作品整理,應該是吳新榮過世(1967)之前,對自己的文學活動完整的回顧。
〈新詩與我〉發表前20年,在戰爭的高峰期時,吳新榮也曾整理過自己的作品,給予分期分類,並賦予各階段的特色。1943年7月,吳新榮開始整理過去所寫的詩稿,打算集印為《震瀛詩稿》出版。在日記中,吳新榮表示:「因為現在正好是從一時代轉換另一時代的分界,而且自己的詩境已到了窮地,正好告一段落」。同時將自己文學活動與作品分為四期:「第一、搖籃期—東都游學時代。第二、前期—鹽分地帶時代。第三、中期—臺灣文學時代。第四、後期—」。整理詩稿的當時,則是「現在是第三期,故第四期尚未可知。」
在日記中,吳新榮提到了「現在」處於時代轉換的分界,自己也在自省「詩境已窮」之後,期待「另一個時代」的到來。這樣的時代自覺,反映在吳新榮對自己文學發展階段的分期。這一個被吳新榮有意識地設定的時代轉換,是一個在第三期的「臺灣文學時代」之後的階段,也就是在日記中寫的「第四期」,雖然「尚未可知」,但已經意識到了一個即將到來,但還沒有命名的階段。
吳新榮提到的第二期鹽分地帶,是他在1932年返臺後,以鹽分地帶同仁而活躍的時代。第三期「臺灣文學時代」則是指自己也擔任編輯委員的《臺灣文學》雜誌時代。《臺灣文學》雜誌於1941年由前臺灣文藝聯盟成員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等人成立的啟文社所出版,在當時被認為是與日本人文學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立場對立的文學雜誌。由於總力戰動員統合的強化,1943年底在「臺灣文學決戰會議」(11月12、13日)後,《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被合併,改名為《臺灣文藝》,改由臺灣奉公會發行。吳新榮在參加臺灣文學決戰會議時,在日記中寫下:「在時局決戰下,此會議具有歷史意義,為了戰爭,文學不得不奉獻決戰的決意」。但同時對於文學雜誌合併也感嘆並思索著:「文學之路值得走下去嗎?」若《臺灣文學》的消滅,意謂著吳新榮數月之前對於自己詩的文學活動分期中,第三期的結束。而這同時也宣告了未命名第四期的開始。1943年底到1945年戰爭結束前的階段,剛好是決戰期的高峰。〈獻給決戰〉一詩,即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轉換的當下發表。雖然在臺灣文學決戰會議後,吳新榮曾經感嘆此後的文學之路何去何從。但是很明顯地,次月(1943年12月6日)在《興南新聞》文藝欄的「筆劍進軍」專欄中發表的〈獻給決戰〉,似乎已經為決戰期自己的文學之路,找到一個方向。
這一個未命名的分期,指出了一個曾經存在過的歷史可能性的瞬間。戰後的重新分期,使這一個吳新榮特別劃分出來的短短一年多的決戰期消失了。然而戰後的重分類並不必然意謂著對於戰前歷史的消除。就吳新榮最後的分類來看,「理想主義期」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將決戰期的未命名的「第四期」也包含在「理想主義」的分期中,這倒是為我們指出了閱讀〈獻給決戰〉,撥開表面呈現的時局色彩迷霧外,進一步可以探究的方向,一個在決戰期共時性的世界史論述空間下,一些臺灣思想史歷時性主題的延續與發展。
三、在新高山上
既有的決戰時期的文學研究,多集中探討皇民文學形成過程中的認同政治問題,在最終變成日本人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中,尋找臺灣人集體認同的位置,並且試圖辨識在民族認同的這個身份範疇上,出於自願或者他力的認同變遷程度。這些研究,不論是強調國家政策、文藝政策、書籍流通與閱讀經驗等物質基礎之結構層面分析,或是針對文學家美學經驗、文學活動歷程、乃至戰時生活的再現經驗等行動者層面的分析,大致上都是在繪製「成為臺灣人,或者日本人」,乃至「或者都是」的民族認同的意識地表形構。換言之,戰時臺灣的文化史,一方面作為自1920年代以來逐漸成形的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化實踐形式的延伸。另一方面則是殖民者針對帝國臣民的國民形成同化要求中,異民族(臺灣人)與國民(日本人)兩種不同身份範疇差別待遇的時間政治(作為異民族不平等的「現在」與作為國民平等的「未來」),在戰時極端化的發展及其克服。殖民統治的時間政治,被轉換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認同的差別,殖民統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時間上(歷史階段)的差別,變成了空間上(民族文化)的差別。
如果決戰期的意識形態,是指日本帝國企圖在世界史的歷史進程中,透過空間上的回歸(東亞、黃種人、被殖民者、乃至「日本」),在時間上克服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進入一個在「近代」之後的新世界史階段,以求「東亞永遠之平和」(大戰詔敕)。那麼在這戰爭的世界史歷史哲學的論述空間中,就不單單只是存在著「變成日本人」(或者「皇民化」)由上而下的帝國國民統合政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被殖民者由下而上的抵抗與協力過程中,集中在民族認同政治的議題而已。戰爭,不僅突出了各種空間性的符號,例如大東亞圈、日本帝國、新秩序、皇民、日本精神,同時也刺激了對於時間的世界史歷史性的自覺。
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若與既有的同時代著重於民族認同政治的文本相互比較,則清楚地顯示了對於戰爭的世界史歷史性時間意識的自覺。〈獻給決戰〉一開始,「地軸不斷地在旋轉/歷史永遠在繼續」,在未直接明言戰爭的同時,把世界歷史的永恆發展,提到前面。戰爭,即將被歷史性的理解。
〈獻給決戰〉全詩分三段,第一段強調臺灣的地理位置,一個空間性的安置,呈現臺灣四周環繞的地理特徵:東為太平洋,西為亞洲大陸,北為日本群島,南為熱帶馬來群島,在這樣的地理空間中,「啊!這個島,我們臺灣/東亞的中點/八紘的關門」,臺灣位處正在發生的世界史事件的關鍵位置。
第二段則是把這一個物理性的空間位置歷史化,指出了臺灣地理位置所在的太平洋四方,曾經有過的歷史經驗。吳新榮以太平洋對面的麥哲倫海峽、巴拿馬運河,太平洋南端的澳大利亞,以及北端的阿留申群島四個地方象徵性的呈現近代西方對外的帝國主義擴張歷史。同時作為「我」的吳新榮,站在臺灣,在朝東方面向太平洋的位置上,將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周鄰地理,變成了再現世界史中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地理。從第一段到第二段的發展,是一個從客觀的地理空間變成歷史性行動所累積而成的歷史地理空間的發展。臺灣在這一個歷史地理空間中,也從亞洲大陸的附屬島嶼,轉化成當下世界史事件展開場所的太平洋的島嶼,從大陸進入海洋,「啊!這汪洋的太平洋/新時代的搖籃/新世紀的祭壇」。
第三段則是以太平洋島嶼上的煙硝,將戰爭象徵性地帶入。而此一戰爭,在前兩段發展出來的歷史地理空間中,被設定成是亞洲各古老文明─民族結盟再起的契機。在這一個世界史事件的戰爭中,在亞洲古老文明所代表的「勤勉」、「勇敢」、「信仰」、「天神」等精神性力量的結合下,即將克服之前以物質發展為核心的世界史階段,一個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與帝國主義海外擴張的「近代」。最後吳新榮並具體的強調了「這一戰」,亦即「大東亞之戰」的歷史性意義,「新時代」與「新世紀」正在太平洋這個歷史性的空間中展開,「新秩序」與「新文化」即將在克服西方近代的世界史事件中建設與創造。新的歷史契機,即將在歷史性的世界史事件的戰爭中,改寫以前歷史所累積下來的歷史地理空間,並超越前此累積下來的西方的、物質的「近代」,進入到一個在「近代」之後,以亞洲文明的復甦,民族平等的結盟、以及精神力量勝利的新世界史階段。
吳新榮在這首詩中,以作者「我」的立場,在各段中「站在新高山頂」上,分別「在思想」、「在眺望」、與「在呼喊」。如果第一段的「在思想」,意謂著建立在地理上「以臺灣為中心」的思考。第二段的「在眺望」,則「我」的視線明顯的是面對著太平洋。最後在第三段,站在新高山頂「在呼喊」,則是進一步的召喚在亞洲的各古老文明─民族的結盟,包含了「黃帝子孫」的漢人(包含臺灣人以及吳新榮自己在內),「成吉思汗後裔」的北方蒙滿游牧民族,「釋迦子弟」的南亞民族,以及「天神子孫」的日本人。在這三段中,「我」從靜態的思考,到視線投射遠方的眺望,到呼喊的發展,從個體「我」的內在出發,到透過「我」的視線延伸至敵性他者(英、美在太平洋的歷史據點),並進而召喚在個體「我」背後的那些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支配陰影下共同命運的友性他者(亞洲古老文明─民族),以形成一個新的集體連帶。
而「我」所在的位置新高山,不單只是象徵著臺灣而已。「站在新高山頂」召喚新歷史可能性本身,是一個充滿象徵性的行動。事實上,沒有哪一個臺灣地景,比「新高山」具有更多重的歷史意義了。「新高山」的命名本身,象徵著近代日本帝國在亞洲擴張的起點,也就是殖民地臺灣的獲得。1895年甲午戰爭後,臺灣變成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1897年,經初步的地理調查後,發現原來臺灣原住民鄒族稱為「Pattonkan」,或是臺灣漢人音譯為「八通關山」,或是以形意紀錄為「玉山」,在西方的地圖上則標示為Mt. Morrison的山,是帝國領域內海拔高度最高的山,因而明治天皇將之重新命名為「新高山」。地理空間的命名,從來就是一個權力在地表施作的刻痕,十九世紀中葉,當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完成地圖上臺灣島的海圖繪測,並將Pattonkan依「發現」此山的美國海軍船長之名命名為Mt. Morrison時,臺灣已經象徵性地進入了西方的「近代」。日本統治臺灣後的「新高山」命名,在地圖上改寫了西方命名。新的命名,意謂著日本在東亞區域的興起。最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吳新榮此一詩所呈獻的「決戰」,不是指1937年的中日戰爭,而是指1941年12月8日,在「攀登新高山」的開戰命令中,展開的太平洋戰爭。決戰時期的帝國意識形態,於再一次呼喚「新高山」之名的這個歷史時刻,不只是複誦帝國領臺初期已經改寫過的地名而已,而更是要創造新歷史。而帝國也將從與西方強國比肩的狀態,更進一步地超越西方。吳新榮詩中的「我」,立腳在這一個覆蓋了好幾層意義的「新高山」上,不是一個偶然的選擇,而是歷史的必然。
四、時間,或者空間;歷史,或者民族
仔細閱讀吳新榮的〈獻給決戰〉,如果放在當時的決戰時期言論空間中來看,其所呈現的歷史性,並不在臺灣人如何變成日本人的時間政治上,而是在世界史的時間政治上。這一點,讓吳新榮與同時代的皇民文學產生了明顯的區別。
從1941年周金波〈志願兵〉開始到1943年王昶雄的〈奔流〉、陳火泉的〈道〉,這些代表作使「皇民文學」成為決戰時期臺灣文學的標誌。不論作者們在皇民文學中想要表現的協力/屈從要素,或是戰後學者們在皇民文學中想要汲取的抵抗(積極的要求一視同仁或是消極抗議)要素,都還是在強調民族寓言或是民族敘述中,複製「日本」或「臺灣」的空間性意涵。吳新榮的〈獻給決戰〉則是少數臺灣文學家在空間性之外,試圖把握決戰的歷史性的時間意義作品。即便在〈獻給決戰〉中,吳新榮在第三段中召喚著各個亞洲的古文明─民族,似乎是呼應了當時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意識形態中東亞各民族團結在日本的領導下,反(西方)帝國主義的(日本)帝國空間意識。然而決戰本身,被當成一個世界史事件,將歷史帶向一個新的階段。戰爭對於吳新榮來說,不只是民族認同的身份政治而已,更重要的是新歷史的產生。
時間在〈獻給決戰〉中,不只是如同別的文學作品中的敘述性時間,只是鐘錶時間或是編年的數量單位,充當情節發展背景(如同皇民文學中周金波〈志願兵〉的「我、明貴、進六」,王昶雄〈奔流〉中的「伊東、林柏年」,陳火泉〈道〉中的「陳君」等主角們的自我意識成長與認同轉換的發展)。相對的,時間就是該詩的主題,一個本身具有質量的世界史的時間透過決戰展開。
吳新榮對於臺灣人的民族身份的處理,在〈獻給決戰〉中,則是為其留下了曖昧不明的位置。在第三段召喚華夏民族、蒙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印度民族、以及日本天孫民族時,臺灣人是作為「黃帝子孫」呢?還是「天神的子孫」?站在新高山頂面向太平洋,呼喊在自己周邊的亞洲各古老文明─民族的「我」,似乎又同時與「黃帝子孫」以及「天神子孫」有所區別。「我」雖然曾經是黃帝子孫的一員,但現在卻不是。正在進行中的皇民化運動,似乎也沒有讓臺灣人的「我」變成了天神的子孫的成員。作為臺灣人的「我」在〈獻給決戰〉中,雖然站穩在新歷史的發動點與中心位置(新高山),但卻以一種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曖昧位置,在新的世界史契機中,保持「我」所代表的臺灣人身份。在近代處於一種非國家社會(non-statist society)的存在樣態的臺灣人,在1920年代形成了集體身份認同的範疇之後,到了戰爭時期,既沒有因為國家的戰爭動員,就被國家透過國家作為行動主體的戰爭所吸收,也沒有回歸到一個黑格爾主義式的前政治階段的民族的範疇中。吳新榮似乎重新賦予了一個原來在以國家(作為理念或是作為實體)為行動者的世界史中並沒有位置的非國家社會(=臺灣),一個在新的世界史中的位置。
在戰爭動員的高峰期中,吳新榮以時間取代空間,以歷史取代民族,但同時又保留一個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國的曖昧的臺灣人位置。然而這並不意謂著吳新榮採取一種消極的等待歷史的發展,接受外力歷史發展的結果,而是期待著在世界史事件的決戰所開啟的歷史契機中,「我」與「我們臺灣」的新秩序與新文化,指向一個與現在歷史階段不一樣的未來。而這樣的態度,也說明了吳新榮在詩中對於「新高山」的挪用,在新高山這個場所累積的重層歷史經驗中,再一次地賦予新高山新的歷史意義。
五、哪一個戰爭
吳新榮的〈獻給決戰〉中的戰爭,如本文前面所述,是指太平洋戰爭。根據學者的研究,吳新榮對1937年的中日戰爭,跟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呈現了不一樣的態度,有很明顯的心境上轉折。他從一個在歷史之外的被動接受者,變成在決戰中看到了創造新文化的歷史契機的行動者。〈獻給決戰〉可以看成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吳新榮對於戰爭態度轉變後針對戰爭意義的思考逐漸累積而成的最後文本。
從1932年回到故鄉臺南佳里開業,吳新榮在1936年底,於日記中總結自己截至當時的「行事」時,寫下:「一九三六年將過矣,我這一年的行事實不少。第一進出臺灣文壇,第二步入社交界,第三獲得政治的地盤。」從第二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吳新榮大致上即在這三個屬於「公」的領域,被編入了日本殖民政府戰爭動員體系的地方末端,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雖然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吳新榮在當天的日記上短短寫了「正義如不滅,良心遍世界」。但是作為地方領導者,吳新榮與其家人,自然地被編進戰爭動員體制。從1937年10月開始,吳新榮參加了佳里防衛團、軍機獻納會、國民精神總動員佳里分會,並擔任幹部。夫人毛雪芬則是參加了愛國婦人會與佳里婦人會。這段期間,吳新榮也顯露被歷史捲進去,不得不配合的態度,在日記中寫著「時時都去服務集合,以為銃後大眾的指導者。免講如何,這是時勢,這是潮流」,以及「人人都有部伍,人人都順時勢」等感想。
這段期間,吳新榮也常常感嘆自己生活的墮落。在「時勢」之下,非但採取了一個消極配合的立場,這樣的心態,也反應在自己生活的改變上。相對於中日戰爭爆發前,明朗、充滿活力,立身出世與社會關懷並行的吳新榮,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日記中呈現的,卻是一再地退卻,在「娛樂、交際、與時勢」的目的下,「日日都打麻將食燒酒」,從而一再地感慨自己生活的「完全墮落」的吳新榮。最能代表吳新榮此時心境的,大概就是他在1938年在日記中寫下的感想:「我們的矛盾混亂愈來愈深,一切只待歷史的奔流來解決?我們靜的行動只待外力而得動的前進」。
日本帝國在此時強化總動員體制,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國家深入社會各領域,不論是內地或是殖民地,在總動員體制下,物質與人力皆朝向高度管理化發展。吳新榮身為地方領導者,日常生活深深的嵌入動員體系的地方末端。在戰時社會之下,曾經以「畸形的生活」作為被動的「無形的抗議」的吳新榮,到了1940年中,也開始改變對於動員體制與戰爭的想法。在此時的日記中,他多次寫下了自己心境的轉換:「在這地球的苦惱時代,豈能獨吾安然?無論對世界有任何細微之點,都應去貢獻」(6月11日),「防空演習……連愚直的民眾也漸漸組織化。吾人感受到東洋大胎動,世界大轉折的空氣」(7月6日),甚至在美日逐漸交惡時,吳新榮理解到「作為日德義同盟之應理解事物,要覺悟今後的敵國是美國與英國,從而,我臺灣成為最重要的地區之一矣」(10月3日)。1941年8月10日,吳新榮在日記中寫著:「一個人坐在書房中,無所事事望南壁的地圖。終於理清思緒,完成『臺灣中心說思考』」。以臺灣在東亞的地理位置,羅列了十則臺灣在東亞與太平洋區域中的地理環境特徵與地緣政治特點。〈獻給決戰〉詩中第一段呈現臺灣在東亞與太平洋地理位置的構想,大致上在1941年中就已形成。同年12月8日,日本攻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吳新榮在日記中寫著:「該來的事終於來了」,「這是前史所未有的決定性大事件,人人痛感,故極度緊張」,「地域性的戰亂終於擴大成世界大戰」。雖然並非意料之外,吳新榮感受到的「緊張」,是此一決定性事件「前史所未有」,意識到了現在是處在一個世界史的轉捩點,這種「緊張」感,類似同時代的日本知識人對於美日開戰所感受到「知的戰慄」的「特殊時點的感覺」。1942年12月9日為「大東亞戰爭」第一週年紀念,吳新榮在地方上奉公壯年團舉行的「曉天動員」中,演說時局。吳新榮在演講中提到:「南至澳洲雪梨一帶,白人的白澳主義迷夢已被黃色人種打破,北至阿留申群島的攻略,使北美洲有史以來頭一次看到東亞人的腳印」,並且在結論中強調「面對人類歷史大轉變時期,不站起來打的民族是墮落,不站起來打的國家將是落伍」。〈獻給決戰〉第二段西方帝國主義在太平洋南北活動的歷史地理,以及第三段亞洲古老文明─民族的興起的泛亞細亞主義,似乎也可以追溯到作品發表一年以前的公開演說。
吳新榮對於戰爭態度的轉變,從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消極,逐漸轉變到太平洋戰爭後,在臺灣中心論的地緣政治思考中,反西方帝國主義的世界史歷史意識的自覺中,正面地思考決戰所帶來的歷史可能性。原先作為外在力量的「歷史」,變成了自己也可以積極參與創造的「歷史」。
作者简介
韓國研究小組:
金艾琳(Kim, Yerim),延世大學國語國文學博士,現職: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院HK教授
金杭 (Kim, Hang),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HK研究教授。
白文任(Baek, Moonim),延世大學國語國文學博士,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學科副教授。
蘇榮炫(So, Younghyun),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HK研究教授
車承棋(Cha, Seungki),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院HK研究教授
臺灣研究小組
柳書琴,臺灣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惠珍,臺灣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石婉舜,臺灣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博士
三澤真美惠(Misawa, Mamie),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副教授
目录信息
中文版編者序柳書琴
合作紀要與會議重點(一)臺灣與朝鮮如何設法相遇?:殖民地文學的比較研究╱柳書琴
合作紀要與會議重點(二)「總力戰」下的殖民地文化狀況:殖民從屬國相互關係的探討視野╱金艾琳
第一章:時空重塑與意識的地形學
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陳偉智
戰爭景觀(Spectacle)與戰場實感的動力學:中日戰爭時期帝國對大陸的統治與生命政治或者對朝鮮和朝鮮人的配置╱金艾琳
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力戰」前臺北與哈爾濱的比較╱柳書琴
第二章:他者經驗與自我建構的力學
搖墜的帝國,後殖民的文化政治學:皇民化的技術及其悖論╱車承棋
戰前臺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中心╱王惠珍
「我們─我─存在In-dem-Wir-sein」哲學轉向:朴鐘鴻與海德格╱金杭
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改造╱石婉舜
第三章:差異、欲望或龜裂的政治學
戰爭和情節劇:日本殖民統治末年宣傳電影中的朝鮮女性╱白文任
被遺忘的「抗戰」電影導演何非光:一位殖民地時期臺灣出身者想像中的『我們』
╱三澤真美惠
戰時體制期的欲望政治╱蘇榮炫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我耳目一新,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一些固有认知的著作。在阅读之前,我脑海中关于“总力战”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宏大叙事、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战争对经济、军事的直接影响。然而,《戰爭與分界: 「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这本书,却带领我深入到了一个更为细腻,也更为触及灵魂的层面。作者并未简单罗列历史事件,而是巧妙地将“总力战”这个概念,置于台湾和韩国这两个不同但又有着复杂联系的东亚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我尤其被书中对于“主体的重塑”这一议题的探讨所吸引。战争,尤其是近代以来那种吞噬一切的“总力战”,不仅仅是对物质资源的掠夺,更是对人心、对身份认同、对民族精神的改造。书里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爬梳,呈现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国家动员下,个体如何在集体洪流中寻找或被塑造出新的“主体性”。这让我开始反思,在极端环境下,所谓的“个人”与“集体”、“民族”之间的界限究竟是如何被模糊、被重新划定,甚至是被意识形态所操控的。同时,书中对于“文化政治”的关注,更是将这种主体重塑的过程,与艺术、文学、教育、媒体等多个文化维度紧密相连。我开始意识到,文化从来不是战争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迷雾中拨开层层云雾,看到了在历史的巨变之下,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是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走向新的存在形态的。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让我对“人”和“历史”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犹如一道锐利的解剖刀,精准地剖析了“总力战”这一沉重历史时期对两个东亚社会——台湾和韩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它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的宏观分析,更将目光投向了微观层面,探讨了战争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这两个地域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我被书中那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翔实的史料运用所折服。作者并非空泛地谈论概念,而是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和二手研究,细致地展现了在“总力战”的巨大压力下,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个人情感是如何被扭曲、被重塑的。书中对“主体”的定义和分析尤为精彩,它揭示了在国家意志的强势干预下,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空间如何被压缩,而新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又如何被灌输和强化。这种重塑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全然被动接受,书中对其中复杂的互动和微妙的心理变化都有深入的描绘。更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将“文化政治”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将战争时期的文化生产、意识形态传播、艺术创作等,置于政治动员和国家叙事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让我看到了文化如何被用作动员民众、巩固政权、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将书中的论述与我对这两个地区现代历史的零散认知进行比对,发现书中提出的观点既有颠覆性,又有深刻的洞察力。这绝对是一部能够引发深刻思考,并对理解东亚现代史提供全新视角的学术力作。
评分终于读完了《戰爭與分界: 「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这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直以为“总力战”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但是,这本书以一种极其深刻和独到的视角,将“总力战”的概念,延伸到了对社会主体和文化政治的颠覆性重塑。书中对台湾和韩国这两个东亚社会在“总力战”时期的历史考察,让我看到了战争的触角是如何深入到最细微的社会细胞和个体精神世界的。我被作者对于“主体重塑”的论述深深吸引,书中揭示了在巨大的国家压力下,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如何被模糊、被重构,从而形成一种服务于战争的集体主义“主体”。这种重塑的过程,并非简单粗暴,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密的文化和政治操作来实现的。而“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引入,更是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艺术、文学、教育、媒体等文化领域会如此敏感,又为何会成为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国民动员的重要阵地。书中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文化产品是如何被审查、被扭曲,以服务于战争的宣传和动员。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智识上的洗礼,它迫使我重新审视历史,理解战争对人类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的损耗,更是精神的改造和文化的变迁。
评分在翻开《戰爭與分界: 「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之前,我对“总力战”的理解,更多地局限于其军事和经济层面的含义,认为它主要是国家机器为了战争动员而进行的资源整合和人口调配。然而,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固有的认知框架,它将“总力战”的视野,拓展到了对个体精神世界和文化认同的深刻改造。作者通过对台湾和韩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致考察,有力地论证了“总力战”不仅仅是一场物质上的较量,更是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主体重塑”工程。我尤其被书中对于“分界”这一概念的解读所打动。在“总力战”的大背景下,国界、族界、阶级界,甚至是个体内部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又在新的意识形态下被重新划定。这种“分界”的重塑,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份认同,使得原本多元、流动的主体,在国家意志的强力驱动下,变得更加趋同和单一。而“文化政治”的引入,更是让这种主体重塑的过程具体而生动。书中细致地分析了在战争时期,文学、艺术、教育、媒体等文化领域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战争动员,如何塑造民众的意识形态,如何构建和传播新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复杂互动的深刻洞察,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肌理是如何在字里行间被揭示出来的。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充满了挑战性,因为它迫使我去重新审视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并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和解读。
评分这本书绝对是一次智识上的冒险,它带领我深入到一个我之前从未真正触及过的历史深水区。我一直认为,“总力战”主要指的是国家将人力、物力、财力等一切资源都投入到战争中的极端状态,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和军事概念。然而,《戰爭與分界》这本书,却将“总力战”的核心,精准地聚焦在“主体重塑”和“文化政治”这两个极其关键的维度上,而且是以台湾和韩国这两个鲜活的案例来展开。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我尤其惊叹于作者如何能够将如此宏大的历史命题,分解成如此细腻的、关于个体命运和文化变迁的微观叙事。书中对“主体”的定义和讨论,颠覆了我过去对于“国民身份”的简单理解。在“总力战”的熔炉里,个体不再是独立的原子,而是被国家机器精心打磨、重塑的零件。这种重塑,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洗脑,更是情感上、认知上的深刻改造,从而构建起一种服务于战争的“新主体”。而“文化政治”的视角,更是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立体和具象。我看到了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审查和改写的,教育内容是如何被修改以灌输爱国主义的,媒体又是如何被用来妖魔化敌人、鼓舞士气的。这些细节的描绘,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总力战”的时代,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艺术表达,而是政治动员最强大的武器之一。这本书的阅读,不是轻松的消遣,而是一次对历史真相的深入挖掘和对人类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onlinetoolsland.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本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