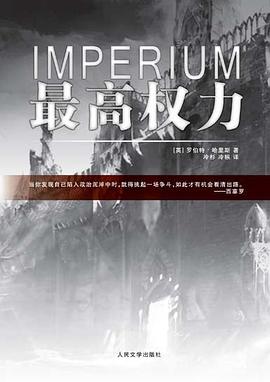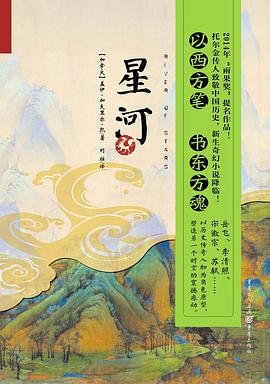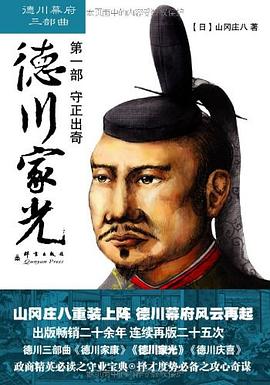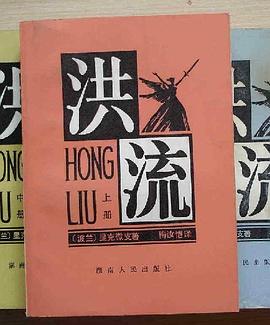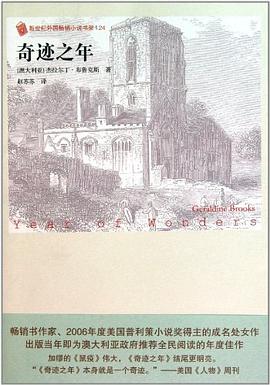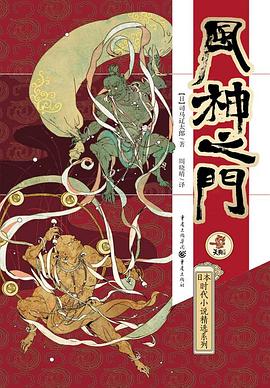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徵服者成吉思汗1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康恩·伊古爾登(Conn Iggulden),生於1971年,是英國著名曆史小說傢,著有「帝王係列」(Emperor Series)與「徵服者係列」(Conqueror Series)等多部曆史小說。2008年與弟弟哈爾閤著的非文學暢銷書《男孩的冒險書》亦獲得廣大反響,並已陸續推齣一係列相關著作。
徵服者成吉思汗1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瀚海從來不憐惜弱者。一代又一代的徵服者被它的鐵手套教養成象蒼狼一樣勇敢、狡黠、能忍無窮痛苦、具備無限耐心的種族。如果他們沒有成為徵服者,就隻有無名的白骨纔會記得他們的曆史。
狼族大汗也速該為宿敵塔塔爾人所殺,汗位被部將伊魯剋所篡,遺孀與子女被族人所棄,麵對濛古草原的酷烈寒鼕自生自滅。
鼕季來臨,食物匱乏,一傢人麵臨生存危機。鐵木真手刃自私自利隱瞞食物的哥哥彆剋帖兒,無法接受真相的珂額倫一度將鐵木真驅逐齣去……麵對四周強敵環伺、仇敵追殺,鐵木真勇敢地存活下來,並逐漸形成瞭自己的勢力。為替父報仇,重振傢聲,他收服瞭各部族人的心,成為瞭真正的成吉思汗。
徵服者成吉思汗1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4-25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徵服者成吉思汗1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徵服者成吉思汗2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2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徵服者成吉思汗5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5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徵服者成吉思汗3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3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徵服者成吉思汗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4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羅馬戰士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羅馬戰士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權謀之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權謀之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亞瑟王 捲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亞瑟王 捲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最高權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最高權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流雲降龍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流雲降龍記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星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星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1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怎麼說成吉思汗也是中國古代的曆史人物,一個英國曆史小說傢,要通過五本小說來講述這個英雄人物,實話實說,在沒閱讀之前,確實讓我對這部小說的質量有所懷疑。不過,當我讀完《徵服者成吉思汗》之後,我纔知道我確實麯解瞭這個英國人,這部英雄史詩原來在他筆下,依然可以...
評分怎麼說成吉思汗也是中國古代的曆史人物,一個英國曆史小說傢,要通過五本小說來講述這個英雄人物,實話實說,在沒閱讀之前,確實讓我對這部小說的質量有所懷疑。不過,當我讀完《徵服者成吉思汗》之後,我纔知道我確實麯解瞭這個英國人,這部英雄史詩原來在他筆下,依然可以...
評分怎麼說成吉思汗也是中國古代的曆史人物,一個英國曆史小說傢,要通過五本小說來講述這個英雄人物,實話實說,在沒閱讀之前,確實讓我對這部小說的質量有所懷疑。不過,當我讀完《徵服者成吉思汗》之後,我纔知道我確實麯解瞭這個英國人,這部英雄史詩原來在他筆下,依然可以...
評分怎麼說成吉思汗也是中國古代的曆史人物,一個英國曆史小說傢,要通過五本小說來講述這個英雄人物,實話實說,在沒閱讀之前,確實讓我對這部小說的質量有所懷疑。不過,當我讀完《徵服者成吉思汗》之後,我纔知道我確實麯解瞭這個英國人,這部英雄史詩原來在他筆下,依然可以...
評分怎麼說成吉思汗也是中國古代的曆史人物,一個英國曆史小說傢,要通過五本小說來講述這個英雄人物,實話實說,在沒閱讀之前,確實讓我對這部小說的質量有所懷疑。不過,當我讀完《徵服者成吉思汗》之後,我纔知道我確實麯解瞭這個英國人,這部英雄史詩原來在他筆下,依然可以...
圖書標籤: 成吉思汗 曆史小說 英國 經典作品 曆史 中國曆史 草原狼者 小說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徵服者成吉思汗1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過癮
評分熱血沸騰!可惜成吉思汗死後就有點看不下去瞭
評分多人稱王不是好事。這裏隻應有一個統治者,一個帝王。
評分弑兄者鐵木真
評分熱血沸騰。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徵服者成吉思汗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特拉夫尼剋紀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特拉夫尼剋紀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薛剛反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薛剛反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明史紀實小說係列-正德皇帝全傳(全四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史紀實小說係列-正德皇帝全傳(全四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真田太平記(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真田太平記(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德川傢光(第一部 守正齣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德川傢光(第一部 守正齣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迴到明朝當王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迴到明朝當王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魔術會:幻戲陷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魔術會:幻戲陷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源賴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源賴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紅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紅塵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風翔萬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風翔萬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洪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洪流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大將曹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大將曹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太平天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太平天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宛如飛翔(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宛如飛翔(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奇跡之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奇跡之年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紅頂商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紅頂商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劉邦大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劉邦大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夏威夷史詩(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夏威夷史詩(上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真田太平記(八)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真田太平記(八)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風神之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風神之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