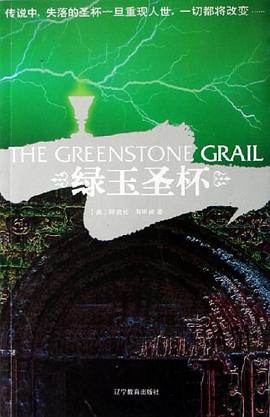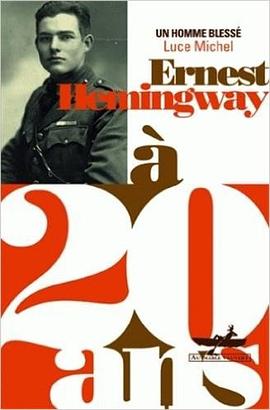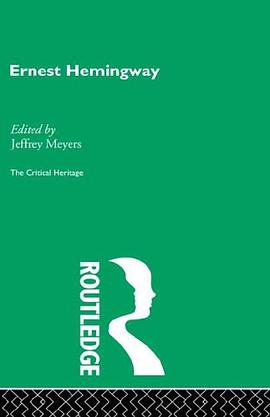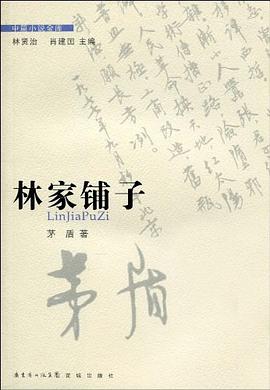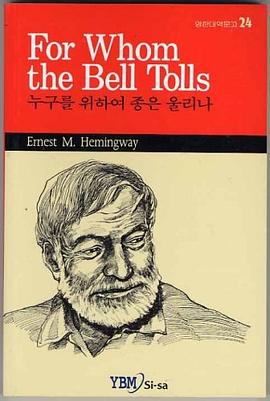《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乞力馬紮羅的雪》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歐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國作傢、記者,“迷惘的一代”作傢中的代錶人物,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傢之一。他以文壇硬漢著稱,作品中蘊含勇敢、直率、堅定的獨立精神,代錶美利堅民族精神,在美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海明威一生獲奬頗多,其中包括以《老人與海》先後獲得普利策奬和諾貝爾文學奬。2001年,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與《永彆瞭,武器》被美國現代圖書館列入“20世紀100部最佳英文小說”中。
《乞力馬紮羅的雪》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普利策奬、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海明威短篇小說精選。
★人可以被毀滅,卻不可以被戰勝。
★名傢譯本,精裝修訂版。
★課外讀物首選,一生必讀的經典名作。
-------------------------------------------------------------------------------------------------------------
◆《乞力馬紮羅的雪》裏寫的都是真事,其中的素材足夠完成四部長篇小說。海明威的作品強大的情感力量和高度個性化的風格糅為一體,為他贏得全球聲譽和影響力。你可以模仿他的風格,但你學不像。
——《紐約時報》
◆舉世無雙——字一句都滲透齣這個國傢清澈明亮的光輝。
--《每日電訊報》
◆ 深深烙印著海明威式的緊促感--冷血的描寫背後,卻湧動著藏不住的柔情。
--《衛報》
-------------------------------------------------------------------------------------------------------------
諾貝爾、普利策雙料得主海明威短篇小說精選集。
收錄《乞力馬紮羅的雪》《白象似的群山》《印第安人營地》《殺 手》《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在密執安北部》《雨裏的貓》《在異鄉》8篇海明威經典中篇和短篇小說。《乞力馬紮羅的雪》是他的著名中篇小說之一,蘊含著一種獨特的人性力量。這篇小說發錶於1936年,一問世便得到瞭來自各方麵的好評。其錶現齣作者客觀對待死亡的態度以及對死亡由恐懼到平靜的心理曆程,因而也充分體現齣海明威賴以成名的“壓力下的風度”。本書收錄的文章極好地詮釋瞭海明威極簡文風、冰山理論,極具代錶性。
《乞力馬紮羅的雪》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2-26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乞力馬紮羅的雪》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乞力馬紮羅的雪》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圖書標籤: 美國 海明威 短篇 文學 小說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乞力馬紮羅的雪》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啊,真喜歡海明威,喜歡這些偉大的作傢對人性幽深、細微情緒的理解和共情。《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裏虛無於人的重要性,有些夜晚,它和燈光便是所需要的一切; 《在密執安北部》裏女孩莉茲小心翼翼又抑製不住的喜歡一個人的心情; 我也屬於在小酒館裏待到很晚的那一類人。
評分我問你是否尊崇本心?沒有在舒適安逸物欲橫流的生活中忘記書寫賦予我們的使命
評分都是看過的文章,但依然能夠靜下心來重新讀一遍。翻譯的好壞不談,但是他的文章,真的需要看原文。目前我唯一看到過的令我滿意的相關譯本,竟然是一個不知名的大學教授翻譯的。
評分喜歡這樣簡明利落、刀子一樣鋒利的小說,讀完覺得,囉嗦是一種罪過。
評分我問你是否尊崇本心?沒有在舒適安逸物欲橫流的生活中忘記書寫賦予我們的使命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乞力馬紮羅的雪》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綠玉聖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綠玉聖杯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and Other Storie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and Other Storie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Ernest Hemingway à 20 an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Ernest Hemingway à 20 an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入土不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入土不安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Volume 3, 1926–1929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Volume 3, 1926–1929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A Farewell to Arm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 Farewell to Arm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Ernest Hemingway (Critical Heritag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Ernest Hemingway (Critical Heritag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你一年的8760小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你一年的8760小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林傢鋪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林傢鋪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從男人到男子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從男人到男子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Angels in America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Angels in America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Hemingway in Lov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Hemingway in Love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現代語境下海明威的生態觀和性屬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語境下海明威的生態觀和性屬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老人與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老人與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物語日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物語日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老人與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老人與海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危險的友誼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危險的友誼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河的第三條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河的第三條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