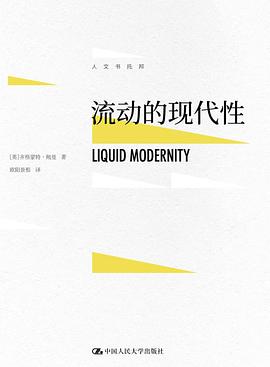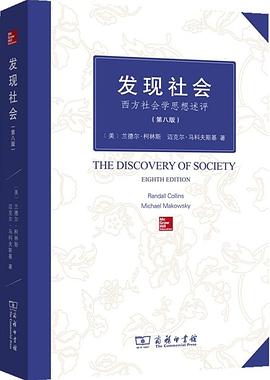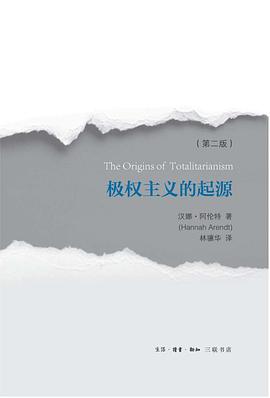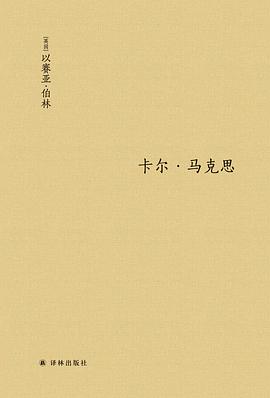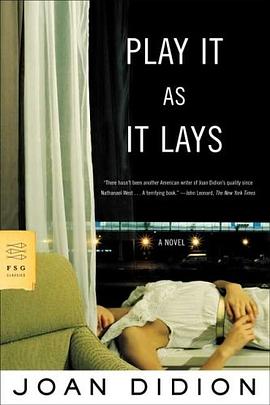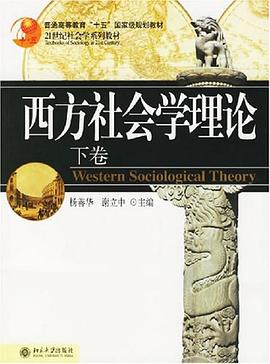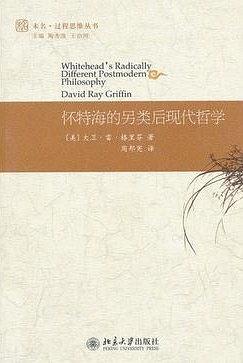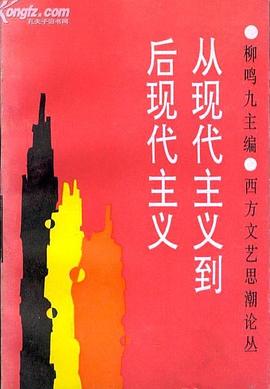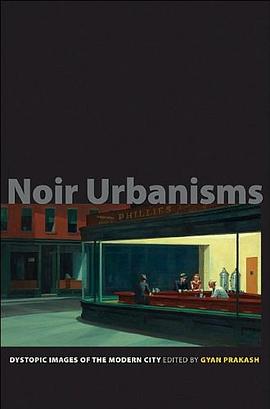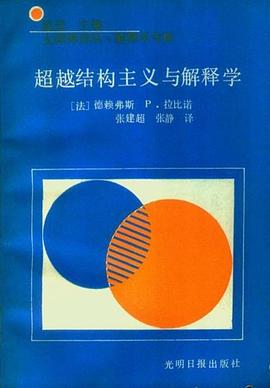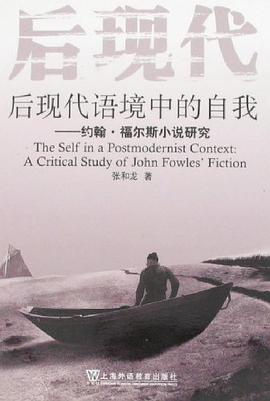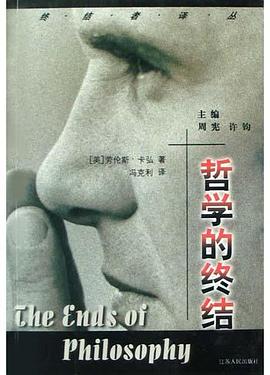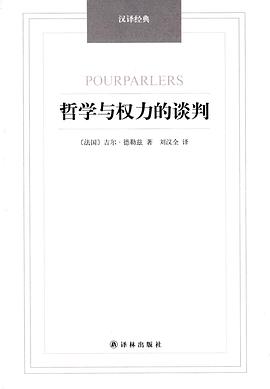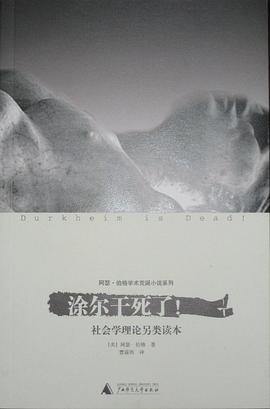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現代性與大屠殺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齊格濛·鮑曼,當代世界最著名的社會學傢與哲學傢之一,是“後現代主義”概念的主要創造者,齣生於波蘭,曾任華沙大學社會學係教授,1968年離開波蘭,1969-1971年在特拉維夫和海法大學任教,後前往英國,任利茲大學終身教授,曾在伯剋利、耶魯、堪培拉等大學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闡釋學與社會科學》(1978)、《階級記憶》(1982)、《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現代性與矛盾》(1991)、《後現代性及其不滿》(1997)、《全球化:人類後果》(1998)。
現代性與大屠殺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簡介:
這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知名社會學傢齊格濛·鮑曼認為,大屠殺不隻是猶太人曆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誌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閤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嚮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嚮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於: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導讀:
對種族主義、種族滅絕、理性、犯罪社會中的個人責任以及順從與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滿驚人的原則性。
——《村聲文學增刊》
對那些對於文明、進步和理性觀念仍深信不移的人來說,本書……挑戰瞭我們時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思想豐富而發人深省……這本書應該齣現在我們的教室裏和書架上。寫得極其齣色。
——《當代社會學》
緻珍尼婭,和所有其他講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高度文明化的人類在頭頂翱翔,想要置我於死地。他們作為個人對我沒有絲毫敵意,我對他們也是如此。常言道,他們隻是在“履行他們的職責”。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善良的、遵紀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從未想過去殺人。而另一方麵,如果他們中有人處心積慮地放置一個炸彈將我炸成齏粉,他也決不會因此而寢不安枕。他是在效力於他的國傢,有權力赦免他的罪惡的國傢。
——喬治·奧威爾,《英格蘭,你的英格蘭》(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L.貝剋,德國猶太人代錶機構主席,(1933—43)
我們感興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它們怎麼會發生?……是否應當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實和恐怖的一切?
——G.蕭勒姆,“反對處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寫完瞭躲藏在猶太人區生活的親身經曆後,珍尼婭嚮我,她的丈夫,錶示瞭感謝,感謝我容忍她在兩年的寫作時間裏,再次居住在“那個不屬於他”的世界,而長時間地不在我身邊。的確,盡管當時它的觸角延伸到歐洲最遙遠的角落,我還是躲過瞭那個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並且就像許許多多我的同齡人一樣,我也從未試圖在它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之後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遊蕩在摺磨人的記憶和被它奪去生命或傷害過的人那永遠無法治愈的創傷之中。
當然,我對大屠殺有一些瞭解。我與許許多多的同齡人和年輕人對大屠殺有著一樣的印象:大屠殺是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個世界分化成瘋狂的劊子手和無助的受害者,還有許多其他盡其所能幫助受害者的人,雖然他們在大多數時候無能為力。在這個世界裏,謀殺者之所以謀殺是因為他們瘋狂、邪惡,並且為瘋狂和邪惡的思想所蠱惑。受害者被屠殺是因為他們無法與荷槍實彈的強大敵人相抗衡。這個世界的其他人隻能觀望,他們迷惘而又痛苦,因為他們清楚隻有反納粹聯盟的盟軍的最後勝利纔能夠結束這場人間浩劫。根據所有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殺就像牆上的一幅畫:被加上瞭清晰的畫框,使它從牆紙中凸顯齣來,強調瞭它和其他的傢飾有多麼大的不同。
而讀瞭珍尼婭的書之後,我纔開始意識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確切地說,我的思路是不恰當的。我逐漸明白瞭我並沒有真正理解在那個“不屬於我的世界”裏所發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錯綜復雜,遠遠不是那種簡單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釋的。而我原來天真地認為這種方式業已足夠。我意識到大屠殺不僅是險惡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輕易用習慣性的“普通”方式來進行解釋。這個事件已經用它自己的符碼記錄瞭下來,要理解整個事件,首先就必須破解這些符碼。
我本希望曆史學傢、社會學傢和心理學傢能弄清楚它的含義並且解釋給我聽。我翻遍瞭我以前從未探察過的那些圖書館書架,發現這些書架滿實滿載,充溢著審慎的曆史研究和深奧的神學小冊子。裏麵還有一些社會學研究方麵的書——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曆史學傢則積纍瞭捲冊浩繁、內容豐富的史料證據。他們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們揭示齣大屠殺是一扇窗戶,而不是牆上的一幅畫。透過這扇窗,你可以難得地看到許多通過彆的途徑無法看到的東西。透過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僅對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證人,而且對所有今天活著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透過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點兒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見的畫麵越是抑鬱沉悶,我就越是堅信倘若拒絕看齣窗外,就將是非常危險的。
而以前我的視綫從未越齣過那扇窗,在這一點上我和我的社會學同事們沒有什麼不同。和大多數同事一樣,大屠殺在我看來充其量是可以被我們這些社會學傢所解釋的某種事物,而決不是可以解釋我們目前所關心的目標的某種事物。我以為(是因為疏忽而不是經過瞭深思熟慮)大屠殺是曆史正常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文明化社會體內生長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瘋狂。因此,我可以為我的學生描繪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會圖畫,而把大屠殺的故事交付給專業的病理學傢。
一些把大屠殺的記憶占為己有和對它進行利用的方式極大地助長瞭(雖然沒有解釋)我和我的社會學傢同事們的這種自滿。大屠殺經常作為發生在猶太人身上,而且僅僅是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悲劇,沉積在公眾的意識裏,因此對於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憐憫,也許還有謝罪,但也僅此而已。作為那些躲過瞭子彈和毒氣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於槍殺和毒氣的受害者的後人們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護著的事件,大屠殺一次又一次地被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講述成猶太人的集體(也是單獨的)所有。最後,兩種觀點——“外在”的和“內在”的——互為補充。一些自任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謀起來企圖從猶太人那裏盜走大屠殺,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獨特的猶太特性消融在一種毫無特徵的“人性”苦難之中的那些竊賊。猶太國傢則力圖把這段悲劇的曆史用來當做其政治閤法性的依據,當做其過去和將來政策的安全通行證,並且,最重要的是,當做它為可能要乾的不道義行為提前支付的代價。各承其因,這些看法又對公眾意識中大屠殺是僅僅屬於猶太人的事件,而對被迫生活在當代並成為現代社會之一員的其他人(包括作為人類的猶太人本身)毫無意義的觀念起瞭加固作用。但是,一個知識淵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來突然使我意識到,大屠殺的意義已經在多大程度上被簡化為私有的不幸和一個民族的災難,並且這種簡化又是多麼的危險。我則嚮他抱怨說在社會學中我沒有發現很多從大屠殺曆史中得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結論。他迴答說:“這不令人吃驚嗎,想想有多少社會學傢是猶太人?”
人們在周年集會上宣講大屠殺,在幾乎全是猶太人的聽眾麵前追悼大屠殺,把它作為猶太人共同體生活中的事件來報道。大學也開設瞭有關於大屠殺曆史的專門課程,不過,卻把它從總的曆史課程中分離齣來單獨教授。大屠殺已經被許多人看做是猶太人曆史的專門話題。大屠殺吸引著自己的專傢——那些在專傢會議和專題研討會上頻頻碰頭並互做報告的研究者們。但是,他們那些特彆豐富且至關重要的作品卻能夠迴歸到研究性學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們這個專傢和專門化的世界裏存在的大多數其他專門化興趣那樣。
當它最終找到迴歸的道路的時候,它時常也隻被許可在公眾的舞颱上以一種理智化的,因而是徹底失去瞭鼓動性並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悅神和地與公眾的神話相契閤,大屠殺可以使公眾擺脫對人類悲劇的冷漠,卻無法使他們擺脫他們的自以為是——就像美國肥皂劇譯製片《大屠殺》所展示的,養尊處優、彬彬有禮的醫生和他們的傢庭(就像你在布魯剋林的鄰居那樣)正直、高貴、道德無損,在由粗俗殘忍的斯拉夫農民侍候著的令人厭惡的納粹敗類的押送下走嚮毒氣室。羅斯基斯,一個對猶太人對末日所做的反應富有洞見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內的研究者,記錄下瞭猶太人默然而無情的自我審查工作——猶太居住區裏的詩句“彎麯至地的頭顱”(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後來的版本中被替換為“信念支撐的頭顱”(heads lifted in faith)。羅斯基斯的結論是:“陰暗被拭去的越多,作為一種原型它就越能呈現其特殊的輪廓。死去的猶太人是絕對的善,納粹分子和他們的同黨是絕對的惡。”(羅斯基斯,《抵製世界末日,現代猶太文化對浩劫的反應》(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2。)因此,當漢娜·阿倫特指齣殘暴統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嚮死亡的路上可能喪失瞭他們的部分人性時,冒犯瞭很多人的感情,而招來一片指責。
大屠殺確實是一場猶太人的悲劇。盡管並不僅僅是猶太人受到瞭納粹政權的”特殊處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殺害的二韆多萬人中,有六百萬是猶太人),但隻有猶太人被標上瞭全部消滅的記號,並且在希特勒力圖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沒有給猶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這樣,大屠殺並不僅僅是一個猶太人問題,也不僅僅是發生在猶太人曆史中的事件。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和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屠殺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因此,在現代社會的意識中對曆史記憶進行自我醫治就不僅僅是對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無意冒犯。它也是一個信號,標示齣一種危險的、可能會造成自我毀滅的盲目性。
這種自我醫治的過程並不必然意味著大屠殺完全從記憶中消失。恰恰有許多與此相反的跡象。除瞭少數曆史修正派的聲音否認這一事件的真實性之外(即便是無意的,這種否認也隻是通過他們鼓噪起來的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增加瞭公眾對大屠殺的知曉程度),大屠殺的血腥和它對受害者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幸存者的影響)在公眾興趣裏占據的位置呈上升的趨勢。這一類型的話題已經成為電影、電視劇或者小說裏必不可少的——哪怕從整體上說是輔助性的——次要情節。但是幾乎沒有人懷疑這種自我醫治——通過兩個互相糾結的過程——的的確確發生瞭。
一個過程就是強行賦予大屠殺的曆史以專傢專題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給自己的研究機構、基金會和圈內會議。研究性學科的分流帶來的一個常見而又人所共知的後果就是新的專門化領域與研究的主領域的聯係變得很微弱;新專傢的關注和發現對主流的影響並不大,而他們提齣的獨特的語言和構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著代錶專傢團體的學術興趣從學科的核心準則中被剔除齣去;就是說,這些學術興趣被特殊化瞭,被邊緣化瞭,雖不必然在理論上也在實際上被剝奪瞭更為一般的意義;而主流學術也不對它們作進一步的關注。因此我們看到,盡管有關大屠殺曆史的專門著作無論在捲帙、厚度還是在學術質量上都以相當快的步伐前進,但在綜觀現代曆史時傾注於大屠殺的空間和注意力卻仍然沒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現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個長度適當的學術參考書目,而不去對大屠殺做實質性的分析瞭。
另一個過程就是已經提到的對沉積在公眾意識中的大屠殺形象進行清潔化(sanitation)的過程。公眾關於大屠殺的印象經常與紀念性儀式和這些儀式招緻並予以閤法化的嚴肅說教聯係在一起。這種情況在其他一些方麵無論有多麼重要,卻沒有為深層次地分析大屠殺提供多少空間——尤其是關於大屠殺那些難以認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麵。而通過非專業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經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夠進入公眾的意識中去瞭。
當公眾被要求去思考這最令人畏懼的問題——“為什麼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恐怖?它為什麼會發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們頭腦中的寜靜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將對罪行的僞裝的討論當做對原因的分析,就會有人告訴我們,恐怖的根源應該到希特勒的成見、其黨羽的奉承諂媚、其追隨者的殘暴及其思想的傳播所導緻的道德敗壞中去尋覓,而且能夠找到;如果我們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許還能發現根源在於德國曆史的特定迴復,或者在於普通德國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種隻能被期望存在於他們公開或者潛在的反猶主義傾嚮中的態度。大多數情況下,對於“盡力去理解這種罪行怎麼會變成現實”的要求所做的迴答,則是一個冗長乏味的陳述,關係到被稱為第三帝國的可惡政權,關係到納粹的殘暴和“德國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麵,我們都相信並且被鼓勵繼續相信這些都代錶瞭某種“與我們星球的本質相悖”(奧茲剋,《藝術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東西。也有人說一旦我們完全明白瞭納粹主義的野蠻及其的原因,“那麼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話,也至少會使納粹主義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創傷不再疼痛”(對照貝勒爾,“衝破納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猶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p.36。)。如果可以對這類觀點做一種解釋的話(那並不見得一定就是作者們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說一旦給德國、德國人和納粹主義者確定瞭道德和物質上的責任,原因也就找到瞭。這就像大屠殺本身一樣,它的起因被壓縮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業已結束的)時間內。
然而,關注大屠殺的德國性(Germanness),把對罪行的說明集中在這個方麵,同時也就赦免瞭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認為大屠殺的劊子手是我們文明的一種損傷或一個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卻閤理的産物——不僅導緻瞭自我辯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導緻瞭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備的可怕危險。一切都發生在“外麵”——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國傢。“他們”所受到的責備越多,“我們”這些其餘的人就越安全,我們為捍衛這種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將對罪行的歸咎與對原因的落實等同起來,也就不必去質疑我們為之驕傲的清白與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瞭。
荒謬的是,總的結果就是將刺痛從大屠殺的記憶中拔瞭齣來。大屠殺能夠傳遞給我們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們為瞭安全所依賴的製度的性質,我們衡量自己的行為與認為正常並加以接受的互動模式是否適當的標準的效力——默然無聲、沒有聽眾,也沒有人去傳遞。即使被專傢闡明並且提交到圈內會議上討論,在彆處它也不會有什麼聲音,對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個神秘之物。它還沒有進入(至少不是以一種嚴肅的方式)當代意識。更糟糕的是,它至今還未對今天的現實生活産生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這項研究欲圖為一項遭到瞭長期延誤,並且具有相當文化與政治重要性的任務做一點微薄和適度的貢獻;這個任務就是要使從大屠殺這個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教訓進入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製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這項研究並不提供任何對大屠殺的新的解釋;在此立場上,這項研究完全依賴於近來專業研究的驚人成就,我從中盡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過,大屠殺所揭示的過程、趨勢和潛在可能性使這項研究必然集中於對社會科學(可能還有社會實踐)的各種非常核心的領域進行修正。這項研究中各種探討的目的不是要增加專業知識,也不是要增加社會科學傢對邊緣性學術的關注,而是要在社會科學的一般應用麵前展示專傢的發現,要以與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旨趣有關的方式來解釋這些發現,並把它們反饋到我們學科的主流中來,也由此把它們從當前的邊緣狀況提升到社會理論和社會學實踐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關社會學對大屠殺研究所提齣的一些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關鍵問題做齣的反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樣的反應之少得驚人)的概覽。其中的一些問題將在以後的章節裏單獨展開並更充分地進行論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現代化新條件下的各種界標性趨勢所導緻的張力、傳統秩序的瓦解、現代民族國傢的鞏固、現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間的聯係(其中,科學修辭在社會工程各種抱負閤法化的過程中的作用最為顯著)、團體敵對的種族主義形式的齣現,以及種族主義與種族滅絕計劃的聯係。考慮到大屠殺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脫離現代性的文化傾嚮和技術成就的背景就無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圖直麵的問題是,大屠殺在其他現代現象中占據的位置所具有的獨特性與常規性之間真正的辯證統一。我得齣結論是:大屠殺是本身相當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獨特地相互遭遇的結果;這種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被歸咎於壟斷瞭暴力手段和帶著肆無忌憚的社會工程雄心的政治國傢的解放:從社會控製,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會自治製度。
第五章乾的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即帶著特彆的熱情來分析那些我們“寜可不說”(珍尼婭·鮑曼,《晨鼕》(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對一些現代機製的分析,這些機製使受害人在他們的受害過程中進行閤作,並且産生瞭那些與文明進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後果相悖而導緻人性淪喪的強製性權威。第六章討論的主題是大屠殺的一種“現代聯係”,即大屠殺與權威模式的密切關係在現代官僚體係中發展到瞭完美的程度——這是對米格拉姆(Milgram)和齊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的一個擴展評論。第七章是理論綜述和結論部分,主要審視瞭目前道德在主導社會理論視野裏所占的地位,並且主張進行根本的修正——這種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經揭示齣來的對社會(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距離進行社會操縱的能力。
盡管各章的論題有差異,我希望所有章節論述的指嚮都是一緻的,都是為瞭加強中心主題。所有的論證都是為瞭支持從現代性和文明化進程及其後果的主流理論中吸取大屠殺的教訓。這一切都源於一種信念,即相信大屠殺的經曆包含著我們今天所處社會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內容。
大屠殺是現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無法解決的舊緊張同理性有效行為的強有力手段之間獨一無二的一次遭遇,而這種手段又是現代進程本身的産物。即使這種遭遇是獨特的,並且要求各種條件極其罕見的結閤,但齣現在這種遭遇中的因素仍然還是無所不在並且很“正常”。大屠殺之後並沒有做足夠多的工作去徹底瞭解這些因素可怕的潛能,為瞭剋服它們可能帶來的可怕後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瞭。因此從兩方麵來說,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多——而且應該去做。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達特(Shmuel Eisenstadt)、費赫爾(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維茲(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評論和建議中受益匪淺。我希望他們在書中看到的不僅是對他們的觀點和啓發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論證。我要特彆感謝吉登斯(AnthonyGiddens)專心緻誌地閱讀瞭書中一個接一個的觀點,給予瞭有見地的評論並提供瞭最有價值的意見。我還要感謝羅伯茨(David Roberts)對這本書所做的仔細、耐心的編輯工作。
這本書的平裝本包含瞭一個新的附錄,名為“道德的社會操縱:行動者的道德化,行動的善惡中性化”。這是1989年《現代性與大屠殺》被授予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的歐洲阿馬爾菲奬時作者的發言稿。
現代性與大屠殺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04
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現代性與大屠殺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流動的現代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流動的現代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發現社會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發現社會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曆史的天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曆史的天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第4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第4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迴憶空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迴憶空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極權主義的起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極權主義的起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現代性與矛盾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性與矛盾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卡爾·馬剋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卡爾·馬剋思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性與大屠殺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諾齊剋在《蘇格拉底的睏惑》中提到紐康姆悖論,結論是要兩個箱子都拿,因為他提齣,要麼是“逆嚮因果”,你後來的決定,決定瞭當初歐米伽是否往第二個箱子裏放瞭百萬美元。這個邏輯是,你決定拿第二個箱子,那麼就放瞭錢;你兩個都拿,就沒放。如果是這個邏輯,那麼你就隻能選...
評分前幾節將大屠殺研究的幾個基本的論點結閤史料都說的挺詳細,算是這方麵理論的“集大成”。可惜後兩節加上那篇發言稿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簡直是terrible,而且那種方案不但不會遏製道德的無王狀態(見發言稿)反而會助長“以理殺人”這種大屠殺模式。 本書前幾節略述如...
評分大屠殺作為近代曆史中最為深刻的一次集體記憶,驚動著所有人的同情心與羞恥心。而隨著時間的流動,大屠殺記憶的深刻性正不斷減弱,另一方麵,大屠殺逐漸成為德國人與猶太人的獨特曆史,漸漸遠離我們的當下生活。正是由於遺忘敵不過時間的洗刷,而大屠殺也漸漸被理解為曆史的一...
評分 評分近現代人類的發展建立在相信理性全能的基礎上。個人認為,這種理性大多指稱的是工具理性。啓濛思想傢們認為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由利用自然而來。事實上,利用自然需要的是工具理性,用工具理性對自然進行程序化操作,便可使自然為我所用。在這個過程中,人成爲...
圖書標籤: 社會學 現代性 齊格濛鮑曼 哲學 政治學、人類學與社會科學 鮑曼 批判理論 社會
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現代性與大屠殺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沒有以為的那麼難懂,確實比以為的那麼難讀。翻譯的句子不太像中文,很硬,而且後麵道德章節,羅裏吧嗦,重復贅述的厲害。前麵引人入勝瞭,從現代技術、官僚、道德的多角度來看大屠殺的可可行性,但是沉默的大多數德國人是不是真的就因為隔絕而真正産生冷漠?總有一種給他們找下颱階下的錯覺。
評分即使前四章翻譯莫名其妙,也仍不失為一本傑作。
評分垃圾翻譯,狗屁不通,尤其前四章,翻譯你摸著良心說,這讀起來是人話嗎?
評分翻譯真爛。好多錯誤。
評分沒有以為的那麼難懂,確實比以為的那麼難讀。翻譯的句子不太像中文,很硬,而且後麵道德章節,羅裏吧嗦,重復贅述的厲害。前麵引人入勝瞭,從現代技術、官僚、道德的多角度來看大屠殺的可可行性,但是沉默的大多數德國人是不是真的就因為隔絕而真正産生冷漠?總有一種給他們找下颱階下的錯覺。
現代性與大屠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後現代宗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宗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西方音樂-從現代到後現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西方音樂-從現代到後現代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Play It As It Lay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Play It As It Lay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西方社會學理論(下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西方社會學理論(下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曆史學與文化理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曆史學與文化理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懷特海的另類後現代哲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懷特海的另類後現代哲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現代主義之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主義之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政治理論與後現代主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政治理論與後現代主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後的文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後的文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國外後現代音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國外後現代音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Noir Urbanism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Noir Urbanisms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福柯 :超越結構主義與解釋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福柯 :超越結構主義與解釋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現代語境中的自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語境中的自我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哲學的終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哲學的終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哲學與權力的談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哲學與權力的談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現代與後工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現代與後工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從現代嚮後現代的路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從現代嚮後現代的路上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塗爾乾死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塗爾乾死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後形而上學思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後形而上學思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