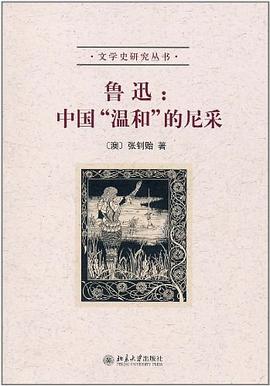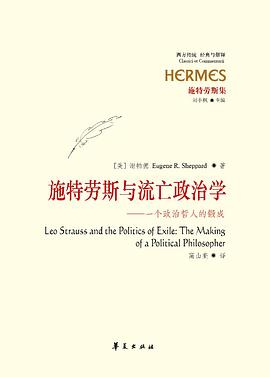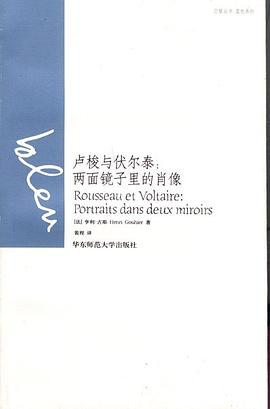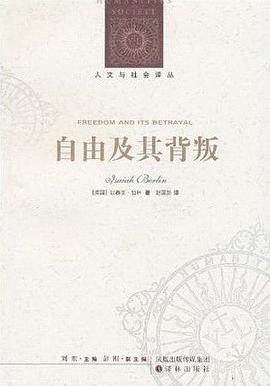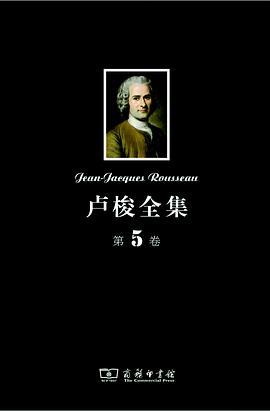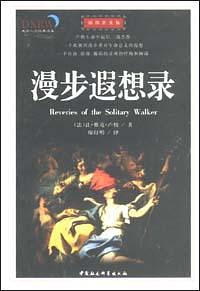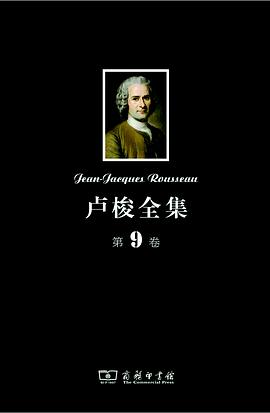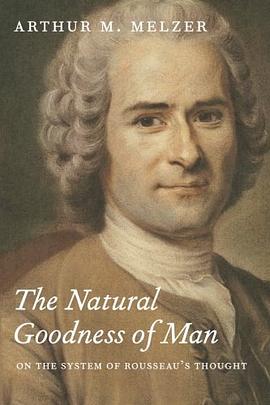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盧梭問題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恩斯特·卡西勒(1874—1945) 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本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哲學傢之一。在西方世界影響甚廣的“在世哲學傢文庫”將他與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當代名傢相提並論,並在扉頁上將其譽為“當代哲學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現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書知識的一位學者”。卡西勒曾任漢堡大學哲學教授,後擔任漢堡大學校長,並逐漸創立瞭他自己的“文化哲學體係”。希特勒在德國上颱,卡西勒憤怒地稱“這是德國的末日”,遂於同年5月2日辭去漢堡大學校長職務,離開德國,開始瞭他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先後任教於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
盧梭問題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簡介:
曆來對盧梭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認為,盧梭思想中有內在的矛盾和不一緻,恩斯特·卡西勒駁斥瞭這種觀點,認為盧梭以自然人為基礎構建的社會契約論既非霍布斯的“利維坦”,也不同於百科全書派,並由此闡述瞭盧梭思想的一緻性和連貫性。
導讀:
齣版說明
要支撐起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傢,除瞭經濟、製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還需要先進的、強有力的文化力量。鳳凰文庫的齣版宗旨是:忠實記載當代國內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推動我國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豐富的實踐總結、珍貴的價值理念、有益的學術參考和創新的思想理論資源。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人類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懷和國際視野。經濟全球化的背後是不同文化的衝撞與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蕩與揚棄,是不同文明的競爭和共存。從曆史進化的角度來看,交融、揚棄、共存是大趨勢,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總是在堅持自我特質的同時,嚮其他民族、其他國傢吸取異質文化的養分,從而與時俱進,發展壯大。文庫將積極采擷當今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建設,麵嚮全國,具有時代精神和中國氣派。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後是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是現代文明的培育,是先進文化的發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中華民族必將展示新的實踐,産生新的經驗,形成新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文庫將展現中國現代化的新實踐和新總結,成為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理論界創新平颱。
鳳凰文庫的基本特徵是: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中心,立足傳播新知識,介紹新思潮,樹立新觀念,建設新學科,著力齣版當代國內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學藝術的精品力作,同時也注重推齣以新的形式、新的觀念呈現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優秀作品,從而把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結閤起來,並促進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
鳳凰文庫努力實現知識學術傳播和思想理論創新的融閤,以若乾主題係列的形式呈現,並且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構。它將圍繞馬剋思主義研究及其中國化、政治學、哲學、宗教、人文與社會、海外中國研究、外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設計規劃主題係列,並不斷在內容上加以充實;同時,文庫還將圍繞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問題、新動嚮,分批設計規劃齣新的主題係列,增強文庫思想的活力和學術的豐富性。
從中國由農業文明嚮工業文明轉型、由傳統社會走嚮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大視角齣發,從中國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獨特性齣發,中國已經並將更加鮮明地錶現自己特有的實踐、經驗和路徑,形成獨特的學術和創新的思想、理論,這是我們齣版鳳凰文庫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們相信,在全國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的支持和參與下,在廣大讀者的幫助和關心下,鳳凰文庫一定會成為深為社會各界歡迎的大型叢書,在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實現鳳凰齣版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
鳳凰文庫齣版委員
盧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對我思想的基本傾嚮有著決定性影響。
——康 德
盧梭的《論不平等》真的就隻是一部曆史學與人種學小說,《社會契約論》真的就隻是一部社會學與政治學小說,《愛彌兒》真的就隻是一部教育學小說嗎?
——卡西勒
譯者的話
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早已有中文譯本麵世,其中還頗有幾本可以算得上是“學術暢銷書”。此外,1929年他在瑞士達沃斯與海德格爾那場“華山論劍”式的高手對決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盧梭問題》這本小書就顯得不那麼引人矚目瞭。
我最初知道此書,是在幾年前讀碩士的時候。導師彭剛先生要求我選擇思想史上的一兩位大人物來細讀其本人著作以及後世的經典研究,在知道我把盧梭作為自己的首選之後,他當即推薦瞭斯塔羅賓斯基的《讓—雅剋·盧梭:澄澈與阻隔》和這本《盧梭問題》。兩本書讀完,讓我見識瞭什麼是第一流的研究。
盧梭的思想是否融貫一體,其中是否有某種“道”一以貫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諸多不同作品之間的“分歧”?盧梭的思想與他那復雜的人生經曆之間有著什麼樣的聯係?“自由”、“感覺”這些關鍵詞在盧梭那裏又有著怎樣的特殊蘊涵?卡西勒在釋讀文獻、解答此類問題時所展現齣的精妙手法和思辨的力量讓我嘆服。在我看來,《盧梭問題》不僅是盧梭研究中繞不過去的精彩作品,而且在諸多以人物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中也堪稱經典,對於同類研究極富啓示意義。
毫無疑問,對於康德哲學的精湛研究滋養著卡西勒自己創建的哲學體係,而當我們看到他特特拈齣“感覺”一詞在盧梭那裏的雙重涵義,強調其主動性的一麵時,也不禁會聯想到卡西勒本人在哲學上的基本立場:在人類的一切文化領域,人心不僅起著調節作用,而且起著構造作用。我們也許可以說,卡西勒自己的哲學思想與他對盧梭的康德式解讀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係。
然而,這本《盧梭問題》是不是沾染上瞭太多康德哲學的色彩,卡西勒對盧梭的認識是不是也由此帶上瞭太多的“後見之明”?這大概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看完本書之後,讀者諸君當會有自己的見解。我私心以為,卡西勒的解讀確實要比許多其他的說法更有解釋力,更讓人信服。而我在譯完此書之後,再看到一些給盧梭貼上種種標簽然後尋章摘句加以證明的研究著作,覺得真是高下立判。如果我們終究無法完全避免某種“成見”,終究非得帶上某種“眼光”不可的話,我寜願選擇卡西勒這樣高明的成見和眼光。或許,也正是於此類成見與眼光的觀照之下,對某些重要問題的永恒思考纔得以在一種較高的水平上延續不絕。
《盧梭問題》發錶於1932年。此時,短命的魏瑪共和國已經行將就木。越明年,希特勒成瞭德國總理,而身為猶太人的卡西勒則開始瞭一去不返的流亡生活。
導 言
應該通過人來研究社會,也經由社會來研究人:想把政治與道德割裂開來的人,對二者都將永遠一無所知。
——讓-雅剋·盧梭,《愛彌兒》
一
將近兩個世紀以來,盧梭的哲學一直睏擾著其解釋者。試圖解決它的批評傢為數眾多,而其中最偉大,卻也是在很長時間裏最為人所忽視的批評傢之一,正是讓—雅剋·盧梭本人。在《懺悔錄》中盧梭強調,從整體來看,他的著作展現齣一種一緻與融貫的哲學:“《社會契約論》裏的所有放膽之言此前已寫在《論不平等》之中;《愛彌兒》裏的所有放膽之言此前已寫在《新愛洛漪絲》之中。”他說,讀者在其著作中發現的齟齬純粹是錶麵上的。這一信念對盧梭來說一定至關重要,在臨近生命終點又一次反思其作品時他重申:他堅持認為,在其所有著作之中,都有“一大原則”顯而易見。
隻有少數盧梭的解釋者認真看待這個自我評估。而大多數批評傢則在他的這部那部主要著作,或是在他一些熠熠生輝的雋語警句中找尋,並自命找到瞭“盧梭的本質”。更糟糕的是,盧梭的著作激發齣迥然各異的諸多運動這一事實雖確鑿無疑,但很多研究盧梭的學者據此就推斷說,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是盧梭作品的特徵,他們沒有注意到,門徒們僅僅取其所需,從而歪麯瞭其導師的哲學,這乃是眾所周知的趨勢。很多思想傢都因解釋者而遭殃,但很少有像盧梭這般受罪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堅稱自己的思想是一個整體,但互相衝突卻同樣言之鑿鑿的主張卻掩蓋瞭這種完整。
恩斯特·卡西勒的論文“論讓—雅剋·盧梭問題”(“Das Problem Jean Jacques Rousseau”)同意盧梭的論點,並力圖提齣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盧梭作品的理解,以揭示齣他思想的意義。要透徹理解卡西勒的成就之巨大,我們首先得簡要敘述一下他這篇論文所要駁斥的對於盧梭的諸種解釋。
二
盧梭的諸多學說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它們在各種各樣的精神和運動中都留下瞭印記。柏剋將盧梭痛斥為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的化身。德·邁斯特和博納爾(Bonald)譴責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和倡導毀滅性混亂的哲學傢。後來諸如亨利·梅因爵士之類的批評傢抨擊他立瞭一個“集體的暴君”,並在《社會契約論》中再次引薦瞭“身著新衣的老一套君權神授說”。
盧梭門徒之間的相互矛盾與盧梭反對者之間的相互矛盾一樣尖銳。雅各賓派以他的名義建立起恐怖統治;德國浪漫主義者把他作為解放者歌頌;席勒將他描繪為殉身於智慧的烈士:
蘇格拉底死在詭辯傢手裏,
盧梭受盡基督徒摺磨而死,
盧梭——他要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盧梭在18世紀最難纏的對手埃德濛·柏剋說得的確不錯:“我相信,要是盧梭尚在人世,在他神誌清醒的間隙,也會被其弟子的瘋狂實踐驚呆……”
在盧梭不再是那場政治鬥爭的象徵之後,各種解釋之間的衝突也絕沒有消弭。在革命與反動都煙消雲散瞭很久以後,盧梭依舊因最為變化多端的理由而受人稱頌或遭人責難。卡西勒的論文錶明,這些分歧並不僅限於盧梭的政治理論。盧梭一會兒被稱作理性主義者,一會兒又被稱作非理性主義者;他的經濟學被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又或是奠基於承認私有財産之上的;他的宗教被視為是自然神論的、天主教的或是新教的;他的道德學說被認為是清教徒式的,又或者是過於感情用事、寬鬆隨便的。
然而,既然大多數評論者都將盧梭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傢看待,或是從政治哲學方麵來評判其思想,那麼在分析他的文獻時,政治學範疇將最為有用。有人說盧梭是個人主義者,有人說他是集體主義者,有人說他是自相矛盾的作傢,還有人說他是在半路從個人主義轉嚮瞭集體主義。
在盧梭去世後的頭幾十年間,反革命者,如德·邁斯特(對他來說盧梭是政治上不虔敬的典型),和激進派,如狂飆突進運動的代錶們(他們盛贊盧梭是那即將來臨的自由時代的預言傢)都認為盧梭是個人主義的典範。荷爾德林稱他為半神,並將傳說中的盧梭對法律羈絆的藐視,敷衍成汪洋恣肆的詩句。
在針鋒相對的觀點流行之前,就已經有瞭這種將盧梭視為個人主義者的看法,而且這種看法也從未完全過時。一些著名的法國評論者巧妙地為它進行瞭辯護。例如,埃米爾·法蓋主張,“盧梭的一切都能在《論不平等》中找到。這固然是老生常談……但我相信確實如此。”而這部“人類的小說”(法蓋這麼叫它)有一個中心主題:人是善的,但置身於社會之中便開始變惡。法蓋覺得不得不承認,《社會契約論》是“反自由的”,盧梭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一丁點兒自由或者安全”。但他又辯解道:《社會契約論》“看似是盧梭著作中孤立的一部分”,並與“他的總體思路相抵觸”。盧梭的政治學說隻不過是一個異數而已。另一方麵,《論不平等》中個人主義的想法,“那反社會的觀念” 纔是根本所在——它貫穿於幾乎所有盧梭的著作之中,在《愛彌兒》裏尤為顯著。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亨利·塞經由不同的邏輯路徑得齣瞭相似的結論。他完全同意法蓋,認為“激發盧梭寫作《論不平等》的,是個人主義的、甚至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想法”。但他在以下這點與法蓋分道揚鑣:“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仍是個人主義者,雖然錶麵上恰恰相反。”盧梭政治學說的中心是要“確保個人充分發展其自由”。因此塞的結論是:“我們麵前的盧梭……是一名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說他想要給予國傢絕對的、富有侵犯性的權威是不閤實情的。”
相反的論點則認為盧梭是一個集體主義者,其最重要的源頭很可能是丹納的《舊製度》(Ancien Régime)一書。丹納認為,法國大革命——其間“野蠻的暴力對激進的教條韆依百順,而……激進的教條也對野蠻的暴力言聽計從” ——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人類世界知之甚少的知識分子的作品。因此,這些知識分子一味沉溺於抽象的理論推導,最終讓法蘭西人的頭腦感染上瞭革命的念頭。丹納將盧梭視為這些害人哲學傢的宗師,這就使得對盧梭的批評又為之一變。他主張,盧梭想用他的政治學說來給法律和政府以緻命的一擊,結果卻反倒不可避免地導緻瞭暴政:“由群眾來解釋主權在民說,將會導緻完全的無政府狀態,直到改由統治者來解釋,而這又將産生徹底的專製。”在丹納看來,盧梭的國傢是一座“在俗之人的隱修院”(卡西勒也提到這一機智的說法),“盧梭照斯巴達和羅馬的樣式建起這座民主的隱修院,在其中個人微不足道,而國傢就是一切”。
現在,這種觀點及與之相似的觀點在研究文獻中大行其道。卡爾·波普爾將盧梭的思想說成是“浪漫的集體主義” ,歐內斯特·巴剋爵士以為,“歸根結底,盧梭事實上是一個極權主義者……就算將盧梭設想為完全是個民主主義者,他完美的民主依然是一種多元的獨裁。”在這些說法中丹納的觀點都隱約可聞。雖說不是全部,但今日許多盧梭的讀者對於公意至高無上、人被迫自由以及公民宗教都銘記在心,而盧梭著作的其他內容卻被拋諸腦後,他們是會對丹納和巴剋深錶贊同的。實際上,現在時興的是把盧梭視為一個極權主義者——或許是“民主的極權主義者”,但還是極權主義者。
三
除上述兩種水火不容的解釋之外,還有另兩種觀點可為補充:有人主張,他的學說因其內在的矛盾而含混不清、支離破碎;也有人以為,在發展、闡釋這些學說時,它們從一個極端跳到瞭另一個極端。法蓋將《社會契約論》中他所以為的集體主義意蘊一筆勾銷,從而確保他能將盧梭解釋為個人主義者。巴剋在一陣躊躇之後,把盧梭歸入集體主義者,但他坦言,在盧梭的思想中無法找到一個真正的核心:“你是左派也好(特彆是左派中的左派),是右派也罷(特彆是右派中的右派),在盧梭那裏都能找到你自己的教條。”
此前很久,約翰·莫利對下麵這一點更為強調。他指責盧梭無視證據的來源——曆史與經驗,而這恰恰是一個完善的社會學說的根基所在。他嘲笑盧梭“性情狹隘、分裂、急躁”,而 “《社會契約論》的假設荒唐透頂”。他追隨著柏剋,把盧梭描繪為“典型的經院哲學傢”,“自以為術語分析是獲取關於事物新知的唯一正確途徑”,卻“錯把成倍翻番的命題當作是新發現的真理”。莫利最後總結:“《社會契約論》中的許多篇章不過是文字定義的邏輯推演而已,稍作一點直麵事實的努力,都會證明其不僅毫無價值,而且全無意義……”
這種認為盧梭“含混不清”的看法也廣為流行,盡管持此觀點的批評傢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之所以說盧梭的學說一錢不值,到底是因為它源自演繹、抽象的邏輯,還是因為像歐文·白璧德說的那樣,盧梭被缺乏條理和浪漫情感主義引入歧途。
對於盧梭思想的這種態度部分地被C . E. 伏漢的著作所抵消,開采盧梭政治學說那一富礦的所有人都深受這位學者的恩惠。在多年收集、校勘盡可能多的手稿之後,伏漢於1915年刊行瞭盧梭政治著作的定本,並加上瞭一篇頗有分量的導言。他那紮紮實實的兩捲本著作影響巨大——有如此影響完全在情理之中。與之後的卡西勒一樣,伏漢將盧梭的思想視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隻供陳列的教條:“用《社會契約論》中的開頭幾頁來抨擊《論不平等》,那盧梭的‘個人主義’將被看作隻不過是個神話。”《論不平等》“即便沒有直言,也暗示瞭一種比此前任何作傢膽敢論述的更為極端的個人主義”,而《社會契約論》開頭的契約則“構成瞭通往一種人類所構想過的最為絕對的集體主義之門徑”。要調和盧梭政治思想中這兩股並行的綫索也不容易:“盡管人們已竭盡所能,但這兩種對立的元素,即個體與共同體,還是彼此不那麼閤得來,好像互相之間有掩飾不住的敵意。”
伏漢認為,解釋盧梭的主要任務便是說明或者解決這一衝突,對此他自己分彆提齣瞭三種不同的解釋。第一,他主張早期的兩篇論文基本閤乎道德,它們寫得偏激,針對的是現存之惡。這種解釋為以下做法開瞭先河:後來如卡西勒和查爾斯·W.亨德爾這樣的批評傢視盧梭在根本上是一個道德傢,以剋服其思想中的所謂矛盾。第二,伏漢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嚮盧梭的抽象思想與具體思想之間的衝突。前者來自洛剋和柏拉圖,這使得盧梭的說法偏激而絕對;後者來自孟德斯鳩,這讓他斷定,生活從不輪廓分明,而原則要被環境所修正。伏漢發現,盧梭的著作越來越關注具體,這種關注在《社會契約論》的後麵幾章中占瞭上風,而在他最後的幾部政治著作,特彆是《山中書簡》(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和《波蘭政府》(Gouvernement de Pologne)中這種關注已經完全居於主導地位。
而伏漢的第三種解釋要重要得多:必須將盧梭在思想上的成果理解為一段從個人主義成長為集體主義的曆程。
把盧梭的政治著作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它便呈現齣從一個立場轉嚮幾乎是其對立麵的一種不間斷的變動。盧梭一開始鼓吹的是能夠想得到的最抽象意義上的自由。在第二篇論文中,它的理想狀態是每個個體都絕對獨立於其餘部分……《社會契約論》除瞭開篇的那幾句話外,反映瞭一種非常不一樣的——無疑不那麼抽象,也不那麼個人主義的——想法。在此處,自由不再被認為是個體的獨立,而是應在個體全身心地忘我於為國傢效勞之中去尋求……
雖然一點也不顯山露水,但語氣和文風卻全然變瞭……(在最後的幾部政治著作中),第二篇論文抽象的個人主義和《社會契約論》抽象的集體主義都同樣被忘卻瞭……這一漫長的曆程終於結束。盧梭現在正站在其齣發點的對立處。
伏漢版功不可沒,但這也不應讓我們對其瑕疵視而不見。伏漢聲稱在盧梭那裏發現的缺陷——言過其實和遊移不定的傾嚮——也奇怪地齣現在他自己的著作之中。他隻是在難得的靈光一閃之中,纔對盧梭思想的整體性有所洞察。而且,伏漢將自己局限於盧梭的政治著作,他強調瞭盧梭的思想的一個方麵,卻付齣瞭不及其餘的代價,這就不可能理解盧梭思想的意義。盧梭確是一名政治理論傢,並且是一名偉大的政治理論傢。但這隻能讓我們更有理由來仔細研讀《愛彌兒》、《新愛洛漪絲》和《懺悔錄》——這些書闡明並且很好地平衡瞭盧梭的政治哲學。伏漢版無意之中錶明,任何想要理解盧梭的批評傢都必須超越政治範疇,並將其著作看成一個整體。
四
盧梭研究中的觀點多種多樣,這也不能全都怪罪於解釋者。卡西勒認為,盧梭實際上既非含混不清,也不前後矛盾,倘若卡西勒這麼講不錯的話,我們就可以得齣結論說,與其後的尼采一樣,盧梭易於招緻誤解。為什麼會這樣?
關於盧梭,大衛·休謨在1766年寫道:“他的著作裏確實滿是誇誕之辭,我無法相信單憑滔滔雄辯就能支撐起他的著作。”但是,給評論者造成睏難的,正是盧梭的雄辯,而不是他的誇誕。盧梭不幸成為那些歡快語句的創作者。這些語句放在上下文中閱讀時,通常能被其所嵌入的論述闡述明白。而脫離瞭上下文,其言辭上的感染力就掩蓋瞭它們僅僅是隻言片語這一事實。被當作口號來使用時,它們就歪麯瞭或者完全破壞瞭盧梭的本意。
盧梭著作裏的三個例子能讓我們充分體味到,亨利·佩爾采用阿爾弗雷德·富耶的說法,稱之為“觀念力(idées-forces)”的東西是怎麼迴事。人們一再援引“沉思的人是墮落的動物”,來證明盧梭衊視思想與理性。“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句話被誤以為是給極端個人主義唱贊歌的開頭;無怪乎照字麵理解這一說法的讀者會對《社會契約論》後麵的內容大失所望。人們還斷定,“所以首先要把一切事實拋開,因為它們並不觸及此問題的要害。”錶明瞭盧梭對經驗證據不感興趣,他所偏好的,是因無視甚至藐視事實真相而得來的抽象命題。
謹慎小心並且滿懷同情地閱讀盧梭的所有作品,將會除去諸如此類的句子所引起的障礙,但盧梭很少有這樣的讀者。關於墓誌銘,塞繆爾·約翰遜曾這樣說過:“鎸刻的銘文並非是人們的誓言。”盧梭讀者也應心存類似的警惕。盧梭本人認識到他強烈的個人風格會給讀者造成睏難,他在給達皮奈夫人(Madame d’Epinay)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的書信用語時寫道:“如果您希望我們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對我的遣詞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語詞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義;與您交談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許會明白,它不像彆人那樣說話。”
將許多解釋者引入歧途的不光是盧梭的風格。引起誤解的另一個根源是盧梭的生平讓其解釋者的想象力和批評能力走火入魔。拜倫稱他為“自我摺磨的詭辯傢,狂野的盧梭”。
這鼓吹痛苦的人,他給
激情施瞭魔法,並從睏苦
中擠齣勢不可擋的滔滔雄辯……
許多盧梭的評論者禁不住誘惑,使“這鼓吹痛苦的人”的哲學淪為隻不過是其經曆的反映,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盧梭對自己這些經曆之麯解的反映。卡西勒在寫下麵這段話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類批評:“在研究盧梭的文獻當中,有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著作,給予我們的不是那個人的作品,而幾乎隻是那個人,這些著作隻在盧梭與他人的紛爭與不和,以及盧梭自己的內在矛盾之中去描繪盧梭。此處,思想史有消失於傳記中的危險,而傳記則看上去又好似一個純粹的個案史。”
誠然,追根溯源的解釋、人物傳記的取徑能讓我們深入瞭解一個作傢的動機,並有助於探尋其學說的個人或社會淵源。這有助於解釋為何作者著有某本書,為何他持有某些信念,但是其學說的客觀有效性並不受著書立說者個人曆史的影響。盧梭坦言將五個親生子女棄於育嬰堂這一事實,並不能影響《愛彌兒》中教育方案的價值。他在與百科全書派的爭吵中偏執多疑,這些爭吵可以說明他發錶《社會契約論》的動機,但卻不能使他政治學說的邏輯無效(或是有所改進)。許多盧梭的批評傢都無視這些解釋的準則。譬如,F.J.C.赫恩肖寫道:“盧梭的著作與其生平結閤得……如此緊密,不對他奇譎而非凡的一生有細緻入微的瞭解,就不可能理解那些著作。”有瞭這種說法作支撐,他便將盧梭的一生分為五個時期:不規矩的男孩、超級流浪者、涉世之初、靈感迸發的瘋子和被追捕的逃亡者。免去瞭對盧梭本意必要的、嚴肅的理解,赫恩肖就能用下麵這段話來概括最偉大的政治理論傢中的一員:“他是個沒有體係的理論傢,在形式邏輯方麵缺乏訓練。他泛觀博覽,無書不讀,然而消化能力欠佳。他是個感情用事的狂熱者,說話不經大腦。他是個不負責任的作傢,卻擁有寫作雋語警句的天縱之纔。”
這種理解的路數被歐文·白璧德推到瞭極緻。他的《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通篇都對盧梭大加鞭撻,這本書滑稽可笑地說明,隻關注傳記,就好似一瘸一拐、跛足而行。“盧梭對18世紀的巴黎懷恨在心,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年少時沒有養成本來可能讓他符閤巴黎風氣的習慣。”盧梭對於18世紀社交界的犀利批判就被白璧德這樣給打發瞭。“相信人性的善良,就是不斷慫恿逃避道德責任。”盧梭對神義論問題的解決也被這樣一筆抹煞。他還輕衊地將盧梭關於愛情的說法與其實際情況對比一番:前者讓他想起瞭“中世紀騎士對其貴婦人的膜拜”;而後者呢,“理想就此打住,現實是泰蕾絲·勒瓦瑟”。
很顯然,一個如此瞎用傳記方法的批評傢不大可能正確錶現他所鄙夷的思想傢的生平故事。白璧德對盧梭的學說的誤解之徹底一貫,真是驚人:“盧梭……眼中,一切內在、外在的束縛都與自由格格不入。”“他的方案實際上就等同於放縱那無邊無垠而又捉摸不定的欲望。”“人們能從盧梭那裏學到的本領,是淪落到理性層麵之下的那種本能的地步,而不是力爭達到理性層麵之上的那種洞察的境界。”
五
大約在本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小批學者開始迴到作為一個整體的盧梭著作中去,並從其中得齣,盧梭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緻的。這些批評傢並非對盧梭的個人主義或者集體主義這個問題喪失瞭興趣,但是這些政治學範疇已不再是他們矚目的中心。相反,他們尋求開拓解釋的視野。他們不否認盧梭的許多說法自相矛盾,但他們和盧梭一樣,認為這些自相矛盾並不損害其根本上的融貫一緻。為尋求盧梭那“一大原則”作齣最為卓著貢獻的,是古斯塔夫·朗鬆、E. H. 賴特,還有1932年的恩斯特·卡西勒。
朗鬆寫過一部著名的法國文學史,他將盧梭描繪為一名個人主義者。但他完全贊同E. H. 賴特,認為這並不是盧梭思想統一性的關鍵所在。賴特對《社會契約論》曾有一句鞭闢入裏的評論:“無論個人主義還是絕對主義,都非本書所欲為。”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作賴特和朗鬆評估盧梭全部作品時的點睛之筆。對於朗鬆的觀點至關重要的,是盧梭自己對其“大原則”的說法,這一原則在《愛彌兒》的開篇第一句話就說得明明白白,它也蘊含於盧梭的所有著作之中,並在《盧梭審判讓—雅剋》中再次齣現:“自然讓人曾經是多麼幸福而良善,而社會卻使人變得那麼墮落而悲慘。”朗鬆認為,這條原則是盧梭哲學的關鍵:《論不平等》告訴我們,社會在本質上的惡是不平等,而不平等並非自然注定——是富有和貧睏製造齣瞭這種不平等。《社會契約論》就是這條原則的例證,同時它也錶明瞭盧梭一直堅持的另一條原則:“人性往而不返。”自然人無法脫離社會,而是必須重新創造社會以重新創造自身。這樣,接下來《愛彌兒》中的教育方案也就順理成章瞭:它簡要地描述瞭“擁有文明人一切優點,卻不沾染其一絲邪惡……的自然人”的成長過程。《新愛洛漪絲》進一步豐富瞭同一主題的細節:它確立瞭人與人之間肉體關係上閤乎道德的價值觀,沒有這種價值觀,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不能有真正的善。最後,盧梭在“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中將上帝也歸入自己的體係:上帝讓人類是善的,並將道德的力量植入人之中,以製伏一個並非按照自然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的惡。朗鬆主張,盧梭哲學的各個部分就這樣閤為一體,互為支撐,居於其中心的學說,是相信人類能夠將自己轉化為善良社會中的善良公民,盧梭之洞見的一切威力正是源自這一中心。
在盧梭誕辰兩百周年,也就是1912年的時候,朗鬆發錶瞭一篇論述盧梭思想統一性的重要論文,重申瞭自己的立場:我們的確能夠發現盧梭作品的細節之間互相矛盾,要是願意的話,我們也可以指齣其學說與生活之間有著無法逾越的鴻溝,但是他思想的大方嚮卻清晰明白、始終如一。朗鬆認為,盧梭的問題乃是:“文明人怎樣纔能不返迴自然狀態,也不拋棄社會狀態中的便利,就重新獲得那如此天真幸福的自然人纔有的好處?在這一問題的觀照下,盧梭的所有著作就都可以被我們完全理解瞭。”早期的兩篇論文反對一切迄今為止存在的社會,並揭露瞭這些社會的邪惡;《愛彌兒》和《新愛洛漪絲》指齣瞭在個人道德、傢庭關係和教育的領域內改造個體的方式;後期的政治著作勾畫齣那種善良的人能在其中適得其所的社會。卡西勒完全贊同朗鬆的方法,贊同他嚴厲批評那些“把盧梭的每部作品都簡化為一個簡單而絕對的程式”的解釋者,卡西勒也同他一樣認為,盧梭的體係是“在其生活狀態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活生生的思想,麵對外在環境的一切變換與騷動,它都無所遁形”。
卡西勒論文的另一個卓越的先驅者是《盧梭的意義》(The Meaning of Rousseau)一書,作者E. H. 賴特不辭辛勞,仔細閱讀瞭有關盧梭的一切。讓賴特大吃一驚的是,遲至1928年,“都沒有一部英語作品,並且隻有極少數不管什麼語言的作品”力圖弄清楚盧梭想要說的是什麼。他自己的方法——與此前的朗鬆和之後的卡西勒相像——直截瞭當:“在努力弄清楚他的學說時,我試圖把他所有著作拿來一塊兒思考。如果我錯瞭,請通過訴諸他的所有言說,而不是偶爾閃現的一處矛盾來展現他的學說。”
賴特在“天性” 之中找到瞭盧梭潛在的觀念,但這裏的天性卻並非是用通常的方式來解釋的。賴特說:“必須通過人類的理性,按照人類天性的樣子來使人類得以完善,這一根本觀念貫穿盧梭的所有著作,並賦予其本質上的統一性。”於是,在討論自然人、自然教育、自然社會和自然宗教的章節中,賴特詳細闡述瞭盧梭的學說。自然人認識到:“自然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一定得是野獸或野蠻人。理性與良心也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而且確乎是他較好的那部分。這也不意味著他必須拒斥藝術與文明:“擴展瞭我們的所有藝術都是對的,而扭麯我們的藝術則都不對。”理性的任務便是嚮人類指明,在人發展的某個階段中,哪些對他來說是自然的;自由的任務便是使他能夠做他應做之事。隻有當我們遵守法律時,自由纔有意義,但我們贊同這法律是齣於自願,因為我們認識到它是閤乎理性的:“當我們的意誌自發地具有原則時,我們就會瞭解那終極的自由。”
自然教育的作用是防止製造齣小暴君或小奴隸。我們一定要讓孩子為他自己找到其自身能力的邊界;我們一定要等他長大到擁有理性的時候纔曉之以理——這是創造齣自然人的唯一途徑。盧梭的政治理論——自然社會的理論——延續瞭這一主題。像現在這樣的人類是不適閤自由的。必須使他們適閤自由,他們必須給自己創造齣一個能使他們適閤自由的國傢:“如果說公民必須造就國傢,那麼國傢反過來也必須造就那些公民。”賴特的立場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盧梭反對將孩童當作成人,,也反對將成人當作孩童。
最後,自然宗教是盧梭思想的閤乎邏輯的産物。它的目標乃是通過完全與感情相符地、自然地運用理性,而不是通過論辯與儀式來瞭解上帝。“自然宗教……是將要有所發展的最新宗教,也是所有其他宗教的唯一繼承者……自然人不是我們最早的野蠻遠祖,而是最後的人,我們正走在成為這最後的人的旅途之中。”
六
以上就是卡西勒在發錶其論文“盧梭問題”時,有關盧梭的研究文獻的大緻情況。卡西勒是傑齣的觀念史傢和專業的哲學傢,也是一名新康德主義者,這兩者結閤在一起使他成為解釋盧梭著作的理想人選。就像卡西勒所樂於指齣的那樣,在18世紀盧梭的讀者之中,幾乎隻有康德一人是因為盧梭那真正的而不是號稱的美德纔青睞他。盧梭的哲學極大地豐富瞭康德的倫理思辨,而卡西勒則進一步發展瞭在康德那裏已隱約可見的綫索,即盧梭的關鍵在於他的理性主義的自由觀。
在討論盧梭的文章裏,卡西勒精彩絕倫地展示瞭理解(Verstehen)的批評方法,他認為,批評傢領會哲學傢著作的過程要以搜尋充滿活力的思想中心為起點。批評傢不能將哲學傢的諸多學說看作是一連串各不相關的立場,而是應將之視為同一觀點的不同方麵。因此,批評傢必須有移情的天賦:他必須滿懷同情地進入——更確切地說,是重新復活——那位思想傢的觀念世界。而且,就算批評傢不為彆人也要為瞭自己,去發揮想象力以再造齣哲學傢著書立說和與人辯難時的環境。
曆史學與哲學就這樣交織在一起,難解難分;如果解釋者使自己沉浸於盧梭的世界,他就不會誤把盧梭對“文化”的抨擊當作是對一切文明的進攻,而是會將之視為對巴黎社交界所代錶的那種文明的批判,這樣來看纔是對的。與此同時,他也不會沉溺於閱讀盧梭的諸多學說不能自拔,而其他解釋者則從這些學說中汲取所有可能的結果。理解隻能是由內而外的過程。卡西勒對自己的曆史哲學之取徑的說法,即他的“目標不(是)記錄和描述乾巴巴的結果,而是闡明那內在的形成性的力量” ,當然也同樣適用於他的盧梭研究。
一旦我們理解瞭卡西勒的這種觀點,他對傳記的精妙運用也就變得更為清晰瞭。卡西勒並沒有對追根溯源的方法嗤之以鼻。恰恰相反,他的論文多處援引盧梭的《懺悔錄》、往來信件和《盧梭審判讓—雅剋》。卡西勒指齣,“除非我們將盧梭的著作迴溯至他生命的起點及這部著作在他個性中的根源”,否則,盧梭的著作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盧梭和他的著作緊緊地糾結在一起,誰要是想將二者分開,就肯定會切斷其共通的血脈,而對雙方都造成傷害。……盧梭的基本思想雖說直接源於他的天性與個性,卻不會被他的個性所局囿、所束縛”。要解釋盧梭,就應將傳記作為重要的齣發點,但絕不應該止步於此;不應該將關於盧梭怪癖的閑言碎語和曆史考證混為一談。
卡西勒的方法雖然沒有指定,然而卻指齣瞭一條通往側重於研究人性的曆史學與哲學的道路。康德對哲學人類學的問題興味盎然。卡西勒也同樣如此。他的巨著《符號形式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將人描述為符號化和塑造世界的動物。而他還不止探尋瞭盧梭對人性的看法——他強調,找尋人類的本質是盧梭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其早期的《論不平等》便是明證;而到瞭暮年,盧梭說自己是“人性的曆史學傢”,這不禁讓人想起,霍布斯將對於人的研究界定為:“解讀自己,不是具體的這個人或那個人;而是人類。”
在卡西勒這樣的哲學傢手中,這種想象的方法有助於揭示使一個思想體係融貫一緻的那些原則。但這篇討論盧梭的文章也說明瞭上述方法在使用中麵臨的種種睏難。對思想核心的不懈求索會將實際上是根本性的矛盾視為無關緊要的而撇在一邊。力求統一與整全的理想主義也往往使矛盾得以調解,達到瞭據認為是更高一層的綜閤,但實際上這矛盾卻是無法調和的。人們的確有可能會認為,卡西勒強加給盧梭的體係已經言過其實,而且對“自由”的強調也使他對盧梭的康德式解釋超過瞭事實所允許的限度。此外,卡西勒對待傳記的理性主義的方法也容易遭人詬病。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批評傢就應該對其所研究著作的作者進行精神分析——這種辦法常常離題萬裏,而且有時有害無益。但是,完全忽視弗洛伊德以及他所建立的那門學科的成果,卻是像卡西勒這樣倚重於傳記的批評傢所付不起的代價。
然而,瑕不掩瑜,卡西勒的論文既是第一流的思想成就,也是一等一的藝術品。在我們麵前,論證有條不紊、從容不迫地展開,證據鏈被仔細地鍛接起來,環環相扣,到結尾處,讀者把握住整個證據鏈,發現它是那麼牢靠,隻有到此時,人們纔能感受到它的全部力量。
七
卡西勒的論文成功地解決瞭它給自己提齣的那個問題麼?自1932年以來,一些討論盧梭的著作顯示齣卡西勒論文的影響,而且它們也承認這種影響。當中最為重要的,興許要算查爾斯·W.亨德爾的《道德傢讓—雅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Moralist),書中特彆肯定地寫道,對卡西勒的“精彩討論”“深錶贊同”。 亨德爾的研究成果是一部詳盡的思想傳記,其要旨就隱含在書名之中:盧梭尋求的是界定善的生活;他的基本問題是“把人類從他們自己內在與外在的暴政之下解放齣來”。這樣來看,他的所有著作就可以視為是一貫的,也是一體的瞭。亨德爾對盧梭作瞭全麵徹底的研究,其間他還為駁斥其他解釋而煞費苦心,卡西勒後來也對他的作品予以褒揚。
近年來,羅貝爾·德拉泰的兩部著作大大豐富瞭有關盧梭的研究文獻。與大多數解說者不同,德拉泰認為,“盧梭的政治學說來自他對屬於被稱之為自然法與萬民法學派的那些思想傢的學說的反思。”德拉泰先生手法高明,他追查到,盧梭倚重於格勞秀斯和普芬道夫,就像他倚重於霍布斯和洛剋一樣。德拉泰令人信服地證明瞭,盧梭在精神上屬於人們認定他已經剋服並予以否認的理性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對於這種理論,卡西勒論文的讀者心裏早有準備。德拉泰大大擴充瞭許多卡西勒隻是簡要分析瞭一下的觀點,他還闡明瞭盧梭是如何處理良心與理性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人類理性的發展問題。他的結論與卡西勒相當接近:“盧梭絕不會認為,一個人會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性……恰恰相反,他想要教會我們如何好好地運用理性……盧梭是一名意識到理性局限的理性主義者。”德拉泰並沒有讓卡西勒的論文免於一切批評。在他看來,卡西勒對盧梭的理性主義的論證,有力得過瞭頭。但話又說迴來,他還是稱卡西勒的這篇論文是對盧梭的新康德主義的諸種解釋中“最為重要的”一篇,也是“迄今為止,朝嚮綜閤所做齣的最大努力,這種綜閤試圖從整體上把握盧梭的思想,並展現齣其中那深刻的融貫性”。
但是除去影響之外,我們對卡西勒的成就還能說些什麼?一名思想傢並不是一道謎題;他永遠不會被徹底“解開”。但卡西勒將讓—雅剋·盧梭問題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更高的層麵。他的論文漂亮地闡明瞭盧梭的基本概念之間,以及這些基本概念和他思想其餘部分之間的關係:實際理性與潛在理性之間的關係,可完善性與要求一個新社會之間的關係,教育與閤理性之間的關係,還有最為重要的是,理性與自由之間的關係。雖然仍然不能使一些批評傢信服;但如果感情用事、自相矛盾的極權主義者的盧梭形象大體上已經讓位於一種更為精準的評價,那麼卡西勒的論文可以說對此貢獻良多。
八
對於卡西勒的讀者來說,隻有在牢牢確立起盧梭哲學基本上的統一性之後,他的政治學說的問題纔能浮現齣真實的層麵。我要再重申一次,盧梭的政治思想為個人主義者、集體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極權主義者所用,這確是事實,但盧梭哲學在客觀上的一緻性卻沒有因此受到影響。然而話又說迴來,盧梭的政治學說與曆史進程之間的關係也引發瞭一些重要的問題,卡西勒的論文有助於我們將這些問題錶述清楚,但它本身卻沒有提供答案。
在我這篇簡要的導言中對這一關係做詳盡的考察不太閤適,但我們或許可以用它來指示考察的方嚮。那麼我以為,我們應該區分作為批判工具的盧梭政治學說與作為建構工具的盧梭的政治學說。把盧梭政治學說作為批判標準來用的時候,它對民主運動無比寶貴;把它當作一幅政治的藍圖,就會對自由主義的理念與製度産生惡劣的影響。
盧梭的“一大原則”——人類是善的,是社會讓他變壞,但也隻有使他遭此浩劫的社會纔能拯救他——是一種批判的工具。它斷定,改革不僅是可取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改革是可能的,它錶明,一個隻産生惡棍與愚人的社會證明瞭自身也有權存在。但是,盧梭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成為那場民主運動的哲學傢:通過其全部著作,他列舉齣那些使當時社會邪惡的特徵,也舉齣瞭可以由之辨識齣善的社會的特徵,在這種善的社會當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至高無上。社會最大的惡是不平等;社會最大的善是自由。從一開始的兩篇論文到《盧梭審判讓—雅剋》,盧梭都一再錶達瞭這些觀點——這也是民主武器庫中的兩門利器。盧梭在社會學說方麵最為重要的論述都是批判的工具。我們隻消迴想一下,他要求公意必須絕對普遍(“必須把所有的票數都計算在內;任何形式的例外都會破壞它的公共性。” );他批判代議政體,在其中主權民族交齣瞭他們理應予以保留的東西(“隻要是一個民族舉齣瞭自己的代錶,他們就不再是自由的瞭;他們就不復存在瞭。” );他還抨擊那時法國的思想文化及風氣(與不平等一樣)貶損瞭而不是拓展瞭生命。
對於一個手中無權的政黨,或是一名持對立觀點的哲學傢而言,沒有什麼學說比盧梭的更為有用、更加一貫瞭。然而,一旦盧梭的學說化身為製度,一旦那個民主黨派掌瞭權,盧梭哲學中的絕對主義意蘊就會浮現齣來。盧梭抨擊自願聯閤起來的團體,反對異見派,他希望將一種公民宗教強加於人,違背它隻有被流放或處死。這與他思想中的其餘部分是協調一緻的:盧梭想要創造齣的那種公民——像愛彌兒那樣的新人,必須要小心翼翼地對之加以防護,以免他受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腐蝕——是不會願意從屬於任何有著特殊利益的群體的;對於公意做齣的決定,他也不會有絲毫異議。他的確會將這種公民宗教當作必不可少的粘閤劑,並毫無顧忌、心安理得地相,,信,它或宣稱信仰它。公意至高無上,這是對好人的一項指定要求,一項道德規定,雖然世上還不曾有過這種好人,但平等的社會與自然的教育將使之誕生。就像盧梭自己所說的那樣,它預先設定,“公意的一切特徵仍然存在於多數之中;假如它們在這裏麵也不,存在的話……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
正是這種一切從規範齣發的思想,這種從人類的可完善性推理齣隻有完美的人纔能生活於其間的完美國傢的烏托邦傾嚮,使得盧梭的思想用作批判時是如此偉大,而用作製定憲法的指南時卻又如此危險。一旦批判者變成最高統治者,那盧梭的批判的原則就會化為鐐銬。
九
閱讀卡西勒促使我們對盧梭政治學說進行瞭這般無拘無束的思考,這既是嚮卡西勒論文所提示的領域,也是嚮盧梭政治思想那經久不衰的魅力緻敬。卡西勒本人並不是政治理論傢,但他的作品對政治理論傢來說至關重要,政治思想演生於一個更為廣闊的語境之中,而政治理論傢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這一點拋諸腦後瞭。①卡西勒的論文在不斷地提醒人們,在盧梭的腦海中,政治著作與其所處的語境是一個整體,將二者割裂開來的政治理論傢就會將這些著作的意思肢解得七零八落。故而,絕少有最偉大的政治理論傢隻是政治理論傢而已,這並非偶然;他們首先是對人類,以及對包括人與社會之間關係在內的世間萬象都感興趣的思想傢。亞裏士多德稱他的《政治學》是自己所著的《倫理學》的續篇,霍布斯認為,《利維坦》一書在寫“共和國”之前先用十六章的篇幅來寫“人”是極為重要的,對於這些蛛絲馬跡,讀者應該予以重視,而解釋者也應該認真對待。
卡西勒對此的確是認真對待的。關於詩歌,塞繆爾·約翰遜曾寫道:“考察過整體之後,纔能去研究部分;要原原本本、恰如其分地理解任何偉大的作品,都必須與之保持一種思想上的距離;貼身緊逼的研究路數固然可以使更加細微精妙之處得以彰顯,但那整體之美卻再也看不齣來瞭。”卡西勒的看法與約翰遜如齣一轍。
英譯本說明
恩斯特·卡西勒的論文“論讓—雅剋·盧梭問題”(“Das Problem Jean Jacques Rousseau”)最早發錶於《哲學史檔案》第41期(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XLI, 1932, 177—213, 479—513)。1932年2月27日,卡西勒嚮法蘭西哲學學會(Société Fran*9觭aise de Philosophie)作瞭一個關於“讓—雅剋·盧梭著作的統一性”(“L’Unité dans l’oeuvr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的演講(與會者隨後進行瞭討論),卡西勒在演講中用法語陳述瞭他這篇論文的基本內容。參見《法蘭西哲學學會會誌》(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oeaise de Philosophie, 32d year, No.2, April—June, 1932,p. 46—66)。
“論讓—雅剋·盧梭問題”一文最初是用德語寫成,但卻一直未曾有德文單行本,而它有一個意大利譯文的小本子Il problema Gian Giacomo Rousseau(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38), 譯者是Maria Albanese。目前我這個版本是它第一個英文譯本。但需要指齣的是,在卡西勒的《啓濛運動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Fritz C. A. Koelln 和James P. Pettegrove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和《盧梭,康德,歌德》(Rousseau, Kant, Goethe, James Gutmann, Paul Oskar Kristeller和John Herman Randall,Jr.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的“康德與盧梭”(“Kant and Rousseau”) 一文裏,含有本文當中幾個篇幅不長的段落。
在這版當中,我力圖在英文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貼近卡西勒的原意與風格。有幾處印刷錯誤我沒有特彆指齣便將之更正,卡西勒的長句也被拆分,除此之外,一仍其舊。
卡西勒援引法文時格式並不統一——至少在這篇論文當中是這樣的。有些引文他譯為德文,有些他則沒有翻譯。凡是他譯為德文的地方,我都將之譯成英語,而凡是他沒有翻譯的地方,我也照他的樣,在文中保留法文,而將英譯放在腳注中。
但有一處(p.86—88的引文)我是直接從原文,而不是從卡西勒的德文翻譯的。除去法文詩是由我的編輯,J. Christopher Herold譯為英文之外,其他的法文都是我自己翻譯的。
卡西勒在引用文獻時經常不加說明便省略其中的字詞,甚至是整句話(附帶說一句,他從未歪麯原意)。有些省略的地方我加以補足,大段大段的省略我則按照慣例,用方括號加省略號錶示。引用原文時我使用的是盧梭著作的Hachette版(這一版本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多次重印),因為它比卡西勒所用的版本好找得多。卡西勒用的版本是Jean Sénelier在《盧梭著作書目提要》(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soeuvres de J.-J. Roussea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中所列舉的第1901號:《盧梭著作全集》(Collection des oeuvres complèttes [sic] de J.-J. Rousseau, Chez Sanson, Aux Deux Ponts [Zweibrücken], 1782—1784, 第三十捲,12開)。
除瞭格式上的小問題外,卡西勒本人的腳注原樣不動。腳注中也和正文一樣,我所添加的部分都用方括號標明。援引盧梭作品時人們從不寫全書名;用的是大傢普遍認可的縮寫——如《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法語引文用的是現代拼寫方式。
彼得·蓋伊
譯 後 記
感謝何兆武先生幫我解決瞭書中涉及法語和德語的若乾問題,感謝我的老師彭剛先生不厭其煩地為我答疑解惑,並糾正瞭譯文中的許多錯誤,從而使得翻譯此書對我來說更是一次難得的學習。另外,與朋友黃穎、梁爽和張可力的討論也讓我體會到“疑義相與析”的快樂。沒有他們的幫助,翻譯《盧梭問題》於我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消說,譯文中肯定還有不少漏網的錯誤,這自然要由譯者來負責,也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王春華
2007年9月16日
盧梭問題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25
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盧梭問題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緻達朗貝爾的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緻達朗貝爾的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戰爭與和平的權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戰爭與和平的權利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異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異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尼采在西方(重訂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尼采在西方(重訂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盧梭與伏爾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與伏爾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問題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盧梭及其著述不僅對人類思想、社會發展産生瞭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引起後人長期圍繞對其褒貶展開激烈的爭論。比如,盧梭的學說內在是否存在著矛盾,特彆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其他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盧梭的思想與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發的諸多暴力革命是...
評分盧梭及其著述不僅對人類思想、社會發展産生瞭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引起後人長期圍繞對其褒貶展開激烈的爭論。比如,盧梭的學說內在是否存在著矛盾,特彆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其他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盧梭的思想與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發的諸多暴力革命是...
評分盧梭及其著述不僅對人類思想、社會發展産生瞭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引起後人長期圍繞對其褒貶展開激烈的爭論。比如,盧梭的學說內在是否存在著矛盾,特彆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其他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盧梭的思想與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發的諸多暴力革命是...
評分盧梭及其著述不僅對人類思想、社會發展産生瞭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引起後人長期圍繞對其褒貶展開激烈的爭論。比如,盧梭的學說內在是否存在著矛盾,特彆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其他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盧梭的思想與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發的諸多暴力革命是...
評分盧梭及其著述不僅對人類思想、社會發展産生瞭極其深遠的影響,也引起後人長期圍繞對其褒貶展開激烈的爭論。比如,盧梭的學說內在是否存在著矛盾,特彆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其他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盧梭的思想與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暴力盛行以及爆發的諸多暴力革命是...
圖書標籤: 盧梭 政治哲學 卡西爾 哲學 法國 法國哲學 通識 思想史
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問題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把盧梭給康德化後,就是強烈的違和感。。。
評分第一篇比第二篇簡單〜
評分分析盧梭思想極好的一本書,受益頗多。
評分論著作與人格的矛盾
評分主要意圖在統一盧梭著作中的思想矛盾問題。認為社會契約論是盧梭著作的異數,於是從中抽取齣“公意”概念作為統一盧梭思想的關鍵詞,此為“問題一”的核心。通過區分理想的與實際的“自然”、“社會”概念,將“浪漫”的"盧梭"形象修正為"前康德"的理性主義者,此為問題二的核心,以愛彌兒為參照點
盧梭問題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論哲學生活的幸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哲學生活的幸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自由及其背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自由及其背叛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盧梭全集·第5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全集·第5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百年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百年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新愛洛伊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新愛洛伊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孟德斯鳩與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孟德斯鳩與盧梭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讓-雅剋·盧梭明信片畫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讓-雅剋·盧梭明信片畫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漫步遐想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漫步遐想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盧梭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文集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社會契約論及其他晚期政治著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社會契約論及其他晚期政治著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漫步沉思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漫步沉思錄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論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論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追尋真誠:盧梭與審美現代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追尋真誠:盧梭與審美現代性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盧梭全集·第9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盧梭全集·第9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社會契約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社會契約論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