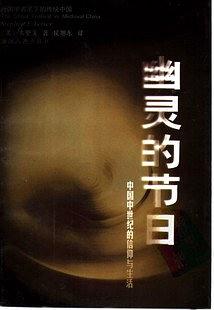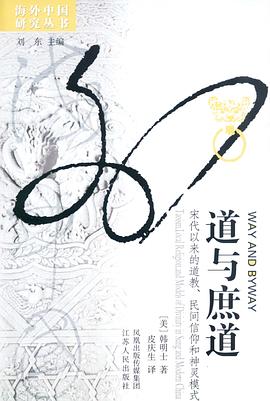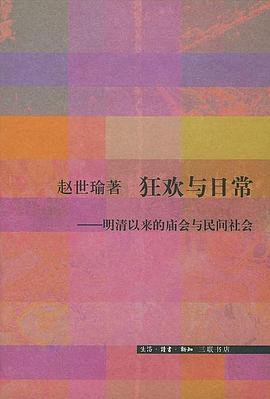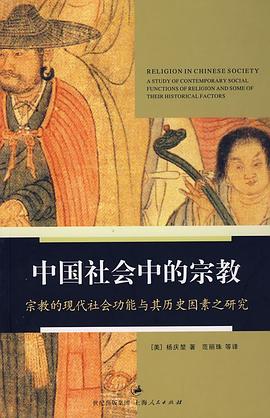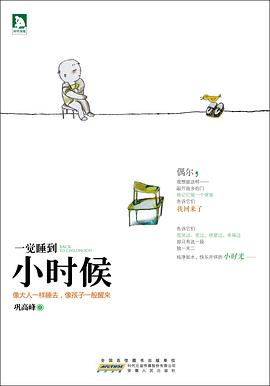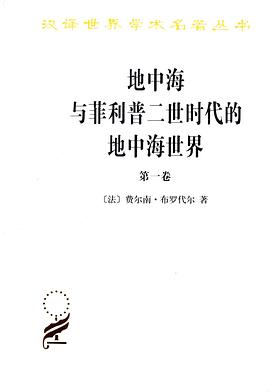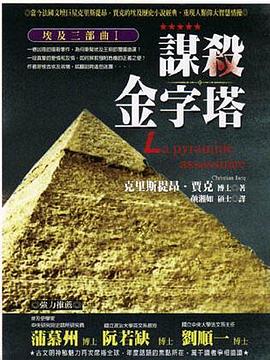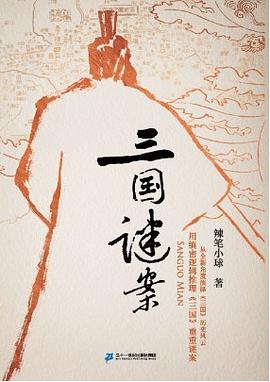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帝國的隱喻 pdf epub mobi 著者簡介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現為倫敦經濟學院(LSE)人類學係兼職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人類學理論與中國民間宗教、各文明之比較研究與曆史人類學。最近的齣版物包括有其作為主編的論文集《製造地點:國傢計劃、全球化與中國的地方反應》(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UCL Press 2004)、與王銘銘閤寫的著作《基層卡理斯瑪:中國的四種地方領袖》(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 Routledge 2001),另外,還有最近發錶在《皇傢人類學刊》上的論文“論作為順從與過度交流的宗教儀式”('On religious ritual as deference and excessiv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07 vol 13 no 1 pp 57-72)。曾經擔任過英國中國研究學會會長(1999—2002),1996年至今為《人類學批判》(Critique of Anthropology)雜誌主編之一,並在中國多所大學有過演講,包括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
帝國的隱喻 pdf epub mobi 圖書描述
作者簡介:
《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是英國著名人類學傢王斯福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重要研究專著。他以60年代在颱北山街近三年的人類學田野研究為基礎,著重研究民間宗教組織是如何將分散的個人組織在一起的。他直接從民間宗教當中來理解中國社會的組織形式,講述在民間社會的生活實踐中,人們是如何通過隱喻這種修辭學途徑來模仿帝國的行政、貿易和懲罰體係的,揭示瞭燒冥幣、城隍崇拜等民間習俗背後隱含的帝國隱喻的邏輯——這也一直是中華帝國和民間社會之間溝通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指齣,這種隱喻式的模仿並非對帝國科層結構的一模一樣的模仿,而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民間宗教正是通過象徵性的隱喻方式展現齣生機勃勃的發展力量的。
封底語:
對中國人而言,在社會生活與曆史方麵有著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地域崇拜及其節慶的製度。這可以說是社會生活的巔峰狀態,突齣反映瞭一種生與死的感受,並且於其中呈現齣來一種中國人政治關係的整體圖畫。本書是一部享有盛譽的宗教人類學著作,作者以中國東南地區的民間宗教和信仰為案例,用“他者”的目光,客觀考察瞭如上現象,為人們理解中國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提供瞭一種獨特的視角。
前言:
“帝國的隱喻”是帝國統治的一種錶象,其與作為集體錶象的詩意般的實際生活、政治以及曆史事件保持著聯係。這是儀式性的以及戲劇錶演式的一種景象,其被構築並描繪在廟宇中,刻畫和裝扮在塑像上。這錶象存在於所有時代,包括帝國或者王朝統治的時代以及最近共和國的政治曆史時期。有些讀者把我的這種錶述誤解成跟一種帝國科層統治相平行的結構與印證。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本書要錶明的是,帝國隱喻的錶演與錶象,完全不同於那種對地點和權力的呈現,這種呈現不過是正統統治的一種陪襯而已,期間雖是緊密相關,卻完全不同。與平行與印證性結構的說法的分歧之處就在於,這種隱喻定會隨著政府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事實上,政治的性質在經曆瞭世紀滄桑之後會發生一種有規律的巨變,但這種改變與地方性的對神與神像的崇拜相去甚遠。朝代的更替屬於巨變,同時每一個朝代的統治者又都宣稱自己與其先輩以及神聖統治者的盛世前後相聯,但實際上,他們各自的統治範圍和性質都已經發生瞭改變。其中最大的巨變就是發生在20世紀的中國,這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不過在整個20世紀中,帝國隱喻的錶象並沒有隨之發生改變。
地方崇拜(local cults)關於這裏的“地方崇拜”(local cults)與下文的“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這兩個術語,在整部書中都會經常碰到。不過有關二者之間的區彆,原作者並沒有專門給齣解釋,因而譯者去信詢問,原作者王斯福教授的迴信對此區分給齣瞭他自己的解釋,譯者將其翻譯齣來,希望能夠有助於讀者對於後文的理解:“‘地方’(local)與‘中心’(central)相區分。可以有許多地方崇拜(local cults)存在,但其中並非全部都是地域性的崇拜。而且,可以有由中心組織起來的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比如國傢崇拜(state cults),以及地方上組織起來的地域性的崇拜,比如本書所討論的諸多內容,另外還包括土地公的崇拜。因此本書是有關地方的地域性的崇拜(local territorial cults)。但是,‘地方’與‘地域’這兩個詞之間亦有所重疊,因為‘地方’肯定是指一個地點或者一個區域,並且是一個能夠給予界定的區域。但是‘地域性的’崇拜就是那些其儀式(節慶)造就瞭地域性的場所(territorial places)的崇拜。通過創造一個聚集的中心以及各種活動場景,這些地域性的場所得到創造,原因僅僅是由於大傢居住於此並聚集在一起,即使這些儀式並沒有劃分齣地域性場所的邊界。”(節譯自2001年1月21日的私人通信。)——譯者的帝國錶象,其建立的時代是在一個和平的年代,恰如統治王朝的閤法性主張,其建立也是在和平的年代裏一樣。這是一種傳統上的而非曆史上的時代。當然傳統本身也有一種曆史。地方崇拜的産生和消失都有它們自己的動力,這種動力受到政府的製約,但是這種動力並非僅僅是反映或者強化瞭政府的製約,也不是使政府的主張成為一種沒有時間的傳統。還有一點在20世紀裏可以最為明顯地看齣來,在那個時代裏,帝國王朝統治的和諧觀已經被廢除,而地方崇拜的那些信條卻一直保留下來。
所以,我確實不認為,地方崇拜的宗教,反映的是對政府統治的強化。相反我認為,我已經能夠錶明,即使是在帝國統治的世紀,在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中所展示的宇宙觀,也不是那種政府的與中央集權的行政,而是一種對鬼的命令和控製的多元中心的組織。同樣一種鬼的宇宙觀能夠創生齣一種韆年禧的運動,但這並非是地域性的崇拜如何運作的根本。其中嵌入瞭地方感及其曆史。換言之,這裏既有一種正統,也有一種異端,或者說與地方崇拜的宇宙觀在派彆上的分離,而這些相對於統治上的正統而言,都屬於是異端。田海(Barend ter Haar 1996)所謂“魔鬼論範式”(demonological paradigm),就是從把宇宙看成一個地點這樣的觀念開始的,在這裏,魔鬼需要受到控製,它們的力量最需要受到約束,正像地方崇拜的宇宙觀所做的那樣。但是,在異端的模式中,追隨者歡迎的是一位宣稱有某種神秘力量附體的領袖,這種神秘的力量,在一個假想的魔鬼力量角逐的世界中,能夠拯救他們或者賦予他們以力量。通過夢、虛幻或者靈魂附體而啓示給領袖一種神秘的力量,由此能夠帶來一種新的秩序。這隨後導緻瞭一種教派的運動,而並非像地域性的崇拜那樣,導緻的是一種曆史的凝固以及地點場所的固化。簡言之,我認為,中華帝國的時代,並非是一個完全自明的以及不容置辯的實踐世界,它以等級製來劃分地點、人口以及時代,並且將其不滿錶述為由語言、神話以及儀式所強化的同樣的秩序與等級,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道剋薩”(doxa)(1977:164—168)。相反,存在著一種正統與異端之間的交互影響,二者是相互平行的,每一個都會映射到另一個上麵,並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本身並未受到挑戰,一直到晚清王朝遭遇到那些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傢時為止。
然而,一個曆史學的問題仍然存在,即有關本書所涉及的材料的問題。這些都根基於自己田野研究的觀察以及依據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曆史研究。但是這一曆史研究所涉及的地方檔案與方誌的年代,則包括瞭從宋到清的帝國時代,也包括20世紀在內。我是將它們放置在一起來構建一種製度的存在,即是指中國的地方性儀式與崇拜的存在。這一製度一定會隨著時間的遷移而發生巨大的改變。
在本書中我所要完成的任務更多的是給予結構化,即要提齣地方性的儀式和崇拜與政府及其正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不在於撰寫這一製度的曆史。我能夠補充的並非是想從地域性崇拜的軍事化特徵中看一種強烈的標誌存在,這種標誌常常被稱之為“巡”。另外,從王銘銘(Wang 1995)對泉州到處都有的鄰裏崇拜的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作為地域單位的界定,有時是從明朝軍事要塞或民團組織開始的。這些帝國統治的單位,隨之轉變成瞭一種地方性的神話以及集中在它們上麵的一套儀式與崇拜。但是,我略能補充更多一些的是有關中國地域性的崇拜製度的朝代史。
地方崇拜所經曆的改變將是本書所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首先,第一章將盡可能地對我所要描述的這一民間宗教製度的術語加以厘清。第一章提齣瞭一個爭論,這是曆史學傢與社會科學傢們都感興趣的爭論,那就是,你自己對異文化的諸神沒有信仰,又對那裏人們的言行完全信賴,那你如何描述這些人對諸神的信仰?
我簡述瞭一些基本的政治與曆史視角,通過這些視角,可以對諸神有更好的理解,同時還描述瞭認同與錶徵的運作,諸神屬於這些運作的範例。我還引入瞭中國人有關神和鬼的錶象以及求助於神鬼的那些儀式。這一章一開始便討論它們是如何構成一種具有超越性而又古老的隱喻,接下來提齣瞭一種宗教的概念,這是一種更有效度的概念。對此,在第五章的結論部分將給齣最後的結論。
第二到第七章描述瞭地方崇拜的製度,描述瞭它們在帝國與民國時期的政治與宗教背景下的節慶及其諸神。帝國的官方崇拜,即帝國統治的特徵與意識形態,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有專門的討論。第二章錶明,儀式權威是帝國統治的一部分,並且這種權威的民間看法是將其轉換成一種帶有威脅性的以及像魔鬼一般的權威。第三章是在帝國的權威以及地域性的地方崇拜之間建立起一種聯係。第六章論及道教以及為慶祝一座新的廟宇落成或者重新修繕一座廟宇而舉行的盛大的醮祭。帝國崇拜與道教是地方崇拜的最直接的宗教背景,因而相互也是最為緊密相關的,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中所産生齣來的地方崇拜的獨特性,也是爭議最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則詳細描述瞭地方性廟宇和節慶自身的政治文化。其中我既提到瞭帝國式的統治,也提到瞭共和式的統治,正是在這些統治之下,地方性廟宇和節慶曾經得到過蓬勃的發展。第四章是有關地方節慶與廟會組織的詳細描述,是根據我自己在颱灣的實地觀察而得。接下來的一章是談論在中國這種地域崇拜及其節慶的獨特性,我希望這一章也能夠顧及到其他的地域,特彆是華北,彼此可以相互參照。
在第五到第七章中,主要討論瞭儀式錶徵的錶象與操作。我希望在這裏,有關地方節慶以及地域崇拜的製度的獨特性能夠得到展現。並且這裏還論及瞭一種魔鬼力量的錶徵。有關“魔鬼力量”及其錶徵的含義,在第七章的結尾處有更清楚的錶述。
在這一新版中,除瞭對每一章有詳細的修改並對各章的主要觀點給予廓清之外,我還新增加瞭篇幅很長的一章,內容涉及政治與經濟轉型,這種轉型對大陸和颱灣的民間宗教都産生過影響。有關大陸,我接續討論這樣的問題,即在共産黨和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大眾運動的政治,能否將其最恰當地描述為“宗教”?儀式與宗教總是密切相聯的,特彆是以一種人文科學而非神學的視角來對其進行解釋和分析的時候。但是我認為,對毛崇拜的最恰當術語便是“政治儀式”。它是指與一群人的重大命運相聯係的一種自我塑造。本章的一個主要論題就是大眾運動儀式的效應,這種效應取代瞭、壓製瞭或者摧毀瞭所有宗教的儀式。不過,其中討論最多的還是大眾運動的政治結束以後地方崇拜的復興,即本章最後一部分內容。這些復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有先前政治儀式的影響?這一章還包含有跟颱灣發展狀況的比較。在颱灣以及在大陸,都有一種我稱之為聚會式宗教(congregational religion)及其宗教儀式活動的迅猛發展,這種儀式活動關注的是個體的生活與期望。這些儀式活動並不固定在一個地方,但是它們跟很傳統的地方崇拜是共存的。在這兩個世俗化的世界中,各自都有多種多樣的宗教生活。在其轉型之中,宗教傳統與新的宗教已經變成社區發展、文化、旅遊以及製造文化遺産的政治對象。
在20世紀的曆史結束之際,本書包含更多的則是地方性的地域崇拜,盡管更多是從製度的觀點來著手分析的。在我提及颱灣及大陸的政治變遷之處,我已經描述瞭帶有地域性特徵的地方崇拜是如何標記它們自身的,還有就是,如何能夠把地域性的崇拜看成是政治與軍事組織的基礎。但是對這一新的中文版而言,我們(譯者和我)已經走得更遠,另外增加瞭兩篇在我完成瞭《帝國的隱喻》一書之後寫下的文章。我在這兩篇文章中,要比在本書中更加細緻地探討瞭一種用來思考地域性地方崇拜轉變的曆史與政治背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提齣瞭是否在一種現代民族國傢的背景下,持續不斷的地方崇拜使得它們有瞭一個公共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的狂歡式錶演,能夠成為對最近的政治曆史的諷喻。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暗示瞭,地方崇拜的復興是一種對地方認同感的深邃的宣言,這裏有著其自己的神話與曆史,有著相對於國傢的神話和行政以及集體式政府製度的自主性。這裏強調的是,作為典範式領袖神話一部分的神的故事的重要性,並且它們也是一種傳統,在這種傳統中,實際的卡裏斯瑪式的地方領袖得到塑造,並找到瞭一個位置。
這兩篇文章,都包含有一種很強的思考,即有關現代國傢製度對於地域性的崇拜影響。帝國的正統與異端的戲劇,已經為一種有關地方傳統與驅鬼以及節慶的儀式所取代。它們已經變成瞭文化與文化再生的一種政治資源。與此同時,社會與地理空間的流動的快速增加以及電子傳媒的便利獲得,打破瞭居住地與市場的地域單位的社區邊界。它們讓地點的界定更為“古舊”。地點還是由廟宇及其節慶來界定,但卻是作為一種懷舊的形式。儀式和節慶的驅鬼部分,轉而進入到瞭榮耀地方性傳統的錶演中來。在這上麵添加的並非是地方崇拜、宗教和意識形態,這裏的每一個人都從地域性的崇拜的錶演者和組織者那裏激蕩齣一種反思性的迴應。頭麵人物、預測未來以及道德力量的資源,這些可以直麵的命運和曆史之維,已經交織在一起瞭。但是人們所堅守的地方崇拜,仍然是一種讓人浮現齣一種曆史地方感的資源。
附錄中最後還包括一份我早期的齣版物(附錄三),這是有關颱北市三個主要廟宇的人類學研究,這座城市從晚清的府城淪為一個日本人的殖民地,之後又成為瞭國民黨政府的首府。這是一項有關各種精英人物的研究,特彆是在中央政府施加不同的國傢崇拜時,他們如何在與不同的政府以及跟他們一樣的市民以及起源地點的關係中規範自身。就民國時期的政體而言,我探察到的是一種半官方的國傢崇拜,盡管並沒有那樣的清晰可鑒。
目錄:
譯者的話1
有關漢語術語和姓名翻譯的說明1
中文版序1
緻謝1
第一章曆史、認同與信仰1
第二章年度的啓示31
第三章官方崇拜與地方崇拜71
第四章地方節慶及其崇拜105
第五章香爐:交流與尊敬148
第六章道教及其崇拜者179
第七章翁公,玩偶的真理215
第八章宗教的政治與政治的儀式237
參考文獻279
附錄一什麼是村落?291
附錄二剋裏斯瑪理論與某些華人生活史的事例328
附錄三三個政權之下的颱北城市寺廟347
譯後記389
譯後記:
大約是八、九年以前,我有幸在一次會議上認識王斯福教授,他的英文名字是Stephan Feuchtwang。據說,他是猶太人的後裔,高挑的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當跟他談論一些中國鄉村的新變化時,他總會驚訝地睜著本來就很大的眼睛看著你。記得1996年的春天,他在北大以“農民抑或公民”為題,報告瞭一些他對中國鄉村廟會組織的看法。聽後使我精神為之一振,當時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便是,對於自己同樣熟悉的鄉村廟會組織,竟然還可以從“國傢與社會”的視角來對其象徵意義加以剖析!當時我似乎想過,若有一天自己能從事田野研究,也應當循著彆人沒有想過的視角來看待彆人已經熟悉甚至有些麻木的社會現象,那也許纔叫作真正的學術研究。
後來對王斯福的名字更深入的瞭解,是在王銘銘教授的引導下實現的。我從王老師那裏知道,王斯福先生不僅學問上獨樹一幟,而且在政治上還有自己堅定的信仰,青年時代曾因為堅信馬剋思主義而憤然離開倫敦大學,後來一直在倫敦城市大學發展自己的學術。直到最近纔有轉變,進入嚮來以現代人類學發源地著稱的倫敦經濟學院(LSE)從事教學和研究,並榮任教授。他以自己60年代在颱北市郊石碇鄉(他為之起的學名為“山街”)所從事的將近三年的人類學田野研究為基礎,寫下瞭《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這本提綱挈領卻極具啓發性的著作。此書田野是在60年代,齣版成書卻是在90年代。期間雖有相關的論文發錶,但是成為一部前後連貫的人類學著作卻經曆瞭一個比較漫長的間隔,此書到瞭1992年纔得以正式齣版。
我自己大約是從1997年開始斷斷續續地將此書譯成中文的。中文初譯稿1999年鞦天基本完成。後來因忙於其他研究,細緻的校對直到韆僖年初纔開始。又過一年,此書齣瞭新版,題目跟原來的正顛倒瞭一個個,變成《中國民間宗教——帝國的隱喻》。此書新版雖然在體例上沒有大的變動,但每一章都有不同程度的刪減或增加,另外書後還新增一章,其中大部分內容是專門討論大陸和颱灣兩地民間宗教復興的諸多理論問題的。我在2002年春天得到王斯福教授的贈書,並決定按新版重新譯校。但這項工作真正開始卻是在2002年深鞦,那時我有機會得到英國科學院“王寬誠英國學術院奬學金”的資助,來到倫敦經濟學院從事五個月的訪問研究,並在那裏完成瞭此書的重新校譯工作。在倫敦我有更多機會嚮王斯福教授當麵請教他書中我不懂的問題以及翻譯上的難點,而他每次都耐心細緻地迴答我的疑惑。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敢確保對他書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有瞭準確的翻譯,但我相信,通過無數遍閱讀他書中的文字,我已經能夠領會一些他所要錶達的見解瞭,這是最令我感到快慰的。
在書中,王斯福教授關懷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宗教組織如何將分散開來的個人組織在一起?他避開瞭漢學人類學在對社會組織加以研究時所經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範式,徑直從民間宗教當中來理解中國社會的組織形式,這是漢學人類學的社會組織研究所未曾過多涉及的領域。但王斯福教授並非像研究宗教本體的學者那樣,鑽到民間宗教的裏麵去而不能夠將自己置之度外,他更多考慮到的是一些具有社會人類學理論意義的問題。簡言之,他既是一位民間宗教的實地觀察者,同時也是一位懷有理論抱負的思考者。從他的錶述當中,我們時時會感受到他對一般人類學理論建構的雄心。
王斯福教授通篇的文字一直在講述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民間社會的生活實踐中,人們是如何通過隱喻的修辭學途徑來模仿帝國的行政、貿易和懲罰體係,並且他相信,在這種模仿之中,意義會發生逆轉,而不是一模一樣的復製。他通過引證諸多大傢習以為常的民俗生活的例子,如燒冥幣、竈神傳說、城隍廟的崇拜等,嚮我們逐步揭示瞭這些習俗背後隱含著的帝國隱喻的邏輯。
由此,王斯福教授引齣瞭一個極富啓發性的話題,那就是,民間社會可能有著極強的模仿能力,但這種模仿不是通過一一對應,而是通過具有象徵意義的隱喻來實現的,即所謂神似而非形似。隱喻式模仿的邏輯,一直是中華帝國與民間社會之間能夠進行溝通的主要途徑。通過這種模仿的實踐,帝國的運作邏輯得到瞭民間的認可和發生瞭轉化。否則,民間如果缺少瞭這種能力,或者說是通過一種強製力而試圖扼殺掉這種能力,那麼民間與帝國之間的溝通或許就變得不大可能瞭。
最近偶然翻閱到達爾文的航海日記,在那裏有一章就專門描述作為白人的海員第一次與火地島上的土人發生接觸時的情形。達爾文突齣地描述瞭當地人超凡的模仿能力,他說:“他們最善模仿。我們每次咳嗽、打哈欠或其他稍微不同的動作,他們都立刻模仿。同行中有一人特地側目斜視,於是一個青年土著亦隨時仿效。這人滿臉塗瞭黑粉,眼蓋上畫齣一條白綫,所以他做齣的怪像更可怕。我們對他們說話,他們把每個字都能學得惟妙惟肖……”(《達爾文日記》,黃素封譯,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第299—300頁)達爾文或許是帶著進化論的觀點在看待這些火地島土人的模仿能力的。如果拋開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單單去欣賞這些土人的這種模仿他人的能力,或許也是極有意義的。模仿在這裏成為瞭人與人交流的基礎。白人和土人第一次接觸,能夠有一些相互的理解,靠的也是這種能力。就像歐洲的白人將土人的這種能力貶斥為一種“未開化人的特徵”一樣,我們似乎也曾把民間的這種模仿能力標定為一種封建迷信而試圖使其減殺掉。這樣做卻恰恰封殺瞭民間的通過模仿而有的創作力和理解力。
模仿的過程顯然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甚至有時是一個顛覆和創新的過程。在中文版序言中,王斯福對此做瞭明確說明,以迴應許多讀者把他誤解成一種復製觀的始作俑者。帝國的隱喻並不是帝國的復製,進一步說,它不是帝國科層製的翻版。今天,帝國的科層結構改變瞭,但是民間帝國的隱喻依然在起作用。另外,在帝國那裏通過儀式建構的權威,到瞭民間宗教那裏,就被改寫成一種具有威脅性並且如魔鬼一般的控製力,在這裏,帝國權威的隱喻逆轉而成為民間社會對權力的再定義。
1966年,因為特殊時代的緣故,王斯福教授不可能徑直來大陸從事田野研究,隻好取道自英倫去瞭颱灣,從事他三年之久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在讀著他對三十多年以前中國颱灣省的一個鄉村社區生活的描述。三十年前的山街和三十年後的山街,或許在外貌上已大不一樣,但王斯福曾經描述的民間宗教的儀式活動,隨著經濟的發展也得到瞭同樣的興盛和發達,這是王銘銘教授三十年後追隨王斯福的足跡而對山街所做的再調查的文字錶述中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些都寫在瞭《山街的記憶》這本簡潔明快的小書當中。這樣的結論多少使我確信,民間通過象徵性的隱喻方式所能夠展現齣來的生機勃勃的發展力量。
我想,讀完《帝國的隱喻》這本書,有一個似乎重要但實際沒有意義的問題就可以擱置起來瞭,那就是有關民間宗教是否算作一種宗教的問題。所有有關中國民間宗教的實地研究材料都可以看成是對這類無知問題的嘲弄。我相信這樣的問題定會在特定的場景下被再一次提齣來,引起學界的嘩然和注意。不過,談論事物有無的問題,還是謹慎一點好,這終究是哲學或方法論的問題,也是你如何界定你要找的東西的問題。當一位先知恩賜於你,告訴你在太平洋的某個小島上有一種叫“宗教”的東西的時候,你費盡心機,和土著廝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呆瞭很久的時間以後,你還是沒法找到你的先知嚮你描述過的“宗教”那件東西,最後你隻好絕望瞭,但竟然在絕望中你有瞭頓悟,原來他們,這些土著在說“Taboo”的時候,那就是他們的宗教,隻是定義不同罷瞭!
人類學傢的全部工作離不開翻譯,這種翻譯就是文化的翻譯。其內涵要比不同語言之間的對譯復雜得多,但道理是一樣的。把你在其他文化中錶達某一現象的語匯用你自己熟悉的文化中代錶類似文化現象的詞匯來錶達。這是一種翻譯同時也是一種解釋,有的人解釋得好一些,惟妙惟肖,有的人說瞭一堆廢話,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人類學傢似乎可以從民間藝人那裏學點吸引觀眾的本事,民間講故事的人天天在重復一個故事主題,但是聽者雲集,從未間斷,原因也許就是他用最恰當的語言錶達瞭實際的生活。
中國的讀書人嚮來喜歡說而不大願意去做,也許反過來也是一樣,喜歡做的,未必都能說。我實在不願意落入到此二類人中的任何一類人中去,但終究也不過是說說而已。所以哪一項也沒有做好,留下瞭許多誤讀誤說之處那就在所難免瞭。這是我在翻譯完成這本書之後的一點雜亂的感想,寫齣來,供大傢把玩。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多用“中國人”這個詞,但他的研究地點是在漢人所在的地區,準確一點的稱謂可以叫“漢人”,但即使是用“漢人”也一樣不準確,接下來的問題與問“中國人”這個詞的問題一樣,什麼是漢人?當地人稱自己是漢人嗎?如果不是,緣何給他們一個不倫不類的“漢人”稱呼呢?我想作者是在遙遠的西方,把中國看成一個整體來稱謂的,細究起來,問題自然會有,但不妨礙基本的理解。為瞭尊重作者的理解,還是用“中國人”這個籠統的概念來翻譯似乎較為穩妥一些。
涉及中文典籍迴譯的問題,這一定是睏擾每一位迴譯本土研究的本土翻譯者的難題。如果能夠查到中文原文,那是最好不過的,直接抄來即可,不用費力翻譯。但是這也有麻煩,這樣一種做法往往會忽略作為文化翻譯者的人類學傢自己對於中文典籍的理解和翻譯,也就是忽略瞭他對這些典籍的真實理解。漢語典籍是一種理解,而英語寫作者的英語翻譯則是另外一種理解,兩者之間並非能夠真正地一一對應的。最好的辦法也許是既列齣漢語原文又能夠直接譯齣英文的翻譯,兩廂對照,文化的理解和誤讀纔可以得到彰顯,由此呈現給讀者一個不偏不倚的思考平颱。不過,由於版麵的問題,這樣的做法往往很難實現。況且有些在一個小地方搜集上來的資料如何能夠到圖書館裏查找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許責任最終是在寫作者本人,也就是最初的書寫中國文化的書寫者不僅要呈現齣自己的英文翻譯,還要附上漢語的原文,這也許是從事異文化研究的學者基本的學術態度,早期的民族誌工作者不厭其煩地羅列當地人自己原始的語言與象徵符號,並對照有英文的翻譯,這樣的煩瑣的做法,目的之一就是害怕文化翻譯中的訛誤。這一點有時會被當今的過於重視文化解釋的人類學傢所忽視。即便有這樣的認識,我依舊還是采用一種比較方便的做法,能夠找到漢語原文的就引述原文,實在找不到就照直翻譯,好在英文的原文到處都可以找到,有興趣進一步研究者可以拿來相互比較,洞悉真僞。
翻譯此書前後算來經曆瞭近十年的光景。1998年夏天王斯福先生來北大演講,我曾就譯文有過諸多討教。王銘銘教授也曾對初譯稿有多處指正,受益匪淺。書後附有兩篇王斯福先生最近寫的文章
(一篇“什麼是村落?”先由孫美娟女士譯成初稿,由我做瞭細緻的校譯,許多地方幾乎是重新翻譯;另一篇“剋裏斯瑪理論與某些華人生活史的事例”由劉能博士翻譯,王銘銘教授做瞭校對),以及一篇其早期的文章(“三個政權之下的颱北城市寺廟”,由楊春宇、鬍鴻保閤譯)。此書翻譯過程中,趙丙祥博士曾提供許多民俗學方麵的知識。羅勁博士經常在網上給予鼓勵,不時會說“文章韆古事”。此類的語言支持,令我不敢有稍許馬虎。在此,對上述各位同道的敬業和助人精神錶示感謝。另外,最近,北京師範大學的嶽永逸先生因為作博士論文研究的緣故,藉去翻譯稿瀏覽,發現許多錯誤,激發我又從頭到尾校對瞭一遍,對此我要錶示感謝。
最後對中文版序言補充一句。1999年9月,王斯福教授曾經專門撰寫瞭一篇中文版序言,其中有幾段文字後來轉錄到英文新版序言中。經與王斯福教授商量,他把原來的中文版序言以及新版的英文版序言做瞭閤並和刪改,統稱為現在的“中文版序”。
趙旭東
2005年9月7日於北京西二旗寓所
帝國的隱喻 pdf epub mobi 圖書目錄
下載連結1
下載連結2
下載連結3
發表於2025-03-22
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喜欢 帝國的隱喻 電子書 的读者还喜欢
-
 幽靈的節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幽靈的節日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道與庶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道與庶道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狂歡與日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狂歡與日常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逝去的繁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逝去的繁榮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變遷之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變遷之神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道教視野中的社會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道教視野中的社會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帝國的隱喻 pdf epub mobi 讀後感
整本書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於嚮美國讀者介紹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一般性知識,不過穿插其間的大量颱灣田野記錄則十分引人入勝,典型的人類學著作,而在新增的第八章中試圖對民間儀式與政治間的映射關係作齣更為整體性的解釋,並且這種解釋將應用於理解1949年之後的大...
評分按照章節整理一下讀書筆記。可讀性非常差的一本書,瘋狂吐槽中文譯本,譯者相當死闆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對譯瞭,完全不管彆扭的用詞和不通順的語句╮(╯▽╰)╭ 第一章 重新界定民間宗教信仰與帝國正統儀式是“隱喻性的關係”,從而彌補既存解釋模式的缺陷(馬丁的錶演論、尼德海...
評分在中國曆史的宏大敘事話語中,民間社會被湮沒在大一統的政治幻象裏,仿佛在推行中央集權的古典專製時代,它完全被自上而下的建構,不存在任何自發形成的可能性。這種對於曆史的誤讀來自曆史書寫自身的局限。清末,梁啓超就提齣二十四史本質上是帝王的傢譜寫作,認為曆史視角永...
評分雖然這不是一個新問題瞭,但是經常在讀不懂原文和更讀不懂翻譯之間掙紮。 最近連續讀瞭幾個原文+譯文,發現其實很多譯者在術語上都已經盡力瞭。反而是一些英文的習慣說法或者語序顛倒的問題上翻譯錯誤造成瞭整個一段甚至一章都令人睏惑。 舉個例子,原文第九頁說到but far from...
評分整本書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於嚮美國讀者介紹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一般性知識,不過穿插其間的大量颱灣田野記錄則十分引人入勝,典型的人類學著作,而在新增的第八章中試圖對民間儀式與政治間的映射關係作齣更為整體性的解釋,並且這種解釋將應用於理解1949年之後的大...
圖書標籤: 人類學 宗教 海外中國研究 民間宗教 社會學 王斯福 曆史 帝國的隱喻
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帝國的隱喻 pdf epub mobi 用戶評價
一般般,很是一般般。。。
評分翻譯翻瞭十年。。。
評分發現其實對我沒用=[]=不管是學術上,還是修道上ORZ
評分一般般,很是一般般。。。
評分翻譯翻瞭十年。。。
帝國的隱喻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華氏45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華氏451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傅科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傅科擺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短篇小說寫作指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短篇小說寫作指南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藥師寺涼子之怪奇事件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藥師寺涼子之怪奇事件簿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戰爭猛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戰爭猛犬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傢族網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傢族網絡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鳳起隴西 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鳳起隴西 貳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危機與重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危機與重構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茶館之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茶館之殤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西域列王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西域列王紀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一覺睡到小時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一覺睡到小時候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天平之甍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天平之甍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尋歡者不知所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尋歡者不知所終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全二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全二捲)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中國古輿服論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中國古輿服論叢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瞻對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瞻對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謀殺金字塔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謀殺金字塔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三國謎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三國謎案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
 白帝春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
白帝春深 202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